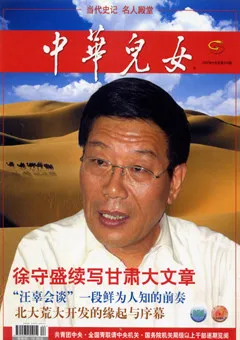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畫

說我的收藏故事,要先說我的岳父姜椿芳。他是1931年入黨的老革命,“文革”中遭迫害,坐了六年八個月秦城監獄。在極惡劣的環境下,他構想出中國第一部《中國大百科全書》并擔任第一任總編輯,被公認為中國現代百科全書之父。
三代人的收藏故事
生活中,岳父姜椿芳喜愛收藏字畫,他家里的客廳是京劇大師馬連良家的排練廳,面積比較大。“文革”之后,他交給我一個任務:把退回來的字畫進行分類整理。我找來幾大本明清和現代書畫家名錄作為依據,把書畫作品一幅幅展開,鋪在地板上仔細查看、登記。這是一個大開眼界又長知識的工作,我仿佛被人世間崇高和真切的情感所包圍,腦海中想象著他們在創作這些書畫作品時的情景;感動于先輩藝術家內心世界的完美,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每天岳父下班回來,我都急切地向他匯報我的工作成果,把我感興趣的字畫介紹給他聽,展示給他看。他又把他了解的名家情況講給我聽,我才逐漸了解到這些字畫后面藏著的更加深厚的學問,從此,我也深深愛上了收藏書畫。
我也從小畫畫,并靠畫素描考上了中央歌劇院舞臺美術工廠。后來劇院領導和歌唱家郭蘭英等人發現我的歌唱能力,我又被調到歌劇一團。
在岳父的熏陶下,從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到現在,我也收藏了不少書畫作品,也有一些當今名家之作。
女兒紀翔宇從小看到人家送給我的作品都題寫上我們夫婦的名字,她問我為什么不寫上她的名字,后來一些書畫家題寫落款時,我就說“題我女兒的名字吧”。現在,她也收藏了一些質量不錯的作品,
看著家中根據季節和節日更換掛著書畫作品,感覺就像換了新房子、新環境,而能夠認識那些人,了解書畫背后的故事,則更讓人心生感動。
姜椿芳:不因字畫畏權貴
“文革”時,岳父姜椿芳家中被抄,只剩下幾張床和一張小餐桌,他多年收藏的珍貴書畫也全部被抄走。1975年1月,鄧小平復出工作,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開始了對“文革”的全面整頓,其中包括對“四人幫”迫害的大批干部的冤假錯案進行改正。同年4月19日,姜椿芳終于被釋放回家。有關部門把原先抄走的書畫退了回來,但很多都已被損壞。不僅如此,有關部門還強行收買了四幅字畫,其中有趙樸初先生送給他的清代“十八羅漢圖”,收買的理由是宣傳迷信,每幅收買價格為二角錢,并強迫他簽收。姜椿芳拒絕簽字,更沒有要那八角錢,趙樸初得知后也深為那四幅畫而惋惜。后來,這四幅字畫都不知了去向。
同時,岳父還有令人吃驚的毅力和才能,書畫上的草書、篆書沒有一個字他不認識,干支年號他看一眼便知公歷是哪一年。岳父告訴我,他年輕時喜歡篆刻,對各種字體都有過研究,干支年號轉換成公歷,則是他在秦城監獄時,怕自己腦子變遲鈍,不斷給自己出題目練出來的。
趙樸初:佛家的遠見
抗日戰爭初期,姜椿芳在上海從事地下黨文化工作,認識了從事慈善事業和佛教研究的趙樸初先生,從此成為最親密的戰友和朋友。趙樸初對我們也像對自己孩子一樣。趙樸初每寫作一首新的詩詞都會講給我們聽,當時我會背誦不少他的詩詞。我們結婚時,趙樸初夫婦親自到場祝賀,并把他的詩作《芝麻開花節節高》書贈給我們,表示祝福。

1976年,周恩來總理病逝,天安門廣場上懷念總理、痛罵“四人幫”的詩詞很多,其中不少模仿趙樸初的詩詞風格,有的干脆就把作者的名字寫為趙樸初。那段時間我一有工夫便去天安門廣場,不敢用筆抄錄那些詩詞,只能用腦子記,然后到趙樸初家里講給他們夫婦聽。當時有關部門還分別找趙樸初和他妻子談話,氣氛十分緊張,好像要把他們夫婦抓起來。但趙樸初無所畏懼,他經常與姜椿芳見面,交談當時的政治形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讓我的岳父——當過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局長的姜椿芳,在諸多馬列著作中查找有沒有“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論述,從一個側面說明他們對那種極“左”的東西何其反感。趙樸初熱愛北京,“四五”運動后,他對北京人愛憎分明的立場很是贊賞,并題詩“燧人取火非常業,世界從此事事新。五十萬年過一瞬,還看今日北京人。”并把這首詩贈給我們夫婦。
上個世紀90年代,我請趙樸初看我們劇院的演出。他對古箏改革感興趣,對古曲“高山流水”有了新的想法,于是寫了一首散曲給我們:“可憐那伯牙琴只為子期彈,卻不料今日弦鳴萬眾歡,恨當年高山流水知音少,幾曾知低抹輕揮聽者難。今日啊!滿堂傾耳獻高山,奔昆侖屋頂車輪轉……”2006年7月10日,火車真的開上了天路,這是佛家的遠見,趙樸初在佛國也會聽到這隆隆的火車聲。
楚圖南:八十習字
“千山聞鳥語,萬壑走松風。居身青云上,植根泥土中。”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楚圖南贈給我的書法作品中的一首詩作。
楚圖南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到哈爾濱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在哈爾濱三中當老師,我的岳父這一時期考入三中,成為楚圖南的學生,解放后他們都成了黨的高級干部。楚圖南對我們夫婦說:“不管在什么地方,你爸爸見到我都給我鞠躬。說這是行弟子之禮。”
楚圖南長期從事對外文化交流和民間友好工作,先后出訪過幾十個國家和地區。
80歲以后,楚圖南開始練習書法,每天上午都要練一個小時,他戲稱自己是練氣功。他還給自己取筆名為“高寒”,并存有兩方印章,一方是“高寒八十歲以后書”,一方是“高寒九十歲以后書”。我多次看他在家習字,雖已如此高齡,還親自裁紙、研墨、蓋章,一切自理。楚圖南德高望重,是民盟中央主席,中國世界語協會主席,我岳父姜椿芳病逝后,他還親自為自己的學生題字:“效忠革命 專研馬列主義;弘揚文化 倡辦百科全書”,總結他的學生的一生。
啟功:大家“刷”字
啟功先生是書法大家。他性格爽朗,語言表達極富個性。當年在全國政協文化組,我岳父和他是正副組長,經常在一起開會,關系很好。
我愛人在榮寶齋工作,啟功也經常去那里,告訴我愛人,“我和你爸爸同歲,我比你爸爸大一個月”,“我也是榮寶齋出身,二百五起家”。這是說最初他的書法作品最高只能賣到250元。
一次,我們夫婦去啟功家,正好趕上沈尹默的親屬從西北來到啟功家里求字。談到沈尹默,啟功興致很高,高興之余便說:“你們別白來,我給你們刷幾筆。”啟功還講:“前不久,楊尚昆同志讓我給他寫幅字,我問他您讓我寫幅什么字啊?什么時候要?楊尚昆同志說,您什么時候有功夫就寫,我也不著急。”啟功對我們說,人家求你寫字是看得起你。我再給你們講個故事:“一個人站在畫案前,看著畫案上的宣紙,得意洋洋,提筆蘸墨正要大筆一揮,畫案旁一個人跪在地上,雙手直作揖,你們猜這是怎么回事?”我們都說這是感謝那位寫字的人。啟功則笑說,“不對。跪著的那個人說,求求您了,我好不容易攢了錢,買了宣紙,您手下留情吧。”我們幾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那次,啟功寫了自己最拿手的《登鸛雀樓》送給我們夫婦,“白日依山盡,黃河人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整幅字剛勁灑脫,寫完后,啟功自己也挺滿意,說:“我寫字和你唱歌一樣,心情很重要,高興就寫得好。”
新鳳霞:霞光萬道,瑞氣千條
吳祖光、新鳳霞也是我們夫婦崇敬的人,來往很多,我們也收藏了他們夫婦的好幾幅作品。

新鳳霞病后不能再演戲了,心情不好,脾氣急躁。吳祖光就耐心地為她創造條件作畫,筆墨紙硯、顏料都準備齊全,再加上新鳳霞本是國畫大師齊白石的干女兒,受過真人指點,又天資聰穎,進步很快。
從此,吳祖光家里滿屋子都是她的畫,荔枝、扶桑、壽桃、梅花等等,她用筆開創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后來,吳祖光見她的畫有了一定的水平,便開始為其題字。吳祖光的父親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創始人之一,他本人又是書法大家沈尹默的弟子,書法很好。有人評論吳祖光的字、新鳳霞的畫是“霞光萬道,瑞氣千條”。
新鳳霞從小沒有上過學,連自己的生日也不知道,還是老舍先生給定的生日:臘月二十三,過小年這一天。解放后新鳳霞上了文化部的掃盲班,和歌唱家郭蘭英是同學。一次在她家吃飯,她對我說:“剛一解放,女干部們都穿上了女式列寧裝,上衣上邊有一個斜兜,都插上一兩支鋼筆,顯得有文化又神氣,我也盼望著自己也能有文化,兜里也插上鋼筆。一次我撿了個筆帽,也插在上衣兜里好幾天,覺得自己也有文化了。”她邊說邊捂著嘴說:“不好意思。”不過,后來新鳳霞經過自己不斷努力學習,不但出了不少書,而且精彩,非常讓人喜歡,還成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吳祖光家客廳的墻上掛著一幅齊白石畫的白玉蘭圖,其實,這幅看似平常的畫中還藏著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1957年,吳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一家老小都靠新鳳霞養活,生活十分困難。一次實在沒有錢了,家里就把這幅白玉蘭圖賣掉了,后來幾經轉折,這幅畫又轉到榮寶齋。一天,老舍先生在榮寶齋看到這幅畫,非常喜歡,花了不少錢買下來。他回家后仔細觀賞,突然發現畫背面用鉛筆寫了‘祖光’兩個字。老舍先生一想,這一定是祖光家的收藏,于是把這幅白玉蘭圖完璧歸趙,送還回去。買畫、送畫,大家風范和仁者情懷體現得淋漓盡致。

江樹峰:有人叫他“皇叔”
1993年11月1日上午,我給住在德勝門外的江樹峰打電話,想在3日到他家去。他說不行,“中南海要來接我,等我回來吧。”沒有想到這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通話,3日,江樹峰病逝。
江樹峰是江蘇省揚州市政協原副主席,江澤民的七叔。解放前,姜椿芳是上海地下黨文委書記,創辦了以蘇商名義公開發行的黨的刊物《時代日報》和《時代雜志》,江澤民的夫人王冶平在那里工作過。剛解放,姜椿芳又創辦了上海俄文專科學校(現上海外國語大學),王冶平又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有了這層關系,再加上江樹峰十分崇敬姜椿芳,所以和我們夫婦的關系很好。
當時全國政協成立中華詩詞學會時,江樹峰是歲數大的,能詩會寫的副秘書長;我是歲數小的,不會寫詩只能跑腿的副秘書長。他不但古體詩寫得好,英語也特別棒,每天都看全英文的《中國日報》。江樹峰講話也很有趣,看到當時北京流行“蓋了帽兒了”,他也這樣說。他看到我認識人多,能聯系,能跑腿,就給我起了個外號“不得了”,還經常讓我陪他參加一些社會活動。
江樹峰揚州老家有親戚,有人來看他時,進門還給他磕頭,叫他“皇叔”,說一些夸張的奉承話。他都會用幽默的玩笑逗人家一笑,讓他們今后不許這樣。
晚年江樹峰十分喜愛書法和繪畫。我多次陪他到琉璃廠中國書店和榮寶齋,我愛人也為他提供了一些碑帖和畫冊。他每天都在家中認真臨摹練習,他的字的確越寫越好,但他卻經常風趣地評價自己的字,“這個字不怎么樣”,“那幅格局不好”,“看那幾個字是不是有我們揚州鄭板橋的味兒”。他還讓我請人刻了方印章“轉益多師是我師”,表明對他有過幫助的人,都應該尊敬為自己的老師,他的作品上都蓋有這方印。刻這枚印章的是青年畫家邵戈,江樹峰欣賞邵戈的才氣,說他的畫是有形的詩,畫出了生活中的自然情景。他親自給邵戈題字:“日月山川氣,風云松竹濤”,還請當時十分年輕的邵戈當他的水墨畫老師,真是活到老,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