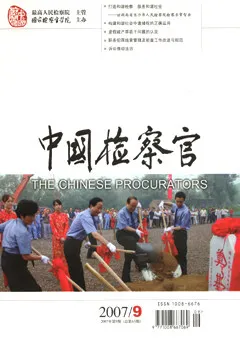為被強奸者私下索要賠償是否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
一、基本案情
某男甲,一日凌晨接到前妻乙的電話,得知其被丙強奸。甲隨即找到丙進行責(zé)罵并毆打,丙逃走。隨后丙打電話給甲,勸甲不要沖動,有事好商量。甲稱此事不會就此罷休。后雙方多次為此協(xié)商,在協(xié)商過程中甲曾數(shù)次追打丙。最后丙提出用賠錢的方法來解決,甲提出要對方賠償10萬元,經(jīng)丙還價為5萬元。此后甲數(shù)次打電話索要該款,說如不給錢,則將此事鬧到丙家。丙交給甲2萬元現(xiàn)金并出具3萬元的欠條。甲將現(xiàn)金及欠條交給了乙。
二、分歧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甲的行為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甲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丙財物的主觀故意,客觀上采用毆打、言語威脅、恫嚇手段強索他人財物,符合敲詐勒索罪的犯罪構(gòu)成。甲在得知丙強奸其前妻后,多次對丙實施暴力毆打等行為,致使丙被迫提出予以金錢補償。后又多次打電話以要挾的言語索要該款。至于敲詐得來的錢交給乙,并不影響甲非法占有的主觀要件,“非法占有”并非一定要“非法自我占有”。
另一種觀點認為,甲的行為不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甲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開始,甲對丙實施暴力行為,并非為索取非法財物,而是得知丙強奸其前妻后的激烈反映,是一種泄憤行為,其并未向丙索要財物。后丙為解決其強奸行為而提出給予財物補償,甲向丙索要財物,只是幫乙催討債務(wù)的行為。債權(quán)人為討還債務(wù)而使用帶有一定威脅成份的語言及行為,催促債務(wù)人償還,不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甲為乙催討債務(wù)并將所得全部交給乙,同樣也不應(yīng)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
(一)乙與丙之間存在著刑法上的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
強奸是一種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的行為,這種案件,一方面需要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同時在民事上也是一種侵權(quán)行為,存在著侵權(quán)之債。從此類案件的性質(zhì)來看,其賠償主要集中在精神損害方面。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問題的批復(fù)》規(guī)定對于刑事案件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失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在該刑事案件審結(jié)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損害賠償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理由主要是行為人既已受到刑事處罰,足以慰撫被害人的精神損害。此觀點顯然違背了民事責(zé)任與刑事責(zé)任分屬不同責(zé)任的基本理論,自不待言。最高法院解釋理由是否允足的問題暫且不論,此批復(fù)在實踐中形成了因犯罪行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shù)貌坏剿痉ň葷默F(xiàn)狀。
雖然基于強奸而提出侵權(quán)之訴得不到司法的救濟,但并不意味著這種債權(quán)不存在。從傳統(tǒng)民法理論上講,這種得不到法律保護的債權(quán)系不完全債權(quán),其典型例子是超過訴訟時效的債權(quán)。這些債權(quán)雖然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但不能說這些債務(wù)不存在,債權(quán)人完全有權(quán)利接受債務(wù)人的履行。我們不能僅憑丙是否愿意交付財物來確定其是否受到了敲詐勒索。例如在采用威脅或要挾手段催討欠債時,債務(wù)人付錢也是迫于無奈,也是非真實意思的表示,其真實意思是不想還債的。所以對于交付財物的行為并不能看交付財物的人是否愿意或不愿意,而應(yīng)看其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交付該財物。如果被害人并無交付財物的義務(wù)存在,可以認為這是違背其真實意思表示而受到敲詐勒索。從民事法律的角度來講,強奸行為是一種嚴重侵害公民人身權(quán)利的侵權(quán)行為,其所形成的侵權(quán)之債,無論從法律上或者事理上講,其應(yīng)受保護的必要性都遠甚于賭債。所以其自然應(yīng)屬刑法中所稱的債務(wù)。
(二)甲索取的財物沒有明顯超過乙對丙的債權(quán)
丙對乙負有侵權(quán)之債的債務(wù),已如上述,但該債務(wù)的數(shù)額并不確定,系不具體的債務(wù)。甲對丙索取5萬元是否明顯超過該不具體的債務(wù)?依筆者的觀點,應(yīng)依大眾的一般價值判斷來衡量。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性的市場化、交易化也有不同程度的發(fā)展,貞操觀念相對于傳統(tǒng)觀念而言,已漸趨淡薄。餓死者事小,失節(jié)者事大,已成為歷史。但傳統(tǒng)的貞操觀念仍為主流社會所重視,貞操在社會公眾心目中仍具有相應(yīng)的價值。強奸行為,嚴重侵犯了婦女的性的不可侵犯的權(quán)利,是對婦女所特有的貞操的破壞,是對婦女的人格尊嚴的嚴重損害,同時也會對其社會名譽造成極大的損害。從大眾的一般價值觀來判斷,婦女遭受強奸而得5萬元的金錢賠償,并不為過。反言之,有誰愿意為5萬元而遭人強暴?所以說甲為乙被強奸向甲索要5萬元的賠償,不能算明顯超過乙被侵權(quán)而取得的債權(quán)數(shù)額。
(三)甲采用要挾的方法為他人索取財物,不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
本案中,甲系為其前妻乙向丙索要財物,并非債權(quán)人為實現(xiàn)自己的債權(quán)而索取財物。但既然債權(quán)人為催討債務(wù),使用威脅或要挾的方法,不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而不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則行為人代為他人催討債務(wù),同樣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也不應(yīng)以敲詐勒索罪論處。本案中,甲基于以前的夫妻關(guān)系代乙向丙索取債務(wù),客觀上甲也將索取的財物全部交給了乙,甲的行為不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
誠然,甲的行為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其實施的自力救濟行為并非法律所允許。作為民法的私力救濟,其有一定的范圍及限制。從國家的法律來講,對于民事權(quán)利的救濟,主要依賴國家的強制執(zhí)行力,而不提倡以私力加以解決。本案甲的行為顯然超出了法律允許的私力救濟的范圍,但是這種行為雖然具有違法法,并不意味著其必然就構(gòu)成刑事犯罪。筆者認為,從刑事法律角度出發(fā),由于敲詐勒索罪系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其表現(xiàn)為直接故意,必須具有非法強索他人財物為目的,此類存在著民事法律上的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的案件,不具有非法強索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故不應(yīng)認定構(gòu)成敲詐勒索罪。至于其是否構(gòu)成其他犯罪,則應(yīng)從其行為是否符合其他犯罪構(gòu)成要件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