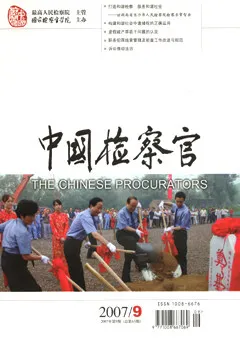訴訟推動法治
法治之路漫長而曲折,特別是對一個擁有幾千年獨特文化傳統的國家而言,法治之路更加艱辛。實現法治目標的艱難有其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但不可否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缺乏訴訟的膽識和勇氣,簡單一句話:怕打官司。中國有句諺語: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轉,其反映的是訴訟的難度,打官司的離奇和曲折。《笑林廣記》記載:官吏聽訟斷獄“無是非,無曲直,曰打而已矣,無天理,無人情,曰痛打而已矣。故民不曰審官司而曰打官司,官司而名打,真不成為官司。”時至今日,觀民意、察民心,這種想法仍舊占據我們普通百姓的心中,仍舊讓我們不想打官司、不愿打官司、不敢打官司。
其實,打官司,即學理上說的訴訟,它的作用遠遠超過打官司以及官司勝敗本身。訴訟,進而引起法院對一個事實的認定,對一個行為的法律判斷,其意義是巨大而深遠的。我們都知道,如果沒有喬占祥狀告鐵道部,也許我們會繼續的對一些習以為常的但未必合理的現存制度更加的習以為常;如果沒有齊玉玲狀告教育部,我們對招生問題的反思也許引發不了那么多人的關注;如果沒有郝勁松先后7次將國家稅務總局、北京地鐵運營公司、北京鐵路局等單位告上法庭,我們對生活中自己所擁有權利的認知也許沒有那么深刻;等等。誠然,姑且不論這些案件中原告是否勝訴,案件的結局又如何,至少有一點可以明確,它引發了人們對一些現存制度的關注和思考。特別的,因為這些訴訟,有些已經存在卻不甚合理的制度受到了質疑和挑戰,這種質疑和挑戰又讓我們對一個個耳熟能詳的詞匯如“強制保險”、“乙肝歧視”、“就業平等”等有了更加深邃的思考;相關部門也自動的或者說更加審慎的處理相應的問題,甚至會修改一些不合理的——如果沒有人提起訴訟這些不合理將永遠存在——規定。由此可以得知,訴訟的效果已經超出官司(個案)勝負的評價,訴訟本身就是一種效果、一種進步,它喚起人們對某個關系全體公民利益問題的關注,進而維護和促進個人合理權益的發展,推動了法治的進程,促進了社會的進步,為邁進和諧之路增加了無窮的動力。
當然,司法資源是有限的、稀缺的,經不得浪費,訴訟是否經濟是整體司法工作優異與否的一個重要的考量標準。筆者主張通過訴訟解決問題并非強調爛訴,并非鼓勵什么事都通過訴訟來解決。相反,筆者主張善待司法資源、嚴格審慎運用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這要求我們要把資源的利用最大化。邊際成本最小化而邊際效益的最大化是我們衡量訴訟是否具有價值的重要參考,稀缺的資源也有其最大的利用價值。法律所創造的規則對不同種類的行為都會產生隱含的費用,因而這些規則運用的后果以及規則本身實施可當作對這些隱含費用的反映加以分析。如果一個訴訟能夠推動解決很多社會問題,那么它產生的效應是規則本身隱含費用的最小化付出,而且體現了實際成果的最大化。因此,訴訟后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和解決問題的力度其實很大程度上發揮了訴訟本身的作用,訴訟通過尋求司法救濟來維護公共權益,其強大的社會影響將引起更多的人來維護自身權益,讓弱勢群體的維權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合理的訴訟、正當的訴訟其實在發揮著推動國家向法治之路前進助動力的作用,它同時讓我們將是否公平、公正交付于司法來審查,讓正義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
法治,要求人們充分尊重法律、尊重法律所賦予人們的基本權利。在自己合法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個人利益在對應其他團體利益顯得那么弱小的時候,法律應該給予充分的保障。盧梭曾有言:“恰恰因為事實的力量總是傾向于摧毀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應當總是傾向于維持平等”。而司法的被動性決定了沒有訴訟,法律的作用可能受到限制,便無法實現維持現實平等的目標。所以,當一些長期存在的不合理現象在我們周圍徘徊的時候,訴訟猶如正義使者,它的功能不僅在于解決糾紛,而且在于通過解決糾紛以及訴訟本身的過程展示了現代法治文明,樹立了行為的模式,禁止了邪惡的事件,成就了善良的風俗。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這么說,即使是訴訟實體結果上出現了無可奈何的結局,訴訟本身所蘊含的法治精神卻是巨大的,將逐漸煥發它的光彩。正如培根所言:“對于一切事物,尤其是艱難的事物,人們不應期望播種和收獲同時進行,為了使它們逐漸成熟,必須有一個培育過程。”在共和國法治路上,在今天我們追求法治理想的社會里,訴訟將是孕育法治之果的良品優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