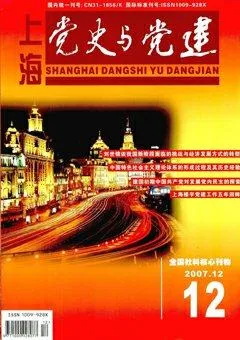吳貽弓:我的電影里也有政治
口述者:吳貽弓采訪、整理:王嵐
采訪時間:2007年5月15日下午
采訪地點:上海市文聯
吳貽弓:著名導演。全國文聯副主席、全國影協主席、上海文聯主席。曾任上海市電影局副局長、局長、上海電影制片廠廠長,上海市廣播電影電視局藝術總監。他先后執導影片《我們的小花貓》(合導)、《巴山夜雨》(總導演吳永剛)、《城南舊事》、《姐姐》、《流亡大學》等。1979年獲文化部優秀青年創作獎、第一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第二屆文匯電影獎最佳故事片獎和最佳導演獎;《城南舊事》于1982年獲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最佳故事片金鷹獎、1983年獲中國電影第三屆金雞獎最佳導演獎、第十四屆貝爾格萊德國際兒童電影節最佳影片思想獎、1988年獲第五屆厄瓜多爾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上世紀80年代,被評為“新時期全國影視十佳導演”之一。1993、1994年分別獲得第二屆上海文學藝術個人杰出成就獎和寶綱高雅文學藝術個人杰出成就獎。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
1960年我北京電影學院畢業,被分到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擔任導演助理。當時導演分4個職級,有導演、副導演、導演助理和場記。我一進廠就是導演助理,是挺幸運的。還有一個幸運是,我進廠后跟的都是中國電影第二、第三代大導演,有沈浮、鄭君里、孫瑜、徐韜、吳永剛還有魯韌等。我覺得,跟不同的導演能學習和掌握不同的風格,跟著這些大導演,我確實學到了不少東西。從進電影廠到“文革”開始的6年,是我重新學習的過程,相當重要。那時,沈浮是海燕廠廠長,他也很鼓勵老導演和年輕導演相互搭檔,以老帶新,取長補短,這樣年輕導演可以學到東西,同時也可以幫老導演分擔一些具體工作。進廠后有一年見習期,我第一個跟的是孫瑜,拍了一部黔劇《秦娘美》,第二個跟的是徐韜,拍了《豐收之后》,后來又跟鄭君里拍《兄妹探寶》。拍完《李雙雙》后,導演魯韌和我講,你以后一直跟著我好了。但我還是想跟不同的導演拍電影,可以多學點。再后來,沈浮點名讓我跟他一起拍《北國江南》,秦怡是主角,演一個瞎子。后來這部電影被打成“大毒草”,我想不通。后來就“文革”開始了。
拍《北國江南》時我還是導演助理,小人物。批判時我沒有受到牽連。這部片子一開始廠里蠻重視的,連張春橋他們都來直接過問,不過在拍攝過程中倒沒有受大的干擾。后來形勢發生了變化,這是當時難以預料的。
當時市委領導對電影抓得很緊,因為列寧說過一句話:電影是所有宣傳武器中最重要的武器。電影的受眾面最廣,不抓不行。《北國江南》在全國遭批判后,老實、善良的沈浮想不通,在會上總是嘀咕:我怎么會反黨?我怎么能反黨?
“文革”中我在上海生物化學制藥廠當工人,翻三班。因為我屬于被廠里清理出階級隊伍的人,我老伴雖然出身好,根正苗紅,但因為嫁給我,也被清理,成為階級異己分子。
電影廠的人大多去了“五七”干校。上影廠的“五七”干校基地,在遠離市區的奉賢海邊。“文革”開始時我28歲,這之前,我和大多數青年人一樣一心想做一番事業,“文革”一來,沒事好做了,反而閑了下來,我也就是那時結婚的。我靠邊是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祖父是杭州的大資本家,開錢莊、開電燈公司,屬于本土的大實業家。我父親又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的財務委員,解放后就成了歷史反革命。還有,因為我19歲還在大學讀書時,就已經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到“文革”自然一起算總帳了。
你問我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我在學校說,電影學院作為高等學府,不應只學蘇聯電影,還應學習美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電影。現在想想當年這話也沒錯。我被打成右派,受到“留校察看”處分。我還算幸運的,我的老師吳國英竭力為我說好話,才讓我跟班學習,盡管還要打掃廁所什么的,在她的爭取下,我終于在畢業前摘掉了“右派”帽子,比較順利地分到上海。和我一屆的表演系學生許還山就慘了,他被弄到新疆十幾年,九死一生,后來好不容易才到了西安電影制片廠,回歸文藝隊伍。
當了副局長后,組織上對我有所要求,想想自己是共和國培養起來的,內心也有一種熱愛黨的情結,就寫了一份入黨申請書。這也是第一次提出入黨要求,后來很快就被通過了。我的入黨介紹人是張駿祥和所在黨支部的支部書記。
“文革”中大家都很苦悶。但是我和那些最純樸的工人們在一起還是很開心。我和他們一起搞技術革新,通過反復試驗,產量提高了三倍,三班制改為早中兩班制。可以說,28歲后,在我世界觀人生觀逐漸成熟的階段,我對人生有了一次新的剖析,在工廠里,我可以更加客觀地看人看事。我記得《李雙雙》的編劇李準說過一句CfKIjsixxsiW8aQZ2c8qHA==話:生活不會虧待人,有失必有得。所以,盡管十幾年在工廠里,盡管失落苦悶,但這也是生活的積累,也因此,“文革”后我能在電影事業上一下子爆發出來。
1978年我拍了《我們的小花貓》,這是個短劇,和另外兩個短劇合在一起才一個半小時。這可以說是一場大練兵、熱身賽。電影發行蠻好,挺受歡迎。
接下來就拍了《巴山夜雨》和《城南舊事》。《巴山夜雨》總導演是吳永剛,這部電影和當時其他反思“文革”的作品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盡管“文革”是一場浩劫,但在電影中還是想通過人的善良的一面來表達一種對人生的看法,在“文革”的廢墟上建立人性的光輝。所以,這部電影中沒有出現一個壞人,人人都是重要角色,缺一不可。
拍這部電影時,交通部特批了一艘船,就是東方紅40號。我們在船上拍了將近一個月,除了工作人員,船上所有人員都是攝制組人員。那時候的人就是純樸,從來也沒有想到要帶些客人可以賺點錢。我們從奉節到宜昌來來回回開了21次,船上的老船長本事很大,巫峽有一段只有90米寬,船身長有70米,他就在那里掉了個頭。這部電影中所有角色都是專業演員,整部電影沒有補拍過一個鏡頭,這對我第一次擔任執行導演是一個很大的鼓舞。影片拍成后送審也很順利,夏衍還寫過一篇文章發在《人民日報》上。
1981年,臺灣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說《城南舊事》發表后在臺灣引起轟動。當時兩岸還沒有文化交流,小說沒有在大陸公開發行。葉劍英發表對臺9條①講話后,中國社科院臺灣文學研究所引進了這部小說,但沒有公開發表。北京電影制片廠編劇伊明最先看到了小說。他是我的老師。他很想把這部小說拍成電影,就動手改編。當時這個項目是北京電影制片廠的,不知道為什么北京后來不拍了,我到現在還不清楚其中的原因。當時文化部管電影的副部長是陳荒煤,他把這個本子推薦給上海,有兩個人看中了,一個是徐桑楚,一個是石方禹。他們兩人看了后,覺得我的風格比較符合這部電影的調子,商量后就把我叫去。
能被廠長叫去是很榮幸的。我看了劇本后,覺得本子很好,當場就被打動了,可就是覺得統戰意識太強。我暗想這不會是作者本人的想法吧?我斗膽向廠長提出,能不能看看原作?不久,我看到了小說的復印本,有的地方字跡都看不大清楚,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已經很可貴了。看后覺得,作者小說中充滿了樸素、溫馨的對故鄉的回憶,作者字里行間流露的是對故鄉的一種難舍情結,雖然筆調淡淡的,但是感情是濃濃的。這么好的小說,只要老老實實拍出來就行了。故事本身就是愛國主義的,根本用不著加什么。廠長問我怎么樣?我就跟廠長說,我再寫一個導演臺本吧。我用了一個半月時間,寫出了導演臺本交了上去。
上面對我們改編是肯定的。但我說伊明是我的老師,他仍然是編劇,我只當導演。導演是有改編權的,那也是再創作。伊明看后對我說,小吳,你膽子蠻大的,里面怎么一點政治都沒有?我說,這個本子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們只要拍出來,統戰部肯定歡迎。伊明對我的改編也首肯了。林海音事后說,辛虧沒加,否則臺灣決不會放這部電影!
我先見到林海音的兒子,他在美國當建筑工程師。當知道他要來大陸后,我們就邀請他。他很激動,說他母親很感謝我把她的小說搬上銀幕。當時原作者的稿費只有800多元人民幣,他就代表他母親象征性地拿了一美元,當時折合人民幣還不到4元,還說,我代表我母親拿過版稅了,我一定把錄像帶帶給我媽媽,她肯定會非常高興。我非常感動,我們沒有經過她同意就把她的小說拍成了電影,他們一點都不計較,這本身不就是一種愛國行為嗎?第一個錄像帶就是我們通過林海音的兒子帶出去的,在臺灣影響很大。所以,林海音1988年來上海前已經看到這部電影了,我們見了面她還說感謝我讓她在內地出了名。
《城南舊事》好像沒有在臺灣公開放映,但幾乎人們都知道這部電影,錄像帶的功勞不小,看過的人不少。
1983年1月9日,我隨中國電影代表團帶著已攝制完成的影片《城南舊事》出席了第二屆馬尼拉國際電影節。馬尼拉國際電影節是當時號稱亞洲第一大電影節,參賽國家眾多。在22部入選參賽片中,東道主和美國各有2部,其余18部分屬18個國家,《城南舊事》即是其中之一。
《城南舊事》和所有參賽片一樣,預定在電影節上只放映2場:一場是評委和觀眾同時觀看;另一場是普通觀眾場。但是,當地華僑蜂擁而至,爭相觀看“來自祖國”的影片。由于觀眾實在太多,電影節組委會不得不加演了一場。影片打動了所有觀眾,包括評委、記者,尤其是華僑。一時間,“來自中國的影片出乎意料地使馬尼拉升溫”的報道壓倒了一切。
當擔任電影節國際評委的謝晉導演把《城南舊事》終于摘取桂冠這個令人興奮的喜訊告訴大家的時候,代表團全體成員都不約而同地歡呼了起來。大家情不自禁地握手、擁抱,連平時一向矜持的團長石方禹也按耐不住,緊緊抱住了我,幾乎讓我透不過氣來。
1月16日,頒獎典禮的當晚,以石方禹為首的全體中國電影代表團成員在一名高舉著五星紅旗的總統衛隊士兵的引導下徐徐步入會場。我行進在國旗之下,感到無比自豪。我做夢也不會想到,作為一名電影導演,竟能有這么大的榮譽,而且,最重要的是,這榮譽是和我的祖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注釋:
①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對臺工作的9條建議,即“葉九條”。
(本文選自即將出版的《口述上海——影人影事》一書)
作者單位: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 責任編輯:王亞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