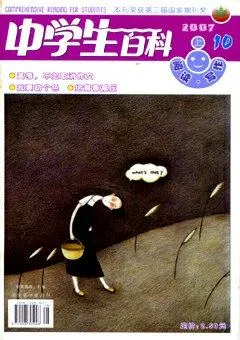在某個早晨醒來
不知道為什么,高中畢業后,我發覺自己好像總活在一種亦真亦幻的恍惚里。在剛剛過去的那個夏天,頭發像吃了肥料,一直長啊長。我不管,我由著它們。當然我也記得,曾經班里的女生說過,我的頭發是更適合像刺猬一樣張揚的,她們說那樣的我會好看一點。
一個人拿著喝空了的可樂瓶,走在街頭,總會想起了那些吹著口哨一臉壞笑的日子,有很多同學,很多朋友。那個時候,我們總是放肆地笑,雖然并不見得就是開心。花生說我注定是該傷感的,因為我總是看或者寫一些傷感的文字。他那么說的時候我就笑了,我讓他閉上他的烏鴉嘴,然后心里又在想或許他是對的。
說到笑,阿旺是不得不提的。我一直很嫉妒他每天都可以很單純地笑,因為他總是考慮得很少。雖然那個時候我們都說他笨,可我總以為“笨”一點就能多一點快樂的。那時候阿旺一踢進球就會擺個很白癡的pose,然后我就會叫他干脆挖個坑把自己埋了。我實在不想看到這個世上還有他這樣的白癡,可是現在卻突然很想看他踢球。離開學校那天,阿旺對我說:“你以后要為自己活好不好。”然后我就不以為然地笑。
他們說我笑起來的時候很好看,我想關于這一點我也是知道的,因為我常常喜歡對著鏡子不停地笑。其實我想說的是,我這樣笑的時候,比阿旺還要傻許多。不過照鏡子也不是我的專利,棒子還過分一些,他好像一有空就靠在窗口,對著鏡子不停地梳頭。每次我都朝他大呼小叫,說棒子啊,你那個樣子看起來真的像深宮里的怨婦。可是現在,我突然很想知道他的頭發是怎么梳的,是不是換了新發型。
我到底是個安靜還是聒噪的人,實際上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記得有一回,我坐在操場邊發呆,剛好被雨倩看到,她就說她從沒想過我會那么安靜。我像被人看穿一般,轉瞬就變了模樣,痞子似的笑起來,然后又對她嘰里呱啦一番,以便讓她把那個安靜的我忘掉。
走的時候大家約好了重逢的時間,可是我不知道那個時候有多遠,或者我那時已忘記了時間。一直以來我是個記性不好的家伙,可是很奇怪,我卻清楚地記得那些傷口還有寂寞,也許我的記憶用來填滿它們了,再也裝不下別的。
似乎我們誰都沒有說再見的,或許是真的知道可能再也見不到。我不知道世界為什么要這么大,時間為什么要那么長,讓那些原本美好的事從此傷愁淡淡。不知道學校的空地里被鋤光的草又長起來了沒有,走的時候那兒只剩下光禿禿的土地。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該背上挎包,然后在風里做出很惆悵的樣子,就像那些憂傷的畫。
我是個習慣走路的人,我總是認為走在路上更好,可以后的長街或許再也沒人陪我走。大概那時候我該問問路人是否愿意把我帶到別的地方。
我總是不停地笑著說時光晃啊晃,然后等我笑完之后就已經過了好多年。我一直很害怕蒼老。花生說他是不那么容易老的,他會保養得很好,在40歲的時候還會有20歲的容顏,可是我不知道等到他40歲的時候他是否還會那樣說。
編輯/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