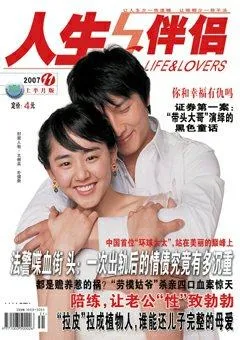和孩子一起打開心窗
下班回來,我在廚房里忙著做飯炒菜,滿頭油煙地將菜端上桌,客廳里的女兒卻不見了蹤影。原來,她在書房里翻箱倒柜——把碼得好好的書一股腦兒地扔得滿地都是,不知在翻些什么,叫她吃飯,她又不肯。我生氣地說:“媽媽忙了一整天,還要做飯,容易嗎?你看你,還把書弄亂了,想讓媽媽再忙些對不對?”
女兒站起來,大聲反駁:“我會碼整齊的,不用你管!”
下午在單位里遇到不順心的事兒,我的心還煩著呢,女兒的話讓我爆發了:“才這么小的孩子,就不用媽媽管了,嫌媽媽煩了是不是?”
那一頓飯,吃得很不愉快。自從孩子爸爸下縣里蹲點后,我的工作和生活忙得一團糟,加上女兒越來越叛逆,我的心情一直很煩躁。
晚上,女兒睡了,我把書架上和書柜里的書重新整理了一遍,也回顧了這段時間和女兒相處的情景。不知為什么,幼兒園的老師一直表揚女兒在班上表現不錯,可她回到家,卻喜歡和我對著干。“不用你管”,這句話她說得越來越多了。有一次,我在書房里加班,叫她好好在客廳練字,她卻在衛生間里玩起了水,說是洗鞋子,把衣服都給弄濕了;上個周末,她比我起得還早,踮腳開消毒柜,打破了一只湯匙一只碗;叫她不要亂跑,她卻趁我不注意跑到小區門口走來走去,讓我虛驚過好幾次……
我的耐性早被忙亂的生活給磨掉了,一遇到她給我添亂,心情就極度不爽,先把她批評一頓再說。她和她爸爸一樣不愛說話,簡簡單單的一句“不用你管”或一個白眼,就表達了她的態度。
聽我在電話里訴苦多了,朋友約我帶女兒到她家過周末。她和兒子的關系一向處得很好,讓我羨慕不已。其實,女兒小時候也挺乖的,但自從我一個人帶她之后,就不知道她心里想些什么了。朋友支開兩個小孩到房里玩,和我聊天。她身邊放著一盆洗好的栗子,她一邊說著話,一邊用鋒利的小刀往一只只栗子的尖頂上切十字。我好奇地問,煮栗子不是直接往鍋里放就行了嗎,怎么還要多做這一道工序?她笑了:“煮熟了你就知道了。”
屋子里飄著煮熟的栗子的清香,朋友盛了一碗出來,那栗子頂上都裂開了口,露出了金黃的果肉。用手剝開,放進嘴里,味道好極了。朋友挑出一只帶點黑色的栗子扔掉,說,栗子是好是壞,光看外殼是看不出來的,要是不切開口子,就很可能咬到壞的。人也是一樣,不說出來,誰也不知道對方在想什么。孩子做事也有自己的理由,但他們的想法和大人的不一樣,所以才會出現分歧。如果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又怎么能做一個善解人意的好媽媽?如果不讓孩子知道媽媽想什么,又怎么能讓孩子心甘情愿地接受媽媽的教育?
朋友指了指那些裂了口的栗子:剝開栗子,就知道它是好是壞,讓孩子把心敞開,就知道孩子這么做的原因了。有時間,多和女兒溝通吧。
朋友的話解開了我這段時間的心結。回到家后,我一直在考慮著該怎么樣和女兒交流。回想起來,我真的很久沒和她心平氣和地說過話了,除了教她應該干什么,不應該干什么。我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感受上,因為工作負擔的加重,因為兩地分居帶來的壓力,我竟變得自私到不顧女兒的感受。以前那個疼愛女兒、處處為女兒著想的我,與現在煩躁的我有了極大的反差,怪不得女兒的變化這么大了。想到此處,我心里充滿了愧疚。
接下來的那幾天,和女兒單獨相處時,我都主動把牽掛著的工作放到一邊,逗女兒說說話。她提起幼兒園里的趣事,說到有趣的地方就咯咯地笑起來,原來說到她感興趣的事,她也是有不少話要說的。我告訴她:“以后要做什么事,主動跟媽媽說一聲,只要是有道理的,媽媽都會讓你試試的。”
轉眼又是星期五。吃完晚飯,我還在廚房里洗碗,女兒進來扯著我的衣襟,說想去大門口看看爸爸回不回來。我說,爸爸這個星期不回來,他晚上會打電話給我們的。她搖搖頭:“要是爸爸想給我們一個驚喜呢?”
我笑笑,這么小,就知道用驚喜這個詞了。她接下來說道:“我知道,媽媽和我一樣,都想爸爸。”我心底有塊柔軟的地方被觸到了,原來,她偷偷地跑到小區門口,是想等爸爸回家啊。她這么小就懂得體諒我的心情,而我呢,卻如此粗暴地對待她。
后來,我才慢慢弄清楚,她看到我忙忙碌碌,想幫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務,可是因為小,卻越幫越忙,被我說了一頓后又不服氣,所以才會賭氣說出不要我管之類的話來。知道原因后,我在做家務時,主動給她分派任務,比如擇擇菜呀,看看時間,擦擦桌子啊,她都很樂意地去干。至于洗鞋子拿碗之類的事,我告訴她,她還小,這些事情還不會做,長大了就可以一個人干啦。
在朋友的指點下,我與女兒的關系變得融洽了。她本來就是一個懂事的孩子,當我尊重和理解了她的想法,并把我的感受告訴她之后,她就不再自顧自地去做讓我煩心的事了。原來,“叛逆”只是我站在個人的角度,戴著有色眼鏡看她的結果。朋友說得對,每個人心里都有不同的想法,如果隱藏起來,就會產生誤會甚至隔閡。家長與孩子也是如此,只有和孩子一起打開心窗,讓彼此的心靈變得敞亮,才能減少誤解,正確地引導孩子健康成長。
編輯 /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