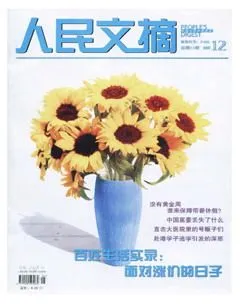抗戰老兵的3239個鮮紅掌印
距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沈陽燃起侵略的戰火,76年過去,硝煙雖已散盡,而當年風華正茂的數百萬中華抗日將士,經歷漫長歲月的戰爭、病痛,幸存下來的均垂垂老矣,并日漸凋零。留下他們的手印,就是留住了一段不能忘卻的歷史——
留下手印是最好的歸宿
在今年9月18日到來之際,我們來到四川大邑縣建川博物館聚落“抗戰老兵手印廣場”。明晃晃的陽光下,3000多個掌紋清晰、手指嶙峋的鮮紅手印“V”型呈現,一如整齊受閱的雄師。他們的“主人”,是當年參加抗戰的老兵。年齡最大的已過百歲,最小的也八十多了。“已征集到3239位抗戰老兵的手印,預計總數將達到8000個。”建川博物館聚落負責人樊建川說,這些老兵的手,曾堅強有力,握住了中華民族的希望,但握不住流逝的時間,總有一天,他們會離開。留下他們的手印,就是留住了一段不能忘卻的歷史。
今年在“紀念七七全面抗戰70周年座談會”上,這些老兵們一如當年挺立著身軀,排隊在雪白的宣紙上留下自己的手印。“場面非常感人。”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秘書長張耀霞說,有個老兵的手,當年扣扳機的食指已經彎曲變形,怎么都印不上去,不肯放棄的他最后把手翻過來,手背印了上去;而一個老兵則打趣說:“以后不用去公墓了,留下手印就是最好的歸宿。”
成都,望江樓公園里,80歲的老兵周棟梁正悠閑地喝著茶。朋友提醒記者說:“看周棟梁的滿頭青發”——白了30多年,最近2個月全變青了。“高興嘛。”周棟梁說,去年9月,在手印廣場留念時,竟然遇見9位中國遠征軍新一軍的戰友。一同參軍,分別60余年后再相逢,昔日的熱血青年早已容顏大變,認不出來了,但老戰友們甭提多高興了。他們相互抱在一起,老淚縱流。
除了激動,也有感慨。樊建川說,開國上將呂正操101歲時已行動不便,他是在床上顫抖著摁下手印的。
廣場上,手印猶在,但新四軍老兵董紹祺已永遠離開了。“他是在摁完手印3天后去世的。”手印廣場工作人員唐兵說。當時他正興高采烈地打電話給董紹祺老人的兒子董小祺,說手印已塑上去了,電話里卻傳來哀樂聲。
女兵的手印緊挨著丈夫
在巍巍壯觀的老兵手印廣場上還有特殊的影跡,那是幾個女兵的手印。張金鑾的手印緊緊挨著丈夫王哲夫的,一如革命時代相依相靠。
張金鑾和王哲夫都是河北省定縣東湖村人,高小同班同桌。1941年,兩人一起進入冀中軍區抗屬子弟中學。這個學校是八路軍辦的,進入該校就意味著光榮參軍。
1943春天,原抗屬中學學生分成三路,從晉察冀邊區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一路上,王哲夫沒見到張金鑾,也沒聽到點滴消息,心里沉甸甸的。到了冬天,他意外收到張金鑾寄來的“寶貝”:一雙陜甘寧邊區工廠做的軍鞋,鞋底鑲著一層薄薄的生牛皮,鞋里還藏一封信。“是寫給我的,并代問另一個同學好。”王哲夫想,既然信中提到另一個同學,不如把鞋給了他,卻遭到“批評”:“傻瓜,給你的我怎么能要,鞋是定情物啊。”周圍戰友都在取笑,王哲夫紅著臉離開了。
1944年秋天,張金鑾給王哲夫寫來第二封信,說得了急性盲腸炎,一個人在窯洞里住院,特別想他去看望。心急如焚的王哲夫把信給指導員看,指導員哈哈大笑:“體病好醫心病難醫,快去啊!”
第二天早上,王哲夫胡亂扒幾口糜子飯就出發了。一見面,躺在床上的張金鑾騰地一下坐起來,未曾開口,眼里已噙滿淚花。一路上想到許多話,王哲夫卻一句也說不出來。沉默,傻坐。
捅破最后一層紙的還是一封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而內戰火藥味漸濃。秋末冬初,抗大七分校校部,一、三大隊和女生隊都準備開赴前線。這時,張金鑾給王哲夫寫了一封直白的情書。“再不表白,恐怕錯過機會,遺憾一生。”張金鑾說,信中寫下了“天長地久日月相依、海枯石爛永不變心”的句子。王哲夫馬上提筆,回信只有一句話:“同意戀愛!”
1949年12月12日,西安終南山下留村,6尺白床單往床上一鋪,沙場伉儷終于結婚了。
說起安仁鎮,王哲夫覺得真有緣分。隨部隊進入四川時,他在安仁住了整整1年,經常在安仁糖廠的操壩上給戰士們講革命形勢。有一天,講著講著,太陽突然火辣起來,于是轉移到大樹下繼續講。兩分鐘后,剛才講課的地方發生了爆炸……離開50多年后,王哲夫再來尋找當年的“救命樹”,卻怎么也尋不著,無限惆悵。“不過,能把手印留在安仁,也是極大的安慰。”
(袁 娟摘自《四川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