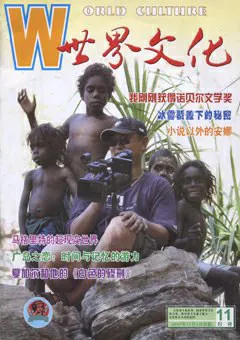小說以外的安娜
上個世紀50年代,國外某組織曾就“你最喜愛的小說”做過一次世界性的調查,結果是,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名列榜首。從那時起到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這部小說仍然是讀者最喜愛的文學作品之一。之所以如此,除安娜這個形象生動、感人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安娜作為文學形象,具有堅實的現實生活基礎。“安娜現象”在小說以外的現實生活中,也是時而可見的。我們在這里所要講的富于傳奇經歷的克呂德內夫人,就正是這樣一位現實生活中的安娜。
嫁給一個卡列寧式的丈夫
克呂德內夫人原名朱麗·巴爾布,1764年出生于當時的俄國波羅的海沿岸的里沃尼亞省的里加,一個有著古老德俄貴族世系的家庭。父親是哲學家和共濟會會員,熱愛藝術,是文學事業的贊助者,母親是虔誠的路德派教徒。
朱麗18歲時,和比她大15歲并曾兩次結婚又都離婚的俄國外交官克呂德內男爵結了婚。男爵是個有頭腦、有教養的高尚的人,性格沉靜,也不乏熱情,但卻是一個卡列寧式的人物,對于自己的妻子,他與其說是愛人,倒不如說是父親。正像奧布朗斯基對妹妹安娜所說的那樣:“你嫁給一個比你大20歲的人,你們之間沒有愛情,也不可能有愛情。這是一個錯誤。”朱麗結婚前曾跟著名的巴黎芭蕾舞師維斯特里學過舞蹈,所以,這位隨外交官進入18世紀最出色的歐洲上流社會的夫人的主要興趣和活動就是業余演出披巾舞。德國著名作家斯塔爾夫人曾在她的小說《黛爾芬》中以克呂德內夫人為原型描繪了黛爾芬跳披巾舞的形象:“優雅和美麗從未對一大批人產生過這樣突出的影響……她開始輕快地舞蹈,把一塊印度披巾圍在自己身上,顯出她身體的輪廓,她垂著長發的頭往后仰,使自己構成一幅十分媚人的畫面。”
一年以后,這位夫人跟隨擔任威尼斯大使的丈夫來到這個當時最放蕩的城市,過上了眼光繚亂的生活,并且成了她丈夫的私人秘書亞歷山大·斯塔克杰夫暗戀的對象。這位秘書陪同他心中的情人到處游逛,欣賞美麗的自然風光之后,用一封信向自己的上司坦白了自己的愛情,而這位卡列寧卻不知出于什么想法,把信拿給妻子看了。單戀的男人離開了,但他那熾熱的感情在這位美麗的少婦心中喚醒了強烈的愛和被愛的愿望。她想使她的丈夫成為她熱烈的愛情的對象,可是,這位卡列寧式的父親般的丈夫,對她熱烈的感情只想加以抑制。這就把她推向家庭以外。她在所有的舞會上任性地、毫無顧忌地賣弄風情。頻繁的舞會和披巾舞的演出把她的身體累垮了,她的神經變得衰弱,肺部受到感染。這時他們在哥本哈根。她的丈夫讓她到南方地中海岸上安靜溫暖的地方去度過1789年的冬天。
渥倫斯基們
而她卻急匆匆地趕到了巴黎。在這個著名的文化大都市,她結識了一些大作家,產生了閱讀的興趣,并遭遇了她的“渥倫斯基”——一個青年軍官德·弗雷熱維爾。經過一番斗爭,她依從了他,并聽從他的勸誘,違反她丈夫的初衷,在巴黎一連度過了兩個冬天。
路易十六逃跑未遂后,巴黎不再是克呂德內夫人安全居住的地方,她讓“渥倫斯基”假份男仆,倆人逃離巴黎,來到漢堡,仍以主仆身份同居,甚至在她丈夫到漢堡接她回哥本哈根時,她仍不肯和她心愛的仆人“渥倫斯基”分手。夫妻倆大吵了一架,丈夫提出離婚。這正是托爾斯泰的安娜百般欲求而不可得的,可這位“安娜”卻不顧女人的自尊,竟然撲倒在丈夫的腳下,請求寬恕。她的父親般的卡列寧丈夫,作為一個“有修養的、高尚的”人,寬恕了她。但她卻并未遵守自己的諾言,而是繼續在歐洲各地游逛,過了10年18世紀末那種放蕩的貴婦人的生活。
在這10年中,她參加了一個又一個舞會和宴會,在業余演出中跳斯塔爾夫人描述的那種披巾舞,并頻繁地更換她的“渥倫斯基”。
1800—1801年,她以俄國大使夫人的身份住在她丈夫任職的柏林。她的不守時和古怪的脾氣,使她在威廉三世這個處事井井有條的宮庭里并不特別受歡迎。雖然她那單純質樸的態度10年前曾使人無法抗拒,她那表情豐富的面容和嫻雅的風度向來招人喜愛,但她知道,她從來就不是一個美人,何況她的面容和膚色也不像年輕時那樣鮮嫩了。因此,她就設法靠大膽的打扮來引人注目,靠打份得異常妖冶,甚至不穿什么來造成轟動。在這期間,她為了一次新的愛情再一次離開了她的丈夫。
1801年秋,她對斯塔爾夫人作了長時間的訪問,產生了當女作家的愿望。不久,她在巴黎聽到了克呂德內死亡的消息。她非常震驚,心中充滿悲痛和悔恨,閉門不出,也不接待任何人。她一直想再次回到他跟前,減輕多年來給他造成的傷害,報答他始終給予的寬宏大量。這樣的機會永遠失去了。
但她不可能長期過那種深居簡出的生活。她開始寫小說,并用一個非常巧妙的宣傳策略,使她的長篇小說《瓦勒麗》于1803年底出版,大獲成功。
皈依宗教
1805年,由于幾個偶然事件的啟示和某種內在的傾向,克呂德內夫人突然皈依宗教,成了熱忱的基督徒。她過去的整個生活在此時滿懷宗教熱情的她看來,都是錯誤的。從這時起,她將年輕時在愛情上表現的那種熱情都傾注到禮拜和行善上了。她成了基督教各種謙卑美德的典型。為了幫助受苦的人,她爬到最臟的閣樓上去。有一天,她看到一個女仆因為主人讓她出來掃地而在街頭哭泣。這位高貴的夫人就拿過掃帚,自己掃起人行道來。一位宗教界的領導人,在對她進行過仔細觀察后寫道:“她對一切人的痛苦和需要表現了最深切、最純正、最積極、最無私、最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同情。”
她甚至要對沙皇施加影響。1815年6月4日晚上,她不顧副官的阻攔,不經通報強行來到沙皇亞歷山大面前,他們倆人在小房間里呆了3個鐘頭。當她離開時,亞歷山大眼中充滿淚水,心頭十分激動。不久,他就完全處于她的影響之下了。他們倆人經常把自己關在屋里,一連幾小時地祈禱、讀《圣經》,討論神學問題。6月18日,拿破侖在滑鐵盧大敗,亞歷山大立即出發前往巴黎,并約好克呂德內夫人隨后跟去。9月初,在香檳省的美德營舉行15萬俄軍大檢閱。一清早,沙皇就派自己的馬車去接她,讓她像一個上天派來把他的軍隊引向勝利的使者那樣參加檢閱。對于當時的情形,法國著名文藝批評家圣伯夫曾根據目擊者的描述記錄如下:“她光著頭,或是戴上她那經常掛在手臂上的小草帽;她那仍然很漂亮的頭發梳成辮子垂在肩上,前額有一綹卷發搭在額上。她穿著一件樸素的黑袍(其式樣和她的體態給人以雅致的感覺),腰間系著一根簡單的帶子。她就這樣打扮,在黎明時分來到美德營,在祈禱時站在吃驚的軍隊面前。”
幾天以后,克呂德內夫人修改了由沙皇亞歷山大起草的俄、普、奧三國國王協議草稿,并給這個協議起了個名字:神圣同盟。
遺憾的是,這是一個反動的同盟。
走向底層
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她的宗教信仰變得更加真誠和狂熱,并努力把這種信仰變成行動。她心中唯一的愿望和生活的唯一目標就是幫助窮人和病人。她給窮人講道,創建教會,宣告天國即將來臨。可是她沒想到,過去那些把她當作宮廷貴婦笑臉相待的王公貴族、權威人士和所有的大人物,看到她走向底層,面向人民群眾,就本能地把她當作敵人。有一次她從瑞士的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講道傳教,幾乎是進行了一種瘋狂的宗教勝利游行;之后她再次進入這個國家時,卻被從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中驅逐出來。巴登發生災荒時,她慷慨大方地進行慈善救助活動,憲兵把她的房子圍住,驅散了向她謀求幫助的人。她設法通過阿爾薩斯進入法國,被警察押送到俄國邊境,在那里由威騰堡的警察交給巴伐利亞的警察,又由巴伐利亞的警察交給薩克遜的警察,最后將她交給了她本國當局。從此她永遠失掉了沙皇的寵幸。因為她所理解的基督教只能引起統治當局的反感。在她散發的宗教雜志和小冊子中,她談到了社會上的壞事,窮人們的說不完的痛苦和統治者對他們的不公正的壓迫,這些言論都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而她本人則被視為革命者。她甚至還對希臘獨立戰爭表示熱烈的同情,宣稱作為神圣同盟的發起人亞歷山大皇帝有責任站在反對土耳其圣戰的前列。在這個問題上,她雖然不能和拜倫相比,可是考慮到她個人的經歷,還可說是勇氣可嘉的。
被沙皇拋棄之后,克呂德內夫人離開了彼得堡,開始過一個真誠的傳教士的自我懲罰的苦修生活。她經歷了種種艱難困苦,盡一切可能減輕別人的痛苦。1824年,當她遠道到克里米亞傳道時,她永遠地離開了那些窮苦的人們。
克呂德內夫人曾在談到日內瓦的貴婦人時說:“她們既沒有品德上招人喜愛之處,也沒有罪惡上的迷人之處。”后面這句話用在她本人身上倒也合適:她那些放蕩的年月,那些頻繁更換情人的年月,從她身上放射的迷人光彩,無疑是含有罪惡的。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是愛情的精神守望者。她以生命和激情,以她對愛情的真誠而不可動搖的信念,在現實生活中尋求愛情的神圣和純潔。她是愛的天使。而克呂德內夫人卻只能說是愛的撒旦。可是,當她晚年為救援窮苦人而受苦,到處被統治者所驅逐,并因此而死時,我們在她身上也看到了道德的閃光。不管怎么說,此時她是真誠的,她值得我們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