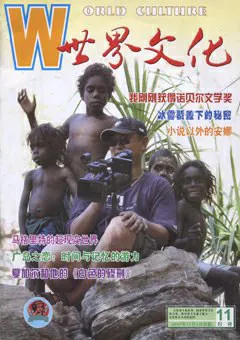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強力集團”代言人 工程兵將軍
在一些音樂著作中,在介紹俄國19世紀60年代對俄國民族音樂的發展有深遠影響的“新俄羅斯樂派”——“強力集團”時,往往提到一位庫宜,也譯顧宜或桂宜的“集團”成員,這都出自我國臺灣省譯者之筆,譯法各有千秋,并非錯譯。但我們大陸的讀者甚至音樂愛好者見到此“三宜”,一定會如墮五里霧中,不知所指何人。筆者現在要介紹的就是此“三宜”在大陸已約定俗成、讀者較熟悉的譯名“居伊”的俄羅斯作曲家。
論音樂創作的藝術成就,居伊稍遜于“集團”的其他4位成員,但他對“集團”的思想建設、促使“集團”樹立先進的創作原則,作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至于在創作的體裁和數量上,他除歌劇外,還有二百五十多首歌曲與樂曲示人,在“集團”里是名列前茅的,這也許與他的高壽有一定關系,他在78歲高齡時還寫了兒童歌劇《小傻瓜伊凡奴什卡》和《靴子里的貓》。
居伊是一位杰出的俄國作曲家,但他并非俄羅斯族人,他的父親是法國軍官,母親是立陶宛人,因此他的姓名頗具西方色彩——愷撒·居伊。1835居伊生于立陶宛的首都維爾紐斯。他從小就喜愛音樂,10歲時開始學音樂,15歲時在波蘭作曲家、指揮家、民族歌劇創始人莫紐什科(1819—1872)的指導下學習音樂理論與作曲,但學習不長時間就隨父母遷居彼得堡。1851年,他先在工程中心學校,后入軍事工程學院學習,1857年畢業后留校任輔導教師,1878年起任副教授,1891年擢升功勛教授。先后講授地形學、筑城學課程,1877—1878年俄土戰爭期間,居伊作為筑城學專家被派往戰地指導俄軍陣地工事建筑,1904年獲工程兵將軍銜。
以上簡歷說明了居伊的主業是軍事工程的教學與實際施工,只是他對音樂的愛好以及結識了鼎鼎大名的作曲家達爾戈梅斯基、“強力集團”領袖巴拉基列夫和杰出的藝術評論家、思想家斯塔索夫,在他們的影響與指導下投身音樂創作,最終成為“強力集團”又一位杰出的“業余”作曲家。
1856年居伊加入“強力集團”后積極推動俄羅斯音樂的進步革新運動。1864年起他在當時很有影響的報刊《彼得堡公報》、《呼聲報》、《公民報》、《新聞與市場報》乃至國外報刊發表音樂評論文章,1885—1888年還參加《音樂評論》的編輯工作,1889—1895年又參與《演員》雜志的音樂專欄工作。19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居伊音樂評論活動最光輝的時期,他經常以“新俄羅斯樂派”名義發表文章,筆鋒犀利,戰斗雄辯的鋒芒直指學院派領導機構的因循守舊、官僚主義的不思進取以及無視祖國年輕藝術的做法。居伊斷言,推動音樂進步的必將是俄羅斯作曲家,“音樂將會由于我們而振興并開創其新紀元”。這段時期,居伊的音樂評論活動對“集團”的思想建設和“集團”成員們的創作起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可是與此同時,由于其思想觀點的局限性以及“集團”主導思想中片面性的影響和個人偏激,居伊對學院派的抨擊有失公允,而且全盤否定18世紀古曲主義音樂,否定德國作曲家瓦格納、意大利作曲家朱塞普·威爾弟以及19世紀其他一些卓越的作曲家的作品。之后,他評論的鋒芒有所緩和,但又摻和著保守性的偏見,從而影響他正確評價穆索爾斯基和鮑羅廷的優秀作品。1900年后居伊停止了評論活動,只是偶爾發表一些文章。
居伊貶斥古典主義卻對西方的浪漫主義情有獨鐘,甚至超過對俄羅斯民族傳統的喜愛。他的創作頗受浪漫派大師舒曼、肖邦以及法國歌劇樂派的影響。居伊豐富多彩的作品中最有價值的是室內聲樂抒情曲,他最優秀的浪漫曲,如根據普希金詩篇《皇村雕像》、《焚毀的信》,詩人邁科夫(1821—1897)的《靜夜里想什么》、《風鳴豎琴》、《痛不欲生》譜寫的浪漫曲無不洋溢著詩情畫意,其精雕細刻的旋律令人傾倒。另一方面,居伊根據法國詩人繆塞、大文豪雨果的詩而譜寫的浪漫曲,在表現激情時顯得過分夸張,表現柔情則往往流于沙龍式的輕薄。
除浪漫曲外,居伊的歌劇創作也受到新俄羅斯樂派的好評,其主要作品有1857—1858年的《高加索人俘虜》、1859年的《閥閱子弟》、1861年起寫了7年的《威廉·拉特克里夫》(根據海涅敘事詩)、1875年的《安哲羅》(根據雨果的同名劇)、1889年的《海盜》、1898年的《撒拉律》、1900年的《瘟疫流行日,華宴盛開時》、1903年的《菲菲小姐》、1907年的《瑪蒂奧·法爾康奈》(根據法國短篇小說大師梅里美的同名小說、詩人茹科夫斯基的譯文譜寫)、1909年的《上尉的女兒》(根據普希金的同名小說譜寫)。
《威廉·拉特克里夫》于1869年首演時,“集團”最杰出的作曲家里姆斯基-柯薩科夫在評論中寫道:“《威廉·拉特克里夫》是一部十分出色的作品,也如達爾戈梅斯基的《美人魚》、格林卡的《魯斯蘭》和《為沙皇獻身》(即《伊凡·蘇薩寧》)一樣,定將在藝術殿堂里占有當之無愧的席位……”然而這部歌劇并沒有獲得真正的成功,因為其陳舊的浪漫主義題材及其抒情的音樂語言與劇中人狂熱的激情很不相稱。同樣的缺點在其他歌劇如《安哲羅》、《撒拉律》中也有表現。在他晚年作品中,如《瘟疫流行日,華宴盛開時》及《菲菲小姐》等歌劇中表現出作曲家對歌劇中的真實主義的濃厚興趣。真實主義是19世紀末意大利文學、歌劇和造型藝術的現實主義流派,接近自然主義,其特點是描寫貧民和農民生活,著重刻畫人物的感受和戲劇性沖突,有強烈的感情色彩。
由于對西方浪漫主義的偏愛,居伊大量的器樂作品中大部分是舒緩風格的鋼琴小型曲,因此,著名的俄國音樂評論家、莫斯科音樂學院、彼得堡音樂學院教授,與“強力集團”有過激烈論戰的拉羅什(1845——1904)稱其為“舒曼派的作曲家”。
居伊在他最后的歲月里,由于結識了女音樂教育家多羅曼諾娃而萌發創作兒童音樂的熱情,先后創作了13首童聲女聲合唱曲、數首兒童組曲獻給教育家,還寫了4部兒童歌劇《雪勇士》、《小紅帽》、《靴子里的貓》和《小傻瓜伊凡奴什卡》(或《伊凡勇士》)。
最后必須指出,達爾戈梅斯基于1866年根據普希金同名詩劇創作的歌劇《石客》以及穆索爾斯基1874年根據果戈里中篇小說《狄康卡近鄉夜話》創作的歌劇《索羅欽斯克市集》(有譯《索羅慶采市集》),都由于作曲家英年早逝,未能完成,但都成了俄羅斯歌劇中傳世之作,這與居伊的辛勞是分不開的。前者由居伊與里姆斯基-柯薩科夫共同續成,后者由居伊、里亞朵夫、里姆斯基-柯薩科夫續成。
居伊在音樂創作方面的成就雖然稱不上樂壇巨擘,但也是斐然卓著,尤其是他三十余年的音樂評論著述雖然在觀點、立論上有偏頗,但瑕不掩瑜,對俄國民族音樂的發展,對捍衛“強力集團”的創作原則還是起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因此后人稱其為“強力集團”的代言人。
最難能可貴的是,同另一位“集團”成員鮑羅丁一樣,鮑氏是化學和醫學領域的精英而以作曲家名垂青史,而居伊是軍事工程學的專家,榮獲工程兵將軍銜時已年屆古稀,但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從事音樂創作,直至耄耋之年仍不擱筆(居伊死于1918年3月),這也是居伊作為“業余作曲家”留給世人的一個光輝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