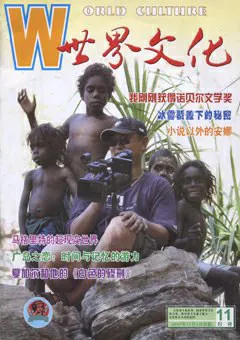廣島之戀:時間與記憶的游歷
上世紀50年代末,戰后法國開始了一場被稱為“新小說”,“新浪潮”(及“左岸派”)電影的藝術實踐。文本和電影第一次互為彼此而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浪潮”電影對傳統電影的高度自覺與革新,其創造性的試圖通過膠片傳遞出在文學哲學領域里被反復演繹著的現代主義氣質,在這個意義上“新浪潮”可算作名副其實的“作家電影”。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是新小說派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與“左岸派”導演阿倫雷乃合作的作品《廣島之戀》。
這部電影完成于1959年,阿倫雷乃延續了其對反戰題材的關注,然而,與其前兩部反戰作品《格而尼卡》及《夜與霧》不同,《廣島之戀》試圖將對戰爭的關注縮回到人物心理層面之下,甚至更溫情——愛情之下。
在這個故事里,法國女人與日本男人沒有自己的名字,他們呼喚對方“拉維爾”及“廣島”——兩座因為同一場戰爭而建立起聯系的城市。他們在戰后某一日的廣島相識相戀,二十四小時的愛情與碎片般關于戰爭的記憶互相打斷,再互相被喚起。
我們可以將電影中頻繁出現的蒙太奇看作兩種時間——物理時間及心理時間(或曰思想時間)的彼此作用,考慮到無論是在戰爭之中還是之后,已經無所謂純然的物理時間,它在戰爭及政治語境下被賦予了承載宏大敘事的口吻,時間不再天真無邪的等待著敘事,哪怕一個單純的數字,比如1949年,對中國人而言它再也不會單純的只表征物理時間了,我們不妨也將這樣的時間稱為宏偉時間,
我試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的,便是這部影片中宏偉時間是如何將心理時間撕裂,強暴的;以及心理時間在宏偉時間中是怎樣一再厭棄自身,否定自身的,而呈現這二者的目的,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存在主義的思考緯度。
如上所說,純然的“物理時間”在這部電影中是無足輕重的,它從未被標示出來。但“宏偉時間”卻通過“原子彈”投下的“那一天”,戰爭結束的那個“夏天的早晨”,顯示出其在歷史時間流中“硬梆梆”的存在。在這樣堅硬的毫無生氣的語境下,個人,兩個相愛的戀人的闖入,無疑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召喚出我們的人本意識。而當二人的心理時間通過性愛和愛情關系被放置在一起,更是加劇了愛情(某種意義上代表了生命)與戰爭的矛盾。
影片的開始,原子彈爆炸,升騰起巨大的蘑菇云,畫面隨即出現的是男女主人公赤裸擁抱著的肩膀,鏡頭里只有軀體,沒有臉,顯然是在提醒,這有可能是任何時間任何兩個人的身體,而肩膀上的汗珠,以及兩個軀體間的緊摟動作,令人“既感到清新,又圖生欲念”。
杜拉斯選擇從這樣一個場景進入該故事,選擇從傳遞“清新”與“欲念”矛盾交織的心理體驗入手,而不是從一個物理場景或一個宏大時間中進入,顯然是在提醒我們重視影片中活躍著的記憶及意識。關于這一點我們還可以發現主人公在電影中始終是鮮有行動的,他們沒有名字,只是“他”和“她”,杜拉斯沒有使用任何詞匯去描寫他們的外貌,面孔或姿態。刻意使其表面身份顯得游離,“他”和“她”既可能是戰爭過后任意一個廣島男人和法國女人,但又因其記憶而永遠區別于他人,這種區別是創傷性的,彼此隔離的,是宏大時間之下個人不可復制的一次性即永遠完成了的“體驗”(而非經驗),這在下文進一步得到加強。
他和她的初次對話,是他們慢慢步入記憶的過程。
法國女人不斷重復說到“在廣島,我看見了,我什么都看見了”。鏡頭隨之指向戰爭博物館,并穿插了原子彈毀壞廣島的紀錄片,女人的聲音“平靜,毫無生氣,像背誦似的”,不斷重復“看到了”,而日本男人自始自終的回答都是——“你在廣島什么也不曾看見,一無所見”,男人的否定——須注意這句話,“你什么都沒看見”并不等同于“廣島什么也沒發生”。在通常情況下對他人記憶的否定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而日本男人在這里的一再反復的否定,恰是在揭示他心里意識中某處印記,這便是戰爭創傷。否定這處記憶,正是為了強調這一切的發生,以及它永遠的發生了,它被放置在過去完成時中。男人還特別否定了這跟復制品、照片、紀念性雕塑都不同——因為發生的這一切具有“一次性”的意義,這一點不同于對其的影音記錄,而關于它發生過的最真實的證據是它在人們記憶中的痕跡。
我們應該特別關注,影片一開始出現的幾乎全是否定與懷疑,男人與女人堅定的互相否定(“這一切,全是你胡編亂造”),女人對廣島游客的否定(他們“僅僅是哭泣而已”),對戰爭紀念性建筑的否定(“盡管人們有時會對它們一笑了之”),這向我們揭示了心理時間是如何將個人記憶隔絕成為一個封閉體的,這個自足的記憶空間的存在,正是起因于宏大時間解放了心理時間,恰是因為心靈看到的這一切使其受到足夠的震憾,以致其無法再正常的去思維,此時心理時間便與物理時間脫鉤,而脫鉤后的心理時間只能自我分化,于是便在體系內自我解釋自我否定。
由此出發,在回憶完一切以后,法國女人接下去說:“我記憶力很好,但我會遺忘一切”,“和你一樣,我忘記了”,然而她卻又繼續沉入其中想象著“地面溫度將高達一萬度”“整個城市將被從地面揭起”“四名大學生情同手足,一起在等待傳奇式的死亡”,這便是心理時間在自身體系內的循環,這遠非自足閑適的過程,而是充滿矛盾的,每當心理時間被拉回為過去時時,記憶便條件反射般的拼命掙脫,而掙脫的結果是心理時間自身也被撕扯成越發尖利的碎片。
法國女人關于戰后廣島的記憶,隨即被另一段1943年內韋爾的記憶橫加插入,宏大時間的線形鏈條徹底被打亂,心理時間不僅將記憶變為共時性的平行的存在,記憶與記憶之間還互相提示彼此串聯。當男人熟睡時,法國女人“注視這個日本男人的雙手時,猛然間,一個年輕男人的軀體浮現在他躺著的位置上,取代了他”,心理時間與宏大時間的接口處是如此殘忍——由初戀情人的尸體而進入,而記憶中細節處更是用了放大鏡在觀看,“這只手因為臨終的痙攣而抖動”。
從這時的對話開始,法國女人第二次提及她的家鄉。
對話呈現于文本的樣子便是任由記憶碎片在心理中游走的過程。記憶的碎片是流動的,仿佛某種帶有生命性的東西,它在心理時間中自我持存,即使偶爾的沉寂也不過是暫時的休眠,在內韋爾發生的一切并非通過法國女人完整精確的敘述來展現,通過多處拼接我們得知:她親眼目睹初戀情人——一個德國士兵,被她的法國同胞殺死,而她自己則因為跟“國家的敵人”戀愛,被剃了頭囚禁在地下室,受盡歧視。
關于心理時間與記憶的討論,我不再用之后的文本再加證明,因為我們可以從主人公4次交談中找到某種類似于格式塔心理的對應結構。關于整部電影,我最后想說的是,與其說杜拉斯和阿倫雷乃是在講述一個法國女人與兩個男人間的愛情,不如說是講述其記憶在心理時間中的一場游歷,正如上文所示,這樣的游歷不是一帆風順的,然而卻是高度哲學性的,他試圖喚起某種對真實的洞察,記憶的引入,是想揭示一種更純粹真實的心理情感。這便回到了關于他真正想說的東西上:關于生命,愛情,戰爭,時間的哲學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