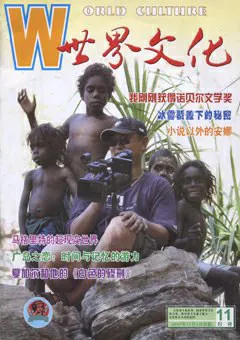體悟法國大革命真諦
悲慘、血腥、殘暴,抑或瘋狂?讀罷《桑松-劊子手世家傳奇(1688-1847)》一書,不由得人們要發(fā)出如此的感慨。歷史的巧合或是機緣,使得桑松家族走上了以劊子手為職業(yè)的道路,而在七代人之后,又戲劇性地終結(jié)了這個家族的不幸命運。
作者貝爾納·勒謝爾博尼埃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以桑松家族七代人的生活經(jīng)歷為主線,為我們展現(xiàn)的不僅僅是這個家族和劊子手這個職業(yè)的不幸,更重要的是,通過他們作為歷史見證人的目光,反映法國17世紀末到19世紀中期這段歷史中發(fā)生的重大事件:王權(quán)的隕落,啟蒙思想的醞釀和興起,大革命的爆發(fā),紅色和白色恐怖時期,帝國的創(chuàng)立和滅亡…… 這段歷史既跌宕復雜、波瀾壯闊,又充滿了激蕩瘋狂、腥風血雨,給后人留下了諸多耐人尋味的課題和慘痛的歷史教訓。尤其是本書作者大量援引法國大革命前后及其進行過程中的重要人物的言論和同代當事人的佐證,再加上桑松本人的日記(他雖然不能算是個文人,但是,也許與他的職業(yè)有關,他的眼光和思考卻往往超常的犀利和客觀),這些第一手材料為我們理解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真實可靠的信息。《桑松-劊子手世家傳奇(1688-1847)》,它首先是一部史書,是以一種特殊視角反映法國大革命的本質(zhì)和真相。其次,它也是一部刑罰史,反映法國中世紀以來刑罰的演變和興衰,尤其是斷頭鍘作為執(zhí)刑工具和刑罰的產(chǎn)生及興衰。再其次,它也不啻為18世紀至19世紀活脫脫的巴黎市井圖。本書跨越的時間和空間,特別是本書第五章展現(xiàn)的18世紀末巴黎經(jīng)濟、文化、社會和政治生活全景,其中不乏詮釋法國大革命暴發(fā)的方方面面的相關因素。巴黎特有的眾多人口,成分的復雜,雜亂的生存環(huán)境,比較縱容的道德風尚,發(fā)達的商業(yè),促使各行各業(yè)、各色人等奔忙于緊張的白天,也樂于享受活躍的夜生活。這一切構(gòu)成了巴黎的魅力和誘惑。漫步巴黎城,“每走一步,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一種新的氣氛,映入眼簾的要么是豪華的奢侈品,要么是最令人厭惡的污穢。這使得您不得不把巴黎稱作是最神奇又最骯臟的、最芳香又最惡臭的城市。”今人只是知道“巴黎是香水和時尚之都,最具魅力的花花世界”,有誰會想到歷史中的巴黎曾有這般不堪入目、不堪入耳、不堪入鼻的景致。此外,巴黎有多少個行業(yè),就被各個特有的風尚和習俗劃分成多少個小村落。城中有貴族和富人區(qū),也有平民區(qū)。再走遠一點,穿過一個小鎮(zhèn),就像到了另一個國家。如:蒙馬特、圣-拉匝爾和圣-洛朗區(qū),主要是紡織品生產(chǎn)地;夏佑區(qū)集中了鐵匠鋪和紗廠;魯爾區(qū)聚集了揀破爛兒的;圣-安托萬區(qū)集中了家具廠家;圣-馬賽爾區(qū)則集中了染坊、鞣革廠和毛刷廠。巴黎的咖啡館和酒館是法國的特有文化,特有景觀,它們不僅是人們休閑消遣的地方,更是各行各業(yè)、社會各階層,政治家、哲學家、文人學者、知識分子、兵工學商樂于聚會、交談、交友、評論時事、甚至是密謀策劃的場所。且看法國大革命同代人費里埃侯爵給我們提供的生動寫照:“我們無法想像在那里匯聚的各種各樣的人,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舞臺……那里,一個人在修改和矯正憲法;另一個人在高聲朗讀一篇抨擊文章;在一張桌子上,一個人在指責部長們;所有的人都在說話;每個人都有傾聽他的聽眾……人們在咖啡館里生活……”此外,巴黎酒館分布廣泛,都有古老的歷史。1790年,有人估算,巴黎有4300個出售酒水的地方,即平均每200人有一個酒館。最密集的地方是塞納河附近的教區(qū),其次是平民街區(qū),圣-馬賽爾鎮(zhèn)平均每80個居民就有一個酒館。大革命期間,每次重大事件的當天,咖啡館和酒館都會成為宣傳站點。巴士底暴動就是在酒館和咖啡館里醞釀策劃的。這些細節(jié)的巴黎場景不僅有利于我們了解法國大革命發(fā)生的環(huán)境和氣氛,也向我們提供了法國和法國人民彼時彼地的具有史料意義的生活側(cè)面。
斷頭臺、斷頭鍘、絞刑架等等,都與劊子手的職業(yè)分不開,這些都不過是劊子手的工具而已。劊子手作為所謂的“最高司法執(zhí)行人”,不過是按照司法當局的命令去執(zhí)行罷了。而他們的社會身份與地位卻又十分矛盾。他們一方面接受最高司法當局,甚至是國王的親自任命,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所從事的應該是一種神圣的職業(yè)了,因此享受某些特權(quán);另一方面,卻又承擔著世人的罵名而幾乎與賤民為伍。隨著歷史前進的步伐,隨著他們的那些行刑工具的演變,我們看到了各個時代人們對于死刑的某種心理需求的變化:從血腥報復、解恨,到人道主義影響的出現(xiàn)(減輕犯人的痛苦,縮短痛苦的時間等),再到死刑的廢除,這也許是人性進化過程中所共有的普遍規(guī)律吧。
法國大革命對于法國對于全世界的影響都是極其深遠的。自大革命以后,法國先后經(jīng)歷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1792年9月22日 - 1804年10月18日)、督政府(1799年12月13日 - 1804年5月18日)、法蘭西第一帝國(1804年5月18日 - 1814年4月6日)、第一次王朝復辟(1814年4月 - 1815年3月)、百日帝國(1815年)、第二次王朝復辟(1815年7月8日 - 1830年8月7日)、七月王朝(1830年8月9日 - 1848年2月24日)、法蘭西第二共和國(1848年2月25日 - 1852年11月7日)、法蘭西第二帝國(1852年12月2日 - 1870年9月4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年9月4日 - 1940年9月13日)……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在這近150年的歷史當中發(fā)生了如此多的政權(quán)更替和反復。在法國發(fā)生的這段錯綜復雜的革命與反革命、復辟與反復辟的階級斗爭史為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提供了絕無僅有的思考。縱觀世界革命史, 英國以克倫威爾為首的大革命(1642年)最終處死了國王查理一世,但最重要的是奠定了議會高于國王的決策權(quán),為此后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打下了基礎。美國的獨立戰(zhàn)爭最終建立了一個全新而獨立的憲政國家。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統(tǒng)治也處死了沙皇,建立了布爾什維克的專政體制。人類近代歷史上發(fā)生的這些革命,其本身在某種意義上都有相似之處,然而其發(fā)生在各個國家的前因后果卻是不同的。它們都值得后人借鑒和思考。
就法國而言,對于本國大革命這段歷史的研究就從來沒有中斷過,并且不斷有新觀點出現(xiàn)。或許法國人骨子里面喜歡反思自己的過去,或許在經(jīng)歷了如此眾多的政權(quán)更替之后,人們可以靜下心來,仔細咀嚼那段既波瀾壯闊,又充滿血腥和殘暴的歷史。從人性的角度出發(fā),革命的過程中往往產(chǎn)生非理性的行為。書中關于法國大革命期間由“暴民們”發(fā)動的種種“暴行”的描述,證明了這一點。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文字獄”,因為“出身不好”或者因為說錯話而獲罪,甚至被處死的事情,在中國的歷史上,包括近代史和現(xiàn)代史,也同樣存在過,可能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恐怖時期”,甚至在革命派內(nèi)部,人人自危,“為了不被害而害人”,人們?yōu)榱俗员P悦幌ハ莺λ恕⑧従由踔僚笥眩率谷诵耘で_到了極致。在國人所經(jīng)歷的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們的人性不也是曾經(jīng)被扭曲,而做出了許多令今人看來都難以理解的事情嗎?從歷史的角度出發(fā),有些法國人認為,當初如果不砍掉路易十六的人頭,結(jié)果對法國的歷史進程會更好一些,然而歷史終究是無法假設的,誰也不能在原時原地重新趟過那歷史長河。汲取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教訓,不僅是法國人自己應該做的事,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典范性,它也該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共同財富。
桑松幾代人雖然身為劊子手,但是,他們并不是毫無良知或者毫無感情的人。他們的心中也會為他們認為被冤屈的死刑犯鳴不平,而他們的身份地位和他們的使命,既不可能,也不允許他們做出絲毫寬恕行動,除非讓死囚盡快死亡,或者使他(或她)在其他人之前死去也算是一種優(yōu)待的話。比如夏爾-亨利·桑松,他在一生中砍掉了不下2700顆人頭,包括國王路易十六、王后瑪麗-安托瓦內(nèi)特、丹東、羅伯斯庇爾等歷史名人的頭顱,而他本人在“恐怖時期”曾經(jīng)一度精神失常。作為一個已經(jīng)看慣了鮮血之人,也忍受不了良心的折磨。這也許就是他的最大不幸之處。而在法國大革命高潮時期,斷頭鍘超速運轉(zhuǎn),革命民眾瘋狂推崇斷頭鍘,稱之為“神圣-斷頭鍘”、“法律之劍”,稱執(zhí)行死刑是“紅色彌撒”,是革命儀式的犧牲,人們?yōu)橹瑁瑸橹瑁粩囝^鍘甚至成為一時的時尚,將它做成如兒童玩具、木偶、耳墜、水果刀等各種各樣的飾物和生活小工具。更有甚者,有的女人竟堂而皇之地給情夫們準備了“斷頭鍘式的避孕套”,將當時各種各樣的樂趣混于其中了。如此種種,該是革命民眾的殘忍的愚昧和不幸了。
法國大革命的同代人杜塔爾關于斷頭鍘這樣寫道:
“盡管回憶起遭受磨難的人性使我很痛苦,我還是要說,在政治上,這些處決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些巨大的影響就是安撫民眾對于他們所遭受的災難的不滿,滿足他們的復仇之心。失業(yè)的商人、面對物價飛漲而工資幾乎失去價值的工人,只有在看到比他們更不幸的人的時候,才能勉強接受他們自己的不幸。”
這種冷靜的思考,在那個大眾普遍瘋狂崇拜斷頭鍘的時期確實是難能可貴的,他的思考在當時雖然顯得蒼白無力,卻也反射出正義人性的光輝和偉大。當集體的狂熱達到一種失控狀態(tài)之時,黨派之爭也逐漸激化,激化到彼此之間相互仇視,達到必置異己者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此時,斷頭鍘的政治角色也發(fā)生了象征性的變化:從“政治懲罰的象征”變成了“黨派之爭的象征”、“黨內(nèi)派性之爭的象征”。斷頭鍘先是處死革命的對象,如保王教士、議員、貴族等,后來的主要目標是處死革命隊伍中的不同派別如吉倫特派,再后來的主要目標是處死革命黨雅各賓派內(nèi)部的不同勢力,最后雅各賓派最高領導、號稱“廉潔公”的羅伯斯庇爾處心積慮地處死了本該是自己親密戰(zhàn)友的丹東,而后,則以羅伯斯庇爾自己也被推上斷頭臺告終,從而導致法國大革命的失敗,為拿破倫建立帝國準備了條件。這血淋淋的歷史現(xiàn)實給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有益教訓。難怪胡斯曼·卡米伊(1871-1968,比利時政治家,眾議院議長、教育大臣,創(chuàng)立比利時社會黨,社會主義國際主席)指出:“過去的革命表現(xiàn)出它是最殘忍的制度”。這句話也許缺乏應有的分析,但是它一語中的點明了伴隨革命可能發(fā)生的一個本質(zhì)側(cè)面。當我們在本書中讀到雅各賓派最高革命領袖如丹東和羅伯斯庇爾者,竟因瘋狂派性大發(fā)作而相互廝殺,最后兩人都死于斷頭鍘下,造成革命派自毀,葬送革命成果,令人扼腕嘆息。究竟何謂革命,他們孰革命,孰反革命,實堪難辨。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法國大革命失敗的悲劇正是法國人民在找到一種穩(wěn)定和民主的政治體制之前所付出的血的代價。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刻地體悟到“自由、平等、博愛”這法蘭西共和國三信條,凝聚了法國人民的政治信仰和智慧,也深刻地影響著后世采取共和國體制的國家。因此,可以說,本書透過特殊的歷史視角,使我們了解到,這種理念是多么地來之不易。同時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本書應是天下革命者,尤其是革命精英們,應讀之書、必讀之書。興許,如果世上的革命精英們讀懂法國大革命,悟出法國大革命給予后世的啟示真諦,就不會發(fā)生或少發(fā)生伴隨革命的那些痛苦、荒誕和瘋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