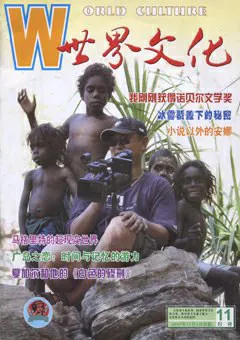植根于文化中的愛情觀
愛情與等級(jí)
每個(gè)民族都有它千年傳誦的神話愛情故事。在中國(guó),最著名的有牛郎與織女、許仙與白娘子的傳說;在西方,則有丘比特和普賽克、宙斯與歐羅巴等。這些愛情故事都發(fā)生在神與人之間,而它們的結(jié)局,它們所折射的對(duì)于人性的態(tài)度,卻大相徑庭。
在中國(guó),統(tǒng)治階層似乎始終只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權(quán)力的代表,他們于社會(huì)道德的維持責(zé)任要求他們以禁欲為美,因而對(duì)于愛情,往往麻木漠視甚至不屑一顧,他們維護(hù)的只有社會(huì)禮教秩序,一切有違于權(quán)力平衡的愛情和人性追求,都需抹煞消滅。因而,牛郎織女和許仙的愛情故事,最終毀于無邊的法力。在電影《大話西游》中,我們也發(fā)現(xiàn):至尊寶是個(gè)徹頭徹尾的“小人物”,他與紫霞仙子和白晶晶的愛情,便須服從于更大的權(quán)力壓迫。白晶晶的選擇便明顯地解讀了這種愛情的結(jié)局:要么選擇退出以明哲保身,要么在愛情的燦爛中被壓迫致死。因而中國(guó)傳說故事中的人神(或人鬼)愛情,只是具有強(qiáng)烈的象征意義,反映了人們對(duì)于等級(jí)倫理壓迫人性的無奈和微弱的抗?fàn)帯?br/> 另一方面,這種等級(jí)制度對(duì)于愛情的扼殺,正體現(xiàn)了重社會(huì)平衡而輕個(gè)性發(fā)展的道德傳統(tǒng)。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注重的是“和”,便須講究“禮法”。這種禮法,在董仲舒那里,便成為了“三綱”。“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可見,等級(jí)制度,是上天制訂的倫理,由不得人們改變。荀子也說,“貴賤有等,長(zhǎng)幼有序,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禮論》)。這種社會(huì)等級(jí)結(jié)構(gòu)的平衡學(xué)說,使得超越等級(jí)的愛情失去了生長(zhǎng)的土壤,而最終夭折甚至胎死腹中。
在希臘的神話故事中,神與人的愛情故事卻比比皆是,且大多圓滿幸福。無論是丘比特與凡人普賽克的愛情也好,還是宙斯與歐羅巴公主的浪漫故事也好,最終都在人性的光環(huán)中結(jié)出了美麗的種子。在這里,人性并沒有因?yàn)樯裥远觯伺c神的愛情故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結(jié)局。我們可以大膽的說,西方的神實(shí)質(zhì)上是人化身的神,他們有神力,卻經(jīng)歷著和人一樣的情感,愛情在他們眼里和凡人一樣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在他們的故事里,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人神——有人性光芒的神。這也奠定了西方文化中愛情至上、愛情平等的地位。
在這樣對(duì)愛情的看法和行為中,我們覺察到了西方文化中的平民化傳統(tǒng):屬于人性的愛情,并不是凡人的專利;權(quán)力和等級(jí),在愛情面前,顯得卑微軟弱;維持社會(huì)平衡的,不是權(quán)力和等級(jí),而是作為“人”所應(yīng)該具有的情感素質(zhì)。這也成為了西方文明的一個(gè)偉大傳統(tǒng)。
愛情與權(quán)力
雖然中西方文化中,愛情的地位不盡相同,但是無論何時(shí),愛情都會(huì)遭遇權(quán)力政治的干涉,為權(quán)力所用。此時(shí),在愛情和權(quán)力間作出不同的抉擇,正體現(xiàn)了一個(gè)社會(huì)對(duì)于人的深刻思考。
名垂青史的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分別與羅馬將軍愷撒以及馬克·安東尼有過戀情,而且他們的戀情,從政治意義上來說,曾經(jīng)影響了埃及和當(dāng)時(shí)世界的歷史。克婁巴特拉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美艷,讓愷撒和安東尼為她的政治目標(biāo)——保衛(wèi)埃及的獨(dú)立而前仆后繼。勿庸置疑,她的愛情是美麗而崇高的;但是,不幸的是,她的愛情卻附屬給了政治需要:她利用了愛情,或者說,她的愛情被政治利用了。就她和她的時(shí)代看來,王朝的使命遠(yuǎn)遠(yuǎn)重于個(gè)人的情感。
在一個(gè)政治需要和國(guó)家意志被視作絕對(duì)價(jià)值的時(shí)代,以愛情的犧牲換取政治的利益,往往是未可厚非的,甚至?xí)玫侥莻€(gè)時(shí)代人民的認(rèn)同;但如果為了愛情,置權(quán)力而不顧,則常常為人所不理解。
唐明皇早年勤政,創(chuàng)歷史上的“開元盛世”。但晚年熱戀上自己的兒媳婦楊貴妃,并寵幸有加,“君王從此不早朝”。勿庸置疑,他們的愛情刻骨銘心;可是我們似乎不肯承認(rèn)唐楊之間的“愛情”,而寧愿說他生活“驕奢無度”、“沉湎女色”。或許皇帝確實(shí)不需要愛情,唐明皇的悲劇,正在于他的貪婪:他追求愛情,卻企圖以他的權(quán)力服膺愛情——這不僅違背了社會(huì)倫理,更使國(guó)家陷入動(dòng)蕩。他需要愛情,卻來不及將政治放手。在人性和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中,他從一個(gè)極端走向了另一個(gè)極端。
因此,對(duì)他們而言,想要愛情,想要做一個(gè)完整而自由的人,便要懂得放棄。愛德華八世與沃利斯·辛普森的愛情故事正可以說明這點(diǎn)。1936年,當(dāng)愛德華八世向王室宣布要和沃利斯結(jié)婚遭到強(qiáng)烈反對(duì)時(shí),他毅然決定遜位來完成這樁亙古未有的婚姻,并于1937年在法國(guó)與沃利斯成婚。愛情與權(quán)利,仿佛是熊掌與魚,斷不可兼得!在政治面前,愛德華選擇了愛情,放棄了地位,卻同時(shí)也完成了人的意義。這或許是西方騎士文化中對(duì)愛情崇拜的體現(xiàn),同時(shí),也是西方社會(huì)思想的多元化、民主博愛平等的價(jià)值觀念的影響結(jié)果。
愛情與自由
愛情雖然時(shí)刻受到等級(jí)禮教和政治權(quán)力的干擾,但它的核心價(jià)值,卻是自由。愛情的自由既包括在追求愛情過程中身體和行動(dòng)的自由,更包括它對(duì)于人性解放所要求的心靈自由。就這一點(diǎn)而言,無論中西文化,人們對(duì)之的渴望是一致的。不過,在這個(gè)過程中,兩種文化所反映出的心態(tài)卻不盡相同。
在中國(guó),據(jù)《周禮·地宮·媒氏》記載:“仲春三月,令會(huì)男女,于是時(shí)也,奔者不禁。”《詩(shī)經(jīng)》中也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描述。可見,先秦時(shí)代尚是一個(gè)兩性關(guān)系自由開放的時(shí)代。而當(dāng)兩漢獨(dú)尊儒術(shù)之后,封建禮教日益加強(qiáng),兩性間的交往逐漸變得嚴(yán)格起來,“男女授受不親”,青年男女幾乎沒有機(jī)會(huì)可以自由地吐露愛情的心聲。尤其在愛人的選擇上,他們根本沒有自由可言。為了達(dá)到維持社會(huì)平衡的目的,婚姻(而且是他人包辦的婚姻)替代了愛情,個(gè)人的情欲和對(duì)異性的審美需求被無限期擱置。在這種背景下,中國(guó)人對(duì)于愛情的自由追求,首先表現(xiàn)在對(duì)愛人的自主選擇之中。
這種選擇精神,首先在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中得到了體現(xiàn)。他們的故事,象征意義甚于實(shí)際意義:愛情雖或存在,但感動(dòng)人的,則是他們對(duì)封建家庭等級(jí)觀念的挑戰(zhàn)。正因如此,“私奔”這一不無貶義的行為才能博得后人的同情與欽佩。
但是,這種反抗精神,并不能替代對(duì)愛情的追求和審視。事實(shí)上,即便是倒戈一擊的青年男女,在他們獲得婚姻選擇的短暫勝利之后,仍會(huì)重新回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路,補(bǔ)上封建婚姻禮教的課。因此,我們可以說,封建的愛情觀,已經(jīng)作為一種奴性內(nèi)化到人們的意識(shí)之中了,偶爾的叛逆根本扭轉(zhuǎn)不了觀念的頑固。梁山伯與祝英臺(tái)對(duì)愛情的誓死追求,固然引發(fā)人們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道德禮教的批判,但是主人公對(duì)待愛情所表現(xiàn)的清醒、理智和成熟,又何嘗不是因?yàn)樗麄儗?duì)封建禮教尚存有幻想,希望自己的行為能得到道德社會(huì)的寬恕和成全?可見,封建愛情的悲劇,是一種依附人格的悲劇。“化蝶”的意象,便清楚地昭示著:真正的愛情自由,只是一種幻想,一種在虛擬的夢(mèng)幻中才能實(shí)現(xiàn)的境界。
對(duì)西方而言,他們的愛情觀往往是狂熱、毫無顧忌的,從中引發(fā)的紛爭(zhēng)也就更為激烈。縱觀西方文學(xué),我們發(fā)現(xiàn),他們對(duì)于愛情的描寫,無所顧忌,在勇敢地贊美外貌、表達(dá)愛慕,也同時(shí)無不包含著強(qiáng)烈的性愛因素。羅伯特·彭斯《一朵紅紅的玫瑰》:
啊,我的愛人像一朵紅紅的玫瑰,
在六月里苞放。
啊,我的愛人像一支樂曲,
樂聲美妙、悠揚(yáng)。
你那麼美,漂亮的姑娘,
我愛你那麼深切,
我會(huì)永遠(yuǎn)愛你,親愛的,
一直到四海涸竭。
這種直白,少了曲折的美,卻將愛的意蘊(yùn)推到了極致。在許多時(shí)候,愛情的至高無上,可以使人們?yōu)榇俗鞒鲆磺校灾氯ズ腿藳Q斗。相比中國(guó)的想象自由,西方的愛情更注重表達(dá)自由。為了表達(dá)自由,他們也會(huì)選擇“私奔”,選擇抗?fàn)帯5强範(fàn)帲嗟氖腔趯?duì)自身獨(dú)立人格的理解,而非簡(jiǎn)單的對(duì)權(quán)勢(shì)壓迫的反叛。
愛情與婚姻
凡是有錢的單身漢,都需要娶位太太,這已經(jīng)成了一條舉世公認(rèn)的真理。這樣的單身漢,每逢搬到一個(gè)地方,即便四鄰八舍對(duì)他的性情想法一無所知,但大家既抱有這樣的真理,因而總將這樣的單身漢看作是自己某個(gè)女兒應(yīng)得的財(cái)產(chǎn)。
這是英國(guó)著名女作家簡(jiǎn)·奧斯汀的代表作《傲慢與偏見》的開篇一段話,它引出了一場(chǎng)關(guān)于愛情與婚姻關(guān)系的經(jīng)典故事。小說中夏洛蒂和柯林斯盡管婚后過著舒適的物質(zhì)生活,但他們之間沒有愛情,婚姻關(guān)系實(shí)際上是社會(huì)形式存在的需要;而伊麗莎白和達(dá)西的結(jié)合,由于是建立在愛情基礎(chǔ)上,因而幸福美滿……這個(gè)故事似乎是對(duì)婚姻和愛情之關(guān)系的很好注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guó)家的起源》中因此指出,“愛情是婚姻的基礎(chǔ)”。但婚姻與愛情的關(guān)系在實(shí)踐中并非如此明了,尤其是將它們置于社會(huì)倫理價(jià)值之中時(shí),孰重孰輕更成了千古難題。
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文化中,重禮輕愛、男尊女卑。婚姻只作為一種維持社會(huì)平衡的“禮數(shù)”而存在著。漢代鄭玄說:“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詩(shī)·鄭風(fēng)豐箋》)因而,中國(guó)古代婚姻事實(shí)上是一種家族禮儀,而非個(gè)人行為;所有的形式,從擇偶到成婚,都須由媒人與父母參預(yù)或做主,即古書所云“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詩(shī)·齊風(fēng)·南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這種重視婚姻禮法的價(jià)值觀,可能會(huì)造成婚姻中最本質(zhì)的缺憾:即情感和性愛被忽視,婚姻脫離了愛情,成為了家族等級(jí)制度的附庸。之中原因,恐怕是中國(guó)在愛情和婚姻問題上,缺乏人文主義傳統(tǒng)。朱光潛先生在《中西愛情詩(shī)》中便指出,西方人認(rèn)為戀愛本身是一種價(jià)值,戀愛有一套宗教背景,還有一套哲學(xué)理論,最純潔的是靈魂的契合……而中國(guó)人,卻一向重視婚姻而輕視戀愛。他們將婚姻(禮儀)視作個(gè)人價(jià)值為社會(huì)所認(rèn)可的重要途徑,也在事實(shí)上將之視為維持父系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有效的符號(hào)手段。他們的實(shí)用主義思想,使他們很難將婚姻視作愛情的神圣歸宿。
這種將愛情游離于婚姻之外的觀念相當(dāng)?shù)馗畹俟蹋幢阍诮邮芰宋鞣剿枷氲闹R(shí)分子那里,也未見動(dòng)搖。譬如胡適先生,在其婚姻生活上,便接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從未謀面的江冬秀為妻;不僅如此,在《貞操問題》中,他甚至道,中國(guó)人的愛情是在“既定名分之上”才產(chǎn)生的。直到了近代,隨著社會(huì)變革的深入,婚姻和愛情觀才在事實(shí)上逐漸發(fā)生改變;同時(shí),隨著從表面的婚姻形式到深層的婚姻制度所發(fā)生的明顯變化,人們?cè)絹碓揭庾R(shí)到婚姻的基礎(chǔ)應(yīng)當(dāng)是愛情。
相比之下,在愛情與婚姻的關(guān)系問題上,西方顯得比較寬容,他們視愛情為至尊,即便這種愛情發(fā)生在同性之間。比如柏拉圖就堅(jiān)信“真正”的愛情是一種持之以恒的情感,能夠讓人得到升華的情感,而唯有時(shí)間才是愛情的試金石,唯有超凡脫俗的愛,才能經(jīng)得起時(shí)間的考驗(yàn)。薩特與西蒙·波伏娃就是廣為傳頌的柏拉圖式戀愛的精典,他們一方面保持親近的、永不結(jié)婚的愛情關(guān)系,另一方面又不干預(yù)彼此的私生活。正是在這種理解與寬容的愛情中,薩特與波伏娃的愛情顯得與眾不同,他們沒有結(jié)婚,但卻情投意合,并將這份情感維持了半個(gè)多世紀(jì),直到1980年薩特去世。
可以說,在愛情與婚姻的關(guān)系中,西方注重愛情的過程,而中國(guó)強(qiáng)調(diào)作為形式與結(jié)果的婚姻。就本質(zhì)而言,婚姻簽訂的是道德責(zé)任義務(wù),而愛情賦予的是精神動(dòng)力。愛情張顯的是個(gè)性,而婚姻標(biāo)注的是社會(huì)性;愛情要求獨(dú)立,而婚姻強(qiáng)調(diào)和諧;愛情追求自由,而婚姻注重契約。沒有愛情的婚姻也會(huì)和睦,而僅有愛情的婚姻也不一定會(huì)美滿。對(duì)愛情和婚姻的本質(zhì)不同的理解必然決定愛情與婚姻的取舍不同。
愛情是不分時(shí)間和空間的,愛情給予的力量一直感動(dòng)和震撼著不同階層、不同文化背景的心靈。在任何時(shí)代、任何國(guó)度,愛情都是一種向往美麗的理想。但是當(dāng)歷史走到今天,物質(zhì)條件的優(yōu)越、生活節(jié)奏的加快、生存壓力的增大,卻使愛情愈來愈與現(xiàn)實(shí)綁定。許多人開始遠(yuǎn)離理想,更多的人愿意相信現(xiàn)實(shí)。當(dāng)理性和科學(xué)侵占了人們的生活時(shí),愛情正逐漸失去神性的光環(huán)。傳統(tǒng)莊嚴(yán)的愛情觀,正被輕松搞笑、務(wù)實(shí)自白的語言所描繪。或許愛情和婚姻的價(jià)值在分裂,但唯有這個(gè)時(shí)候,當(dāng)我們審視愛情所帶來的文化意義時(shí),我們更覺得它的蕩氣回腸的力量!更發(fā)現(xiàn)愛情所帶來的詩(sh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