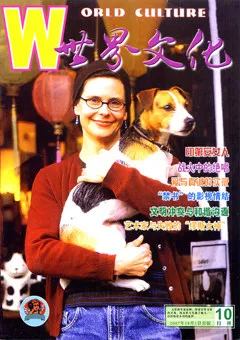文明沖突與和諧溝通
東西方文化沖突
界定東方與西方的分野,文化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東方由“遠東”和“近東”組成;第二種觀點,則主張東方應該涵蓋“非歐世界”與“阿拉伯世界”;最后一種觀點,即贊成東方是除了歐美之外其他欠發(fā)達的地區(qū)。在世界邁入現(xiàn)代化、全球化趨勢之后,第三種看法逐漸成為了學術(shù)界的主流。原本單純的地域概念,逐漸被賦予了經(jīng)濟、政治、宗教、藝術(shù)、文化甚至種族的色彩。于是,“東方/西方”二元敘述范式在愛德華·薩義德的書中被絕對化了,薩義德援引且補充了瓦勒斯坦的觀點,即在晚期資本主義之后,西方成為了世界的內(nèi)核,而東方則成為了邊緣。
需要指出的是,薩義德在書中并非聲稱是自己的觀點。就對于東西方文化沖突的看法,他直接援引了古希臘劇作家歐里庇德斯的悲劇《酒神的伴侶》與另一位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的悲劇《波斯人》中的情節(jié),并稱,通過對這兩部戲劇情節(jié)的分析,他得出,從古到今,西方人一直在用兩種觀點看待東方——第一,東方是容易被打敗的——《波斯人》中的主要情節(jié)就是波斯國王的母親和老臣們在王宮里悲戚地等待他們的軍隊被希臘大敗的噩耗;第二,東方是危險的、非理性的——《酒神的伴侶》中的主要情節(jié)便是從亞洲回來復仇的酒神狄奧尼索斯用東方的巫術(shù)儀式殺死了代表希臘理性的國王。
姑且不說薩義德的援引是否正確,他的觀點是否謬誤。我們需要看到,薩義德為我們打開了關(guān)于東西方“文明沖突”研究的另一扇窗口——跨文化研究。我們無從得知薩義德如何預見到了未來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后來者亨廷頓將文明、文化的東西方?jīng)_突闡述的極為透徹。羅素曾說,“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jīng)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國。”
尤其是“9·11”之后,陸續(xù)爆發(fā)出來的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朝核問題等一系列國際問題。很清楚可以看到,始終是西方陣營(如基督教世界)與東方陣營(如阿拉伯世界)的一種“文化沖突”。其實,文明沖突的作用,在這些局部沖突、局部戰(zhàn)爭中的作用本身就尤為明顯。雖然多元化、全球化、多極化、非冷戰(zhàn)已經(jīng)喊了多年,究竟能否實現(xiàn)?我們目前看到的究竟是否真的是多極化?確實,中國人恐怕會回答是安定和平發(fā)展的多極化,若是換了伊拉克人、朝鮮人或是阿富汗人,面對同樣的問題,難道也會這樣回答嗎?
奧運會是全世界的盛會,體育競技是拋棄了地域、種族、血統(tǒng)無差別進行競爭的活動。優(yōu)勝劣汰,公平競爭,全人類的奧林匹克精神在這里得到了極大的發(fā)揚。從文化上看,奧運會的主辦方對于整場奧運會的文化主導精神,是有著絕對決定權(quán)力的。是否把自己的文化立場融入奧運會,是主辦方的權(quán)力與主張。而這種主張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東方的,一種則是西方的。
其實我們站在文化的高度來看,無論中亞,還是東亞,或是北非、拉美等地,實際上仍然是東方世界,而中國,卻成為了東西方文明沖突下的一塊凈土。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東方國家,本次奧運會的舉辦,對于東方文化與西方世界的對話,顯然有著非常好的積極影響作用。
奧林匹克精神與“和諧”思想
東方的中國且作為東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在東方世界中顯然具備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發(fā)源于古希臘的奧運會,其奧林匹克精神成為西方精神文化的主導。這種精神貫穿幾千年以來西方人的思維方式,成為了西方諸多世界觀、哲學思想中最具特色,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根主線。自然而然,也成為了西方思想的濫觴。
本次奧運會在中國舉辦,這是首次將奧運精神和一個純粹意義上的東方國家聯(lián)系到了一起。兩種強勢文化的碰撞,往往意義并不在于文化的輸贏,而是在于在人類學、思想學的高度,去尋找文化中共通之處,從而獲得文化的互認。中國文化與古希臘文化是世界東西方兩大最為古老,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體系。當然,日后所形成的“東方/西方”文化體系與“中國/古希臘”文化體系并沒有直接的絕對關(guān)系。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就根植于文化體系中本質(zhì)的世界觀而言,如果追根溯源,其濫觴仍然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希臘與古代中國。
歷次奧運會的舉辦,實際上都是從舉辦方的文化立場出發(fā)。奧運會所貫穿的奧林匹克公平競技精神,實際上是古希臘哲學家關(guān)于藝術(shù)、體育與人格的一種詮釋,“那種能把音樂和體育配合得最好,能最為比例適當?shù)匕褍烧邞玫叫撵`上的人,我們稱他們?yōu)樽钔昝篮椭C的音樂家應該是最適當?shù)模h比一般僅知和弦彈琴的人為音樂家更適當。”所以學術(shù)界普遍認為,“希臘哲學是古代奧運的哲學基礎(chǔ),而古代奧運在某些方面體現(xiàn)和實踐了希臘哲學”。
正如李約瑟所說,西方文化是站在全人類發(fā)展的共性上進行建構(gòu)的,而這種普世的全人類并非當下的全球化。自然,柏拉圖的理想國也并非我們當下所說的和諧社會。但是兩者卻有相同之處。追求善美、整體美與人的全面發(fā)展,是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旨。我們清楚地看到,這種哲學思想與中國人的“中庸”、“和諧”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或許,這就是奧林匹克運動——或是說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在精髓上共通的地方,抑或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導致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長期以來并非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極端的沖突。中國文化緣何避開了當今文化發(fā)展的全球性憂慮?
答案很明顯,中國文明向來兼容并蓄的精神,實質(zhì)上為自身的發(fā)展不斷拓開了空間。任何一種民族、一種宗教與一種生活范式在中國都能獲得尊重與理解。這也是為何西方世界高度關(guān)注東方文化的原因所在。在愛德華·薩義德尤其是亨廷頓之后,西方對于東方的概念開始出現(xiàn)了更為細化的區(qū)分,即阿拉伯世界、猶太世界、中國世界與東南亞世界等。而后兩者所代表的遠東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是更為純粹的東方定義。
筆者認為,北京奧運會最大的文化價值,就是將純粹的東方的——中國的和諧精神、包容精神向全世界作一次全面的、綜合的展示。相比較而言,西方世界明顯更熟悉、更信奉于奧林匹克精神。而在北京奧運會上對于中國文明展示,則是結(jié)構(gòu)于奧林匹克精神之上的。
中國文化遺產(chǎn)的傳播
正如前文所說,北京奧運會的文化價值在于對于中國文化精髓——和諧精神的傳播。但這種傳播卻是有著自己的方式。常規(guī)說來,文化的傳播一般形式是非物質(zhì)文化的傳播。有學者認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播,應依附物質(zhì)化的流通進行傳播。任何文化,產(chǎn)品只有參與大流通,才能進行大傳播。”
就當下我國文化遺產(chǎn)的問題而言,確實存在著不樂觀的局面。尤其是可傳播的非物質(zhì)類文化遺產(chǎn),作為曲高和寡的國粹,始終未能獲得相應的社會效應與經(jīng)濟效應。縱觀世界其他文化生命力的決定因素,無非做到兩個關(guān)鍵的步驟,首先是保護,其次是傳播。而關(guān)于我國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和傳播,無論是官方還是學術(shù)界,在主流方向上一直都存在著不謀而合的觀點與主張。
中國總理溫家寶說:“人類文明只有代代相傳,才能不斷豐富發(fā)展;只有相互交流,才能文物化成。”同時,中國傳媒大學博士生導師周華斌教授也認為,“從每個城市自身出發(fā),都需要自己的文化傳承。保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藝術(shù)形式,一方面是城市樹立形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發(fā)展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最好方向。”
文化遺產(chǎn)尤其是非物質(zhì)類文化遺產(chǎn)走向市場,是文化遺產(chǎn)的終結(jié);如果不走向市場,曲高和寡又很難回到民間。正如前文所說,文化需要的是傳播,傳播中才不斷提高其生命力,在根本上才能促使文化遺產(chǎn)獲得真正意義上的保護。但是中國的文化遺產(chǎn)卻遇到當下這種進退維谷的局面,出路何在?筆者以為,中國文化遺產(chǎn)“走出去”的意義遠遠要大于“原地打轉(zhuǎn)”的意義。
因為在當下全球化的語境下,中國的文化是東方文化中唯一在全球幾乎暢通無阻而無意識形態(tài)、宗教信仰與種族歧視阻礙的文化體系。作為東方文化最重要的支系,中國文化在代表東方文化與非東方文化對話時,確實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性文化傳播普遍存在焦慮的前提下,北京奧運會責無旁貸地就成為了東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進行平等對話、溝通,并將中國文化進行有效傳播的一個巨大平臺。
從文化的存在形式來看,非物質(zhì)類文化遺產(chǎn)的存在形式一般有三種:歷史固化的精神態(tài)——文本形式;空間遷移的物質(zhì)態(tài)——物化式樣;文化傳承的主體態(tài)——意識理念。這三種存在形式?jīng)Q定了中國的非物質(zhì)類文化遺產(chǎn)實際上就是我們常說的傳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文化的存在形式有多種,所以說,文化的傳播策略相對也是多樣化的。如果站在生命機理、價值作用和社會影響這個角度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文化自身而言,給定的認識角度和科學定位的不同——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掘模式與出場路徑也就不同。
縱觀當下世界的文化沖突,無非是“傳統(tǒng)/現(xiàn)代性”、“本土/世界性”這兩對二元對立的文化沖突。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確實一開始是立足于本土的,也是傳統(tǒng)的,但是它自身以和諧為本的精髓卻是兼容并蓄的,這就決定了其在意識形態(tài)上破解了傳統(tǒng)的本土性敘事策略。北京奧運會自然而然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世界維度內(nèi)的溝通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正如著名學者、北京奧運會組委會藝術(shù)顧問季羨林先生所主張的那樣,“當今世界并不太平,到處都是你爭我奪。而中國向來是一個追求和平、和諧的國度,奧運會正是一個展示我們國家和民族偉大形象的機遇。”
文化遺產(chǎn)的傳播策略
畢竟,奧運會是體育的盛會,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國際文化交流周,也不是全世界的文化博覽會。作為從文化層面出發(fā)的研究者,只能說我們關(guān)注的只是奧運會所攜帶的文化價值。
就北京奧運會而言,這是中國文化遺產(chǎn)首次在奧運會上獲得主動權(quán),中國文化遺產(chǎn)獲得了世界性的展示和亮相。這種展示有別于一般性質(zhì)文化周、電影節(jié)的展示。因為奧運會是目前國際上最高級別的文化體育活動,是屬于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話。一方面,奧運會為世界各國在和平發(fā)展的大框架下進行無障礙溝通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奧運會仍是一次不可忽視的、展現(xiàn)各國綜合實力的機會。
正如前文所說,當下世界的沖突,在很大層面上是文明(或文化)相互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與理解而形成的文明沖突。對于東西方文明的沖突,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提供一個平等對話的平臺,進行文化層面的對話。奧運會的平等精神實際上就為這種對話,在本質(zhì)上起到了一個“平等”的作用,從而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最佳的“重估”。而北京奧運會,則是在一次全民、全球的體育盛會中,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從傳播精髓上看,北京奧運會的精髓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和諧,但是如何進行行之有效的和諧溝通?如何才能有效地將傳統(tǒng)文化中的和諧進行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深度傳播,這便是北京奧運會的具體傳播的策略。
從具體的策略上看,北京奧運會與歷屆奧運會有很多的不同之處。筆者認為,“和諧精神”與“中國風格”是本次奧運會在文化傳播策略上最大的特色。無論是獎牌、會徽、火炬的設計,還是宣傳片的制作,以及未來開幕式策劃的主題思想,甚至包括比賽項目的設置,都是帶有非常深入的“和諧精神”。尤其是火炬的設計,更是本著“淵源共生,和諧共融”的審美原則,火炬的接力長跑,命名為“和諧之旅”,至于獎牌的設計,更“和諧地將中國文化與奧林匹克精神結(jié)合在一起”。
而“中國風格”則是北京奧運會的主導風格。和以往的奧運會不同,以往的歷次奧運會,雖然都有本國的風格與特色,但是總體來說,是以西方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為主導思想的。而本次奧運會,其主導文化是純粹的中國風格,力圖將中國元素添加、滲透到整個奧運會的各個層面之中。中國的文化遺產(chǎn)——戲曲、繪畫、工藝美術(shù)與和諧的世界觀等等,都無一例外地滲透到了獎牌、會徽、火炬設計,開幕式、比賽項目的策劃當中,尤其是在比賽項目中,首次添加了中國的武術(shù)。這種指導思想,能夠促使每一個感受奧林匹克精神的人,也都真切地感覺到了中國的文化遺產(chǎn)魅力。
從全面來綜合分析,北京奧運會的意義遠遠不止奧運會期間短時效應的影響。舉辦一次奧運會,對于一個國家的影響,絕對不是暫時的。一方面,北京奧運會給全世界打開了一扇如何觀照中國的窗口。如何將“東方熱”、“中國熱”上升到對于中國文化遺產(chǎn)更為全面的了解,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和諧溝通”、“溝通和諧”?一方面,北京奧運會為其他東方國家也做了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范例。如何依托奧運會這樣一個代表全人類利益的盛會,將本國尤其是東方國家的文化遺產(chǎn)放置在一個較高的交流平臺上進行全球范圍內(nèi)的推廣,這也是當下文化全球化、多元化進程中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