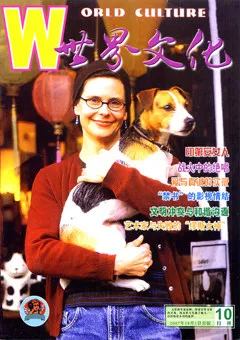“禁書”的影視情結
禁書猶如禁果,總是越禁越有魅力。古往今來,從東到西,曾有那么一批禁書,可望而不可及。而在它們堂而皇之,重見青日,或登堂入室,以光影的形式呈現時,你是否不得不唏噓一下物事輪回?
影視制作:情有獨鐘是禁書
放眼世界銀幕,從《洛麗塔》到《布拉格之戀》,從《湯姆叔叔的小屋》到《西線無戰事》,從《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到《失樂園》,這些禁書的改編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禁書,實質上是一種“禁止的愉悅”。它本身就是一個悖論,一邊試圖禁止那些危險的愉悅,但禁止卻又會喚起另一重愉悅。正如人類學家所說,禁忌是欲望的催化劑。越神秘,越能勾起你的欲望,恨不能一睹而后快。在這種催化劑下,書雖“禁”難“止”。只不過形式稍有變化,由公開轉入半公開或者地下罷了。
當年冒天下之大不韙所讀的文字和情節,現在居然做成巨幅廣告在最繁華的街頭招搖,在最高檔 影院被光電聲影放大無數倍,不遮,不掩,不躲,不藏。與之相伴隨的是巨大的好奇心:看看熒屏或銀幕究竟是如何演繹的?抽象的文字演變成了怎樣的具象畫面?平面的組織轉化成立體的結構,線性的概念轉化為交叉的時空,影視的觀賞和文字的閱讀是有著巨大差異的。為了感受這種差異,在親切感的感召中,好奇心的驅使下,大批觀眾打開電視、走進影院,與自己心愛的禁書再來一次另樣的閱讀。
如果說禁書的觀眾基礎決定了票房號召力的話,那么禁書的思想和內容則是影視創作難得的資源。
例如《失樂園》不僅僅是一本書而已,它是一個充滿人類原欲的性愛烏托邦,傳衍出一場心靈與肉體的掙扎。而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在今天讀來,卻依然和它首次出版時一樣深入人心,因為它交織著政治與哲思、肉欲和靈性、趣味和深度。正如《華盛頓日報》點評:“當今寫作,男女之間多重關系的作者中,沒有人比得上昆德拉的智慧和洞察力。”說到描寫男女關系,《查特來夫人的情人》看起來大肆宣揚的是性愛結合的美妙,和原始身體的碰撞情感,而其本質卻是對當時冷冰冰的上流社會的唾棄,并用喪失了性功能來諷喻當時的上流階層。《兒子與情人》之所以被禁,原因是“有悖倫理道德”。這是性愛小說之父勞倫斯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書中人物的復雜心理狀態刻劃得相當細膩。1961年美國俄克拉荷馬發起了禁書運動,在租用的一輛被稱之為“淫穢書籍曝光車”所展示的不宜閱讀的書籍中,《兒子與情人》首當其沖。
人物多而不亂,情節長而不散,思想深刻而不直白,名著的功力即在于此。所以說,曾被禁讀的這些名著猶如寶庫,不僅給影視劇創作提供用之不盡的資源,而且其成熟的小說技巧也給影視劇創作帶來某些啟發。例如《西線無戰事》,雷馬克曾說,這本書“以最簡潔的方式描寫了戰壕里生活的人在人性方面的偉大和軟弱”。小說沒有主情節,結構看起來松散,但是它寫得像劇本一樣,一個場景接一個場景,扣人心弦,非常富有鏡頭感。對以畫面為第一要素的電影藝術來說,這些是最有價值的。有人稱名著是“導演的卓越指南”,不無道理。
別樣演繹:耳目一新在銀幕
由小說改編成的電影,總會存在著兩個問題,不是電影一攬細節而忽略主題,就是突出主題而喪失細致的布局。
而《布拉格之戀》(改編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主題上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本片的導演菲利普·考夫曼歷來擅長從小說中提煉主題。生命中的輕與重,在小說中表現得是如此深厚與凝重。但是,與作家的闡述方式有所不同,考夫曼的電影表現非常簡單,只單純地用托馬斯與特蕾莎之間長久的愛情,來講述這個哲學化問題。
《布拉格之戀》也許只是米蘭·昆德拉小說里的一小部分,但這一小部分化成影像呈現在我們面前時,留給我們的思考就像電影中層出不窮的鏡子一樣觸手可及,但又冰涼襲人。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成功影片對細節的關照。
“她完全沉浸在一種溫柔的喜悅中,像春天森林中的颯颯清風,迷蒙地、歡快地從含苞待放的花蕾中飄出……在她千絲萬縷互相交匯的身體里,欲望的小鳥正做著美好的夢。”這是勞倫斯筆下的查特萊夫人——康妮。
園丁健壯的身體,出現在康妮眼前,她幾乎是本能的往后退縮。兩個人逐漸走近,走近……肆無忌憚的裸體在森林里奔跑、在草地上做愛,人的赤裸肉體和大自然融在一起……這是銀幕上的康妮。肯·杜塞爾的電影版《查特萊夫人》,對當時社會階層的狀況和風景、服裝、交際等描寫頗為出神,又比較忠實于原著,美致情色,讓人耳目一新,為眾家影評人所稱道。
不僅編導給予昔日的禁書新的生命,演員出色的表演也讓禁書煥發新的色彩。
導演亞德里安·林恩1997年把《洛麗塔》搬上了銀幕。多米尼克·斯萬,電影中洛麗塔的扮演者,她一路過關斬將,從2500多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讓人驚詫的是,之前她并無任何演員經驗。但正是這個沒有任何來頭的斯萬成功地創造出了一個精靈形象——既有少女的純真,又有女人的性感。影片中,洛麗塔趴在草坪上沐浴著陽光,身上微濺水滴的出場可謂情色經典。有人戲稱,這幅畫面很好地解釋了男人們的戀蔻情結。
成功秘訣:立足現實拍經典
禁書改編影視劇本之路,并非鮮花盛開,例如曾經對有些劇本的改編惡評如潮。的確,如果你親眼看見將禁書變成了一個個通俗的愛情肥皂劇,政治和哲學意義都成為虛化的背景,定會失望至極。所以,有批評家對出現在小說里的敘述者的“缺失”感到遺憾,有的探討小說具有“不可改編性”,有的探討文學敘事與電影敘事是否有同一性,有的認為改編的影視沒了小說里的深刻意韻,或難以傳達出小說的精髓。
從小說到劇本,涉及到太多的改編技巧。對于這些技巧,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改編對像的選擇是成功的關鍵。
我們看看奧斯卡金獎巨片《西線無戰事》。小說被視為德國青年一代的控訴書,一戰時慘遭封禁,解禁后,被譯成29種文字,銷量高達800萬冊,受到青年的熱烈歡迎。
雷馬克在1963年接受弗里德里希·盧夫特采訪時說:“十八歲的青年本來應該面對生活,卻突然面對著死亡。他們的命運如何呢?出于這個原因,我與其把《西線無戰事》視為描寫戰爭的書,毋寧視為描寫戰后的書。我一再問自己:我們將會怎樣?我們在不得不與死神搏斗之后,我們能怎樣生活?”雷馬克在這本《西線無戰事》的前言里也說:“它只是試圖敘述那樣一代人,他們盡管躲過了炮彈,但還是被戰爭毀掉了”。
《西線無戰事》這部建立在同名小說基礎之上的影片,通過一群德國士兵的眼睛展示了戰爭的殘酷,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真實寫照。今天看來,這部影片仍然非常尖銳。
除了戰爭之外,有些對人性給予終極關懷的禁書,也是改編劇本的至選。
霍桑的小說《紅字》被禁,是由于政治和宗教原因。書中描述的是十七世紀美國的清教徒殖民社會,發生了一宗年輕少婦在丈夫失蹤的情況下跟當地牧師產生奸情的事。女主人公海絲特因懷孕而暴露奸情,但她寧愿接受嚴酷的懲罰:終生穿著繡著紅字A的衣服,也不肯說出情夫的名字。但海絲特的丈夫突然歸來,并不擇手段追查奸夫身份加以報復,最后挑起了印第安人與當地居民之間的沖突。
1995年,《紅字》被搬上了銀幕。電影沒有完全照搬小說的原貌,而是使故事更完整,人物行為和性格更突出更具特點。片中導演借用電影語言將人物心理活動具象化,用阿瑟的自責行為,丈夫的復仇計劃等等呈現給觀眾。全篇以小珠兒的口氣畫外音敘述,結尾也讓有情人終成眷屬。不過最后阿瑟還是由于過度的自責和內疚英年早逝,海絲特也沒有再和別人在一起——“或許這就是上帝對他們的懲罰吧!”
成功的影片改編,不僅會撩開禁書神秘面紗,而且會蘊含編劇一番良苦用心:但依然會讓人接受。并且在接受的同時,更主動地探討禁書今天的時代意義。
歲月如水,洗去無痕。當禁書已成往事,或許你內心深處還是留著某些影像的片段,讓你咀嚼,讓你回味。禁書與影視,的確是難了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