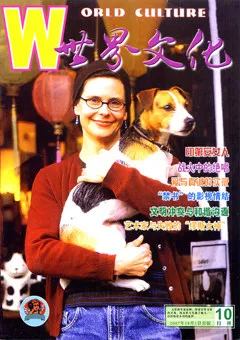英國報業的發祥地
艦隊街,與赫赫有名的英國皇家海軍艦隊沒有絲毫關聯,以前,這里是倫敦城外的一條小河。人們填河后使之成為一條寬闊的馬路。1702年,艦隊街上發行出版了第一份報紙《每日報》,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張定時定期出版的報紙。從那年開始,艦隊街便和報社、報紙與印刷廠結下了不解之緣。《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獨立報》、《鏡報》、《太陽報》、《觀察家報》、《衛報》、《每日郵報》、《旗幟晚報》等100多家報館紛紛入駐此條街上。
那時,編輯在樓上編報,地下室和后街就是印刷工廠,數以千計的記者奔走于議會、唐寧街、白金漢宮和社會各個角落。晚上,各報社燈火通明,印刷機飛轉;編輯、記者聚集在酒吧、咖啡館交流信息;早晨,報紙零售商、售報人游走于街上,批發報紙,發送到遍布全國的營銷網點賣報。那時的艦隊街,儼然是英國信息的集散地,熱鬧非凡,成為倫敦一景。報館之所以鐘愛艦隊街,是因為附近教堂多,如圣保羅大教堂、圣普萊德大教堂、坦波大教堂等。在300年前教堂里教士、神甫是倫敦少數識字的知識分子,亦是報紙所擁有的讀者群,他們對信息交流的渴求奠定了客戶基礎。
有“艦隊街第一夫人”美稱的琳達在1967年成為《每日郵報》的撰稿人。1972年,一位專欄作家離開《每日郵報》另謀高就時,琳達接手那個專欄,從此一干就是32年。琳達去世后,艦隊街大小媒體競相緬懷。琳達“文筆犀利、誰都敢罵”常常讓一些名流不寒而栗。在長達37年的新聞生涯中,她獲得了許多獎項,作為英國頭號女性評論作家,也是艦隊街專欄作家們競相模仿的對象。1997年,因為在新聞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她獲得了英帝國勛章。
中國新聞界的前輩,著名戰地記者蕭乾的戰地生涯,也是從艦隊街起步的。1944年,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正在劍橋大學攻讀學位的他,毅然決定走進了艦隊街。從一個埋首書齋的讀書人,成為戎裝上陣的戰地記者。
在經歷了200多年輝煌歲月之后,上世紀80年代,世界媒體大王默多克收購了《泰晤士報》,不久就將其所屬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太陽報》和《世界新聞報》等報社搬出了艦隊街。后來,其他報社紛紛效尤,也搬到了別處。
報業的繁榮、報社的林立,帶來了艦隊街其他行業的繁榮和發展。相濡以沫的老記者們,還忘不了回到艦隊街,在“柴郡老干酪”酒店、“埃爾維納斯”酒店中品嘗昨日的記憶,以慰藉那躁動難安的心靈。
曾名噪一時的報紙一條街銷聲匿跡了,艦隊街昔日的輝煌不再。目前,艦隊街現在街旁兩側已經讓商家和金融商們占領,淪落成和倫敦普通街市并沒有什么不同的小街,但艦隊街仍被認為是英國新聞媒體的代稱。對于許多記者來說,艦隊街代表著英國新聞界在社會上風光無限的一段往事,因此,艦隊街的稱呼仍不斷出現在懷舊的英國人的口頭和筆頭上,也將永遠珍藏在英國媒體人士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