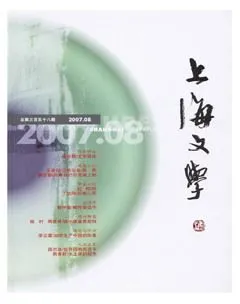廚房
我還記得那間廚房里的地板,這是整幢房子里最肥沃的地方。奇怪的是,應(yīng)該肥沃的,房子前面,朝南的小院子卻是枯瘦的。灰白的地皮,掘不到兩公分,就是破磚爛瓦碎石頭,它們拱著地皮,使得嶙峋不平。除了一些車(chē)前籽和狗尾巴草,它再長(zhǎng)不出什么。昆蟲(chóng)呢,只有一種,瓦灰色的干癟的西瓜蟲(chóng)。小院子反是這里最貧瘠的地方。而廚房,卻很豐饒。地板最初一定是上過(guò)漆色的,此時(shí)全叫油膩糊住。要是幾家合力用堿水刷洗過(guò),它暫時(shí)地呈現(xiàn)出一種慘白,結(jié)果是,更深而徹底地吸進(jìn)油膩。再刷堿水,再吸油膩,這就合了油漆的原理和工序,地板完全成了油膩的顏色,一種肥沃的灰黑,它簡(jiǎn)直要長(zhǎng)出東西來(lái)了!它果然是長(zhǎng)出了些東西。在墻根——假如能夠挪開(kāi)煤氣灶、菜櫥、桌子以及瓶瓶罐罐,露出墻根,就可看見(jiàn)那里長(zhǎng)著一種黑色的植物,它的名字叫作“霉”。這里的動(dòng)物品種就多了,老鼠、蟑螂、壁虎、蜘蛛、蚰蜒、螞蟻,也有西瓜蟲(chóng),但這里的西瓜蟲(chóng)比前面院子里的要肥碩和豐潤(rùn),它們濕漉漉的;有不定期來(lái)到的貓,那都是野貓,過(guò)著居無(wú)定所的生活,時(shí)而來(lái),時(shí)而走;還有人看見(jiàn)過(guò)一只黃鼠狼,神秘地露了一下面,就再看不見(jiàn)了。廚房就像一個(gè)動(dòng)物園。它們彼此相克,比如貓吃老鼠,壁虎和蜘蛛吃蟲(chóng)子,可這就是生物鏈啊!總的來(lái)說(shuō),廚房里的生態(tài)十分活躍。在某個(gè)季節(jié),氣候特別干爽,空氣又十分明澈,午后三時(shí)左右,太陽(yáng)從后門(mén)照進(jìn)廚房,這一刻,廚房里往往沒(méi)有人。燒晚飯的時(shí)候沒(méi)到,小孩子又沒(méi)有放學(xué),陽(yáng)光一下子將廚房照亮。地板呈現(xiàn)出一種油色,黃蠟蠟的,縫是油黑的,地板面上的木紋和裂隙也是油黑,上面有一只三條腿的板凳,是本木的白。廚房突然鮮麗起來(lái),幾乎是奪目的。光線稍一轉(zhuǎn)移,那些爽利的線條和塊面又毛出一層絨頭,變得有些綽約,因而生動(dòng)起來(lái)。然后,噪聲起來(lái)。
我再也無(wú)從知道那個(gè)奶媽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誰(shuí),即使在小孩子的年齡來(lái)看,她也是年輕的。她身個(gè)結(jié)實(shí)勻稱(chēng),面色紅潤(rùn),梳一對(duì)黑亮亮的辮子,直垂到腰間。她的衣褲是一種鮮艷的毛藍(lán),搭襻布鞋。除了奶那個(gè)女?huà)耄€要搭伴著做一些雜事。我總是看見(jiàn)她背著門(mén),面朝里,在砧板上切菜。無(wú)論切什么,她都會(huì)從刀下拾起一塊填進(jìn)嘴里,同時(shí)回身張望一眼,是以為有人看她嗎?這種習(xí)慣不知源于怎么樣的生活經(jīng)歷,也無(wú)從考起了。她所哺乳的那個(gè)女?huà)胪ǔJ撬谝粋€(gè)木頭小床,四面圍著柵欄的小床被她挾在胳膊底下,隨身帶著。下午,小孩子們都放學(xué)回家,壅塞在弄堂里的時(shí)候,她就將小床停放在后門(mén)口,自然就會(huì)有小孩子過(guò)來(lái)看她,逗她,甚至大膽地將她抱出木床,走來(lái)走去。就好像是一個(gè)換工,她借給全弄堂的小孩子一個(gè)大玩具,全弄堂的孩子則負(fù)起照護(hù)女?huà)氲呢?zé)任。免不了會(huì)有摔著女?huà)氲模瑡雰簺](méi)怎么哭,那孩子先嚇得哭起來(lái)。其實(shí)沒(méi)有人會(huì)責(zé)備她,或是他,在多子女的年代里,孩子都是這么摔摔摜摜長(zhǎng)起來(lái)的。
是記憶模糊了,還是事實(shí)如此,那奶媽在印象中是顢頇的。時(shí)間久遠(yuǎn)的人和事都有一種顢頇的表情,就像從舊膠片上放映出來(lái)的老電影,反映遲鈍,有個(gè)時(shí)間差。那奶媽擁著女?huà)攵?tīng)?wèi){她拱著她的乳房吸吮奶水。看不出來(lái)她對(duì)這女?huà)氲膽B(tài)度,是有些親,還是相反,憎恨她吸去了本該是她孩子的奶水。但她顯然不會(huì)是有著強(qiáng)烈感情的女人,她只是年輕,這樣的年輕,身心里總會(huì)積蓄和洶涌著一種能量,這就使她的沉默有了重力。擔(dān)任這家主要家務(wù),包括監(jiān)管她的,是女?huà)氲淖婺浮U绽硪呀?jīng)是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年紀(jì)了,可是上面的婆婆還健在,媳婦們呢,都是現(xiàn)代的獨(dú)立的女性,有自己的收入,所以,這祖母就一直屈抑著,也是沉默的。但這祖母卻有著意想不到的幽默感,這表現(xiàn)在,當(dāng)人們說(shuō)話,她適時(shí)發(fā)出會(huì)心的微笑。這微笑流露出的還不止是幽默,還有一種秉性,敦厚的秉性,這讓她能夠消受別人的智慧。她說(shuō)是東家,實(shí)際要比奶媽辛苦,買(mǎi)菜,收拾,燒飯,洗衣,而奶媽大部分時(shí)間是坐著,哺乳懷里的女?huà)搿5燃覄?wù)暫告段落,有一時(shí)的空閑,祖母也終于坐定下來(lái),就坐在奶媽身邊。她的神情,即便隔了歲月,依然是比奶媽靈敏,靈敏于各種感受,這是由閱歷決定的。于是,她的身型就有了些微的輪廓,破開(kāi)歲月的氤氳。而奶媽是一片空洞,這空洞將在某個(gè)時(shí)候變得深邃,以后會(huì)談到這一點(diǎn)。
這一老一少,一主一仆并排坐在小凳子上,聽(tīng)誰(shuí)說(shuō)話呢?聽(tīng)那個(gè)幫傭的女人說(shuō)話。這個(gè)女人是廚房里的精英,她只要開(kāi)言,大人小孩必聽(tīng)無(wú)疑。從現(xiàn)在往那時(shí)候推溯,她其實(shí)了不到三十,至多三十,可在那個(gè)時(shí)代,卻是一個(gè)成熟的年齡。她的見(jiàn)識(shí)呀,簡(jiǎn)直豐富得沒(méi)法說(shuō),雖然一點(diǎn)也無(wú)從考證,可就她說(shuō)話的威儀來(lái)看,沒(méi)什么可說(shuō)的!她的臉很清晰,在整個(gè)混沌的景象中,唯有這張臉,是以肯定的線條構(gòu)勒的,也因此變得平面,而其他的印象倒是有一些立體的效果,比如奶媽?zhuān)驗(yàn)橛杏罢{(diào)。也因?yàn)榇耍兊眉怃J了。她的眼睛,有著明顯的雙瞼,鼻子有些窄,鼻梁這里因?yàn)槌3J鞘站o的,就有了一道豎紋,嘴唇是單薄的,因而使筆觸更加鋒利。她單身未婚,對(duì)于一個(gè)幫傭的人,這似乎有些過(guò)于摩登了,可是在她,這又理所當(dāng)然,有哪個(gè)男人敢娶她呢!在她們的階層里,那種傳統(tǒng)的婚配,不外是鄉(xiāng)下老家的男人,或者楊樹(shù)浦的也是同鄉(xiāng)人的工人,顯然不適合她。那么,找一個(gè)職員,可是誰(shuí)聽(tīng)說(shuō)過(guò)職員的太太是幫傭的?于是,不結(jié)婚也罷。由于是她,完全有權(quán)力過(guò)這么一種特殊的人生。她所服侍的東家是一對(duì)沒(méi)有兒女的夫婦,這就像配好了的,她也不必和小孩子交道。小孩子總是不潔的,屎啊尿啊,還有乳臭啊!就像那個(gè)奶媽?zhuān)纳砩嫌肋h(yuǎn)散發(fā)出這些氣味,而這個(gè)女人,冰清玉潔。她的用物,我說(shuō)是“她”的用物,而不是她東家的,都是單獨(dú)分出來(lái)。碗是鑲金邊的,筷子鑲的是銀箔。她是懷著怎樣的心情積攢起她的財(cái)物,在這擁擠、油膩,而且嘈雜的廚房里,要收藏它們,不那么容易。它們實(shí)在太精致了,而公用廚房是粗礪的,什么事沒(méi)有,地板上撬起來(lái)的鐵釘子都會(huì)絆你一個(gè)大跟頭,就像地里的老樹(shù)根。她的碗具上的金邊銀片,還有溫潤(rùn)的細(xì)瓷,波光粼粼穿行在時(shí)間的黑暗隧道。
因?yàn)樗@間廚房里會(huì)有一些貴客造訪,那多是隔壁門(mén)牌號(hào)碼里的主婦,總是向她請(qǐng)教某種菜肴如何制作,某種衣物如何洗滌,甚至于,還有一個(gè)主婦,很信任地將小孩子交到她手里,請(qǐng)她刮痧。要知道,她其實(shí)并沒(méi)有生養(yǎng)孩子的經(jīng)驗(yàn),大概唯其因此,才下得了手。只見(jiàn)她將小孩子翻倒,掛在膝上,這時(shí),不易覺(jué)察地,她的身子向后仰了仰,為了避開(kāi)小孩子身上汗、尿、乳、還有眼淚交織成又發(fā)了酵的酸臭味。然后,她很鎮(zhèn)定地將一枚分幣在一碗水里蘸蘸,就像刮魚(yú)鱗一般在小孩子的背上刮去。由這些交道生出了交情,鄰家主婦們就有時(shí)候并不為什么事,而是專(zhuān)門(mén)過(guò)來(lái)與她閑話。她們使這間廚房蓬蓽生輝。
完全是與她相對(duì)而設(shè)地,廚房里另一位成員,也是幫傭的女人,質(zhì)地特別柔軟。你甚至?xí)@異,這樣柔軟的質(zhì)地如何還能在這一片混沌中占位,似乎輪廓的每一條邊線都有危險(xiǎn)被吞噬淹沒(méi),而它卻依然存在著。這說(shuō)明它的韌勁,頗有彈性。這是以圓為單位而組合的占位,有些像太極,含而不露,用的是內(nèi)功。她是記憶中最昏晦的一塊,許多曖昧從她這里生出。她從很年輕的時(shí)候就守寡,已經(jīng)度過(guò)長(zhǎng)久的沒(méi)有男人的日子,可是奇怪的是,她比那個(gè)年輕健碩,奶汁像是從熟透的漿果里迸流著的奶媽?zhuān)哂星橛臍庀ⅲ@也就是曖昧所在。這柔軟的質(zhì)地同時(shí)還是濕潤(rùn)的,就有些幽微的光悄然揮灑出來(lái),這里亮一點(diǎn),那里亮一點(diǎn)。她在廚房所占據(jù)的位置是后窗側(cè)邊,后窗底下是一具水斗,光線就斜著照亮了她的側(cè)面。由于窗玻璃上蒙了油垢,像結(jié)了一層乳膠般的霜,光也是曖昧的。這一個(gè)存在于記憶中的位置最微妙了,它不像那一個(gè)精英女傭的清晰和銳利,它渾圓的形狀很容易和周邊環(huán)境混為一談,于是就有了一種游動(dòng)的不確定的性質(zhì),可它就是不消失。很像是水銀,打散了,碎成齏粉,一旦聚攏一起,又是完整的一顆,一丁點(diǎn)不缺。那精英女傭是焊得很牢的一個(gè)整體,這卻是由細(xì)枝末節(jié)合成,就變得很是黏膩纏綿。
方才說(shuō)的,廚房里露過(guò)一回面的黃鼠狼,就是被她看見(jiàn)。她大驚失色,隨后流下眼淚。在她們的鄉(xiāng)俗看來(lái),黃鼠狼是不吉祥的動(dòng)物,誰(shuí)看見(jiàn)誰(shuí)就遭厄運(yùn)。所以,她不讓人們提起她看見(jiàn)黃鼠狼這件事。可偏偏有些調(diào)皮的孩子,冷不防沖她喊一聲“黃鼠狼來(lái)了”,她慍怒的表情并不讓人駭怕,這就是她和那一位幫傭的女人不同之處,那一位不怒而威。小孩子其實(shí)對(duì)事物的質(zhì)地最了解,他們代表人類(lèi)的本能,所以他們就選中這一個(gè)來(lái)欺負(fù)。小孩子并不為她嚇退,繼續(xù)玩著這個(gè)殘酷的游戲,還扮演著黃鼠狼從她跟前躥過(guò),這一回喊的是“我是黃鼠狼”!結(jié)果,她笑了。她的笑,不是像那位女?huà)氲淖婺福鲇谟哪泻椭t遜,而是好脾氣,甚至是有一些輕浮的脾性,這使她的原則性受了損。她的這種質(zhì)地就是好變通,因?yàn)槊芏炔粔颉jP(guān)于黃鼠狼的信仰就這么瓦解了。盡管她沒(méi)有將她的有神論貫徹到底,可她的宿命感依然籠罩了這一間廚房。我為什么要強(qiáng)調(diào)這一間廚房,那是因?yàn)椋趶N房的前面,還有樓上,各個(gè)居室里,過(guò)著和社會(huì)主流世界觀相合的生活,就像是社會(huì)的正面。而廚房,則是在社會(huì)的邊緣,甚至有一些負(fù)面的意思,這里流淌著思想的暗流。談到宿命論,就要扯出這幢房子之外的一個(gè)女人,一個(gè)老女人,她有時(shí)候會(huì)來(lái)到我們的廚房。
我們的廚房是敞開(kāi)的,任何人都可以進(jìn)來(lái),這也是和正式居室不同的地方。每一種制度,無(wú)論多么嚴(yán)密都會(huì)有疏漏的空隙,廚房就是這樣的空隙。這老女人不曉得住在哪一幢房子里,她可能都不是我們弄堂里的人,而來(lái)自另一條弄堂。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摸到了我們這里,因她來(lái)到這里并不是專(zhuān)對(duì)著某一個(gè)人,好像她看中的就是我們這個(gè)地方。她每一次來(lái),總是坐在一張小矮凳。這張小矮凳的榫松動(dòng)了,一不小心就會(huì)夾了肉,我們就7a6536f0295d87cc44af7f2aa4682d366b8953338fc8199f2ed9f82230e65dc5管它叫“夾屁股矮凳”。這里的物件都有名字,另一張板凳叫“阿蹺”,因?yàn)橹挥腥龡l腿。相反,人倒未必有名字了,小孩子往往叫“阿大”“阿二”“阿三”,這么依次排下去,奶媽就叫奶媽?zhuān)D穭t是“三號(hào)阿姨”“二樓阿姨”“小花園阿姨”,以所服務(wù)的東家的居住地為標(biāo)號(hào)。這從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廚房里的自然觀,世上萬(wàn)物,都是有生命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老女人坐在“夾屁股矮凳”上,身子就靠著門(mén),這扇門(mén)就和地板一樣破損和油膩,我不記得它曾經(jīng)關(guān)上過(guò),它總是推到墻上,敞開(kāi)著。老女人就像癱倒似地靠著門(mén),身子還在繼續(xù)往下滑,終于奇跡般地沒(méi)有滑到地板上。她抱怨她每天夜里聽(tīng)到鬼叫,鬼叫擾得她一夜無(wú)眠。這話說(shuō)得無(wú)比森然,忌諱黃鼠狼的女人同樣忌諱這老女人,每一回她離去,都要在她身后吐唾沫,說(shuō)她帶來(lái)了死氣——這就對(duì)了,我為什么懷疑她來(lái)自另一條弄堂,那就是她攜帶的氣息不是我們弄堂的氣息,別看我們的廚房有著陰晦的氣氛,可這是朗朗乾坤里的陰晦,就像光投下來(lái)的同時(shí)也投下了影子。雖然如此忌諱老女人,但當(dāng)老女人再度來(lái)到時(shí),廚房的門(mén)還是向她敞開(kāi),那宿命的女人依然是聽(tīng)眾之一,她照例不能將原則貫徹到底。
老女人來(lái)到的時(shí)候,最興奮的是小孩子。我們擠作一團(tuán),聽(tīng)她描繪鬼叫。女人們想將我們驅(qū)趕出去,因?yàn)樾『⒆佣涓蓛簦盥?tīng)不得這種事情。可是,她們趕不走我們,我們堅(jiān)決不被趕走。趕不走的另一個(gè)原因是,我們都怕走過(guò)老女人身邊,而她就坐在門(mén)口。我們愛(ài)聽(tīng)她的鬼話,卻懼怕走近她,在我們看來(lái),她和那打擾她的鬼,就是一家人。倘若我們沒(méi)聽(tīng)懂她的話,她的口音很古怪,又總是連哭帶訴,我們向大人們要求證實(shí),鬼叫究竟是如何叫法,那么,所有的人,勿管有神論無(wú)神論全都變了臉,斥道:誰(shuí)聽(tīng)見(jiàn)鬼叫了?誰(shuí)聽(tīng)見(jiàn)鬼叫誰(shuí)就要死!老女人不知道什么時(shí)候不再來(lái)了,可是,也沒(méi)有她的死訊傳來(lái)。對(duì)于這個(gè)人,廚房的全體人員都噤聲不提,她就此退出了廚房的社交圈。
這些陰慘的色彩,并沒(méi)有使廚房變得恐怖,相反,它在某一方面,更加強(qiáng)了凝聚力。因?yàn)樯衩亍⑽纯芍Ⅲ@懼而越團(tuán)越緊,身體擠著身體,由此產(chǎn)生出一股子相濡以沫的氣氛,增添了這里的溫濕度。這種溫濕度特別適合小的物種,一些渺小的情感也在這里滋生滋長(zhǎng)著。比如說(shuō),受委屈的小孩子通常是在這里哭泣。與兄弟口角;受了母親的責(zé)打;或是弄堂里遭到欺壓,弄堂是個(gè)強(qiáng)食弱肉的社會(huì);再有,同學(xué)間的誣陷和背叛,等等,諸如此類(lèi)的冤情,翻是翻不過(guò)來(lái)了,總要有個(gè)地方訴說(shuō)吧!那么,就到這里來(lái)!這里的人閱歷都很深,而且是在最底層,用她們的眼睛看,那么點(diǎn)芝麻綠豆,算得上什么呢?哭一會(huì)兒,再重整旗鼓,回到弄堂,學(xué)校,抑或同胞兄弟的社會(huì)里,人生總是要面對(duì)的。吃偏食和私食也是在這里,多子女的家庭,愛(ài)是有偏頗的,要是在主仆之間,這卻是類(lèi)似私情一般了。人總是有偏疼的一個(gè),那么就叫到廚房來(lái),從碗櫥的角落里,拿出私藏下的半只咸蛋,兩片夾心肉,一個(gè)雞腿,或者面糊里調(diào)了白糖,用肥肉膘開(kāi)一只油鍋,煎一張?zhí)痫灐4藭r(shí)此刻,聲音和動(dòng)作都是細(xì)小而且輕悄的,躡著手腳,以防被家中其他孩子看見(jiàn)。在這機(jī)密的氣氛里,生出貼己之心。一大一小,一個(gè)坐,一個(gè)立,也不說(shuō)什么,偶爾對(duì)一下眼睛,便有無(wú)限的柔情交流。小孩子不被首肯的賓客也是在這里接待,這里綱紀(jì)松懈,小孩子倒有了人權(quán)。他們談一些玻璃彈子或者香煙刮片的交易;磋商玩意兒的技藝;搬弄口舌——上海弄堂里的流言實(shí)在是從嫩到熟,從熟到衰,收割后的老茬子地里再播下種,這時(shí)節(jié),還是些流言的芽?jī)耗兀∷麄償D在這里,也不怕炒鍋里濺出來(lái)的油花燙了,水斗底下的積水濕了鞋,女人們則將他們驅(qū)來(lái)趕去。就像動(dòng)物趨光趨熱的本能,暮色降臨,他們還不想分手,弄堂里暗沉沉的,他們便奔這里來(lái)了。這一盞蒙了灰和油膩的電燈,投下的光,簡(jiǎn)直就是人間的暖意,藏污納垢,卻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這些小蘿卜頭。小小的,薄薄的,幾乎透得光,就像皮影戲里驢皮做的人兒,交互錯(cuò)蹤,一會(huì)兒疊起,一會(huì)兒散開(kāi)。
有多少小孩子從這里流淌過(guò)去,留下凸凸凹凹的印記,然后又彌合起來(lái)。這些小巧玲瓏的凹痕,以及迅速的彌合,使空間呈現(xiàn)出活躍變化的形態(tài)。他們的小身子和小悲歡,雖然是小小的體積,分量又輕,可是具有穿透力,或者說(shuō)滲透力,從漫漫時(shí)光滴漏進(jìn)來(lái),給記憶鍍上亮閃閃的斑點(diǎn)。他們的正史都記錄在前面的和爸爸媽媽共處的居室里,還有弄口的小學(xué)校,在這背陰的脫離了社會(huì)轄制的廚房里,寫(xiě)下的是野史,逸聞?shì)W事,不上臺(tái)面,可是誰(shuí)知道呢?也許這也是重要的,那些雜七雜八的怪力亂神的鬼話,那些傷心的淚水,鬼鬼祟祟吃到嘴里的偏食,也是一種知識(shí)呢,填補(bǔ)著正統(tǒng)教育的盲區(qū)。每一個(gè)時(shí)代里的正統(tǒng)都有著它的狹隘性,需要一些旁門(mén)左道開(kāi)拓視野。
從這里走過(guò)的孩子形形色色,來(lái)自社會(huì)各階層。有一些穿著體面,膚如凝脂,根本和這廚房的環(huán)境不合契,可他們也來(lái)到這里。另一個(gè)極端是,破衣?tīng)€衫,面露菜瓜色,眼睛躲避著灶上鍋里的吃食,是為抗拒誘惑,和這廚房也不大合契。他們帶來(lái)了平等的色彩,使這廚房變成大同世界。事實(shí)上,廚房是一個(gè)中等社會(huì),它的生活水準(zhǔn)是溫飽略有剩余。小孩子沒(méi)什么絕色的,但總歸平頭整臉;衣著平庸,尚可算得上整齊;吃的呢,絕不會(huì)餓著,只是有些饞;家里有些規(guī)矩,卻還不至于完全喪失自由。他們,就是廚房的小主人。
那個(gè)寧波籍的小男孩子,他的橄欖型的頭顱,時(shí)常拓開(kāi)著記憶的空間,出自老練的手筆,凌空一劃,再一收。這種頭型是經(jīng)過(guò)多少千年的進(jìn)化,就像是一種美麗的陶罐,記錄了人類(lèi)文明的歷史。他是一個(gè)有歷史感的小男孩子,他的頭型,口音,還有衣服上時(shí)常散發(fā)出的某一種食物的氣味,都透露出悠久的遺傳。他有著非凡的急智,他機(jī)敏的呀,不像人,而像一種動(dòng)物,不同的是,這機(jī)敏于他是表現(xiàn)在語(yǔ)言上,這就是文明了。他能夠立刻抓住對(duì)方說(shuō)話里的漏洞,作出反應(yīng),稱(chēng)得上“靜若處子,動(dòng)若脫兔”。我們每個(gè)人,都逃不過(guò)他的洞察,然后被他的語(yǔ)言剝開(kāi)偽裝——假如說(shuō)小孩子也有偽裝的話。像他這樣,乳臭未干,并沒(méi)經(jīng)什么世事,只能用天賦來(lái)解釋?zhuān)熨x其實(shí)是歷史的積淀。他的手,那纖長(zhǎng)的十指,也是文明進(jìn)化的果實(shí),制作起游戲的工具,簡(jiǎn)直就是天工開(kāi)物,彈弓,彈丸,三角和四角的刮片,蟈蟈籠,鐵環(huán),俗稱(chēng)“賤骨頭”的陀螺。這雙手對(duì)小動(dòng)物的愛(ài)撫也很溫柔,我說(shuō)的小動(dòng)物就是廚房地板縫里的那些居民,蟲(chóng)子啊什么的,還有來(lái)去不定的野貓。他的手在野貓的胸脯上輕輕撓一撓,對(duì)生靈很有經(jīng)驗(yàn)的樣子。和他的溫柔成為匹對(duì)的是他有同等程度的殘酷,他生生把一條蚯蚓掐成兩段,放在手掌心上看它們各自扭動(dòng),變成兩條蚯蚓。西瓜蟲(chóng)也是生生地掰開(kāi)來(lái),看它小小的白肚腹里有什么。這溫柔和殘酷也來(lái)自原始遺傳,都可追溯到上古,物種之間有著另一種強(qiáng)弱優(yōu)劣的排序,經(jīng)過(guò)漫長(zhǎng)的演變,一種勝出的生物與一種敗出的生物又一次邂逅,彼此認(rèn)不得對(duì)方,又覺(jué)似曾相識(shí)。這是小孩子中的歷史動(dòng)物,還有一類(lèi)完全沒(méi)有歷史的產(chǎn)物,那就是我。
回望過(guò)去,我?guī)缀蹩床灰?jiàn)自己的面目,這就是沒(méi)有來(lái)歷的人的淺近的性質(zhì),還沒(méi)有脫離主觀性,成為客觀的存在。不像那男孩,他的存在不可質(zhì)疑,一下子揳進(jìn)記憶之中,拔也拔不出來(lái)。我的印記是游離的,一會(huì)兒浮現(xiàn)出來(lái),一會(huì)兒泯滅在混沌里。我還來(lái)不及在鑿開(kāi)時(shí)間隧道,于是就無(wú)法在空間里佇留,這就是時(shí)間和空間相互的依附作用。具體到現(xiàn)場(chǎng),我好像是被那歷史男孩一口一口吞噬的,他無(wú)情地譏誚我的口音,這是一種沒(méi)有鄉(xiāng)音的口音。我從小說(shuō)普通話,一種基于北方語(yǔ)系,然后由政治生活再造,為適合傳播刪節(jié)與簡(jiǎn)化韻和聲的語(yǔ)言。為了學(xué)習(xí)上海話,我又損失了普通話的標(biāo)準(zhǔn),屢次在上海話那個(gè)短促的入聲上絆倒,終于生出口吃的毛病。然后我又在廚房這個(gè)五方雜居的地方吸納各地鄉(xiāng)音,幫傭女人的揚(yáng)州話,無(wú)錫話,奶媽的不知什么地方的話,甚至包括那男孩的寧波話,我吸納的都是各路鄉(xiāng)音的糟粕,因?yàn)槲腋静欢檬裁词呛迷挘裁词秦挕2患兞嫉恼Z(yǔ)言,就成了我這個(gè)新移民的羞恥的徽記。作為一個(gè)小孩子,我最大的缺陷是玩不來(lái)弄堂游戲,造房子,跳皮筋,捉人,“老狼老狼幾點(diǎn)了”……全是以?xún)?yōu)勝劣汰的方式進(jìn)行,我一上來(lái)就出局,只得站在一邊看,然后回到廚房呆著。所以,廚房里也染了小孩子我的寂寞,還有屈辱。這屈辱也是他,歷史男孩給予的,他取笑我的挫折,我的挫折作了他的笑料。我的悲傷,滴水穿巖一般從時(shí)光里滲漏過(guò)來(lái),轉(zhuǎn)眼間消除了痕跡。沒(méi)有歷史的拖尾,它轉(zhuǎn)瞬即逝。我只得依靠一種媒介,文字,來(lái)輔助它留下印記,讓主觀變成客觀。
在歷史男孩和我中間,還有一個(gè)過(guò)渡性的人物,我稱(chēng)之為近代女孩。她的形態(tài)比我們倆都光鮮,這就是這城市的近代色彩。她不像男孩那么枝蔓繁多,牽絲攀藤,也不像我,單薄,孱弱,而且形狀不定,一切有待塑造,她線條流利,表面光潔,附著一些織物,猶如蟬翼,從她輪廓周邊派生出來(lái)。她比我和男孩更物質(zhì)化,這些物質(zhì)性的因素幫助撐開(kāi)了空間,使她獲得可觀的占位。于是,她的人,包括肉身,都有了另一種工業(yè)化材質(zhì)的質(zhì)地,哪一種材質(zhì)?琺瑯瓷,發(fā)出人工的光澤。是記憶上的一片螺鈿,打磨得光滑透亮。她也是游戲高手,她的游戲是另一路的,不像歷史男孩那么具有草根氣,而是帶了都會(huì)的聲色,所以叫她近代女孩嘛!比如,挑十字繡,在一塊網(wǎng)格細(xì)麻紗上,穿了花線的針在每四個(gè)一組的格子里對(duì)挑一個(gè)十字,一個(gè)十字又一個(gè)十字組成圖案。她煞有介事地一針一針挑著,就像一個(gè)淑女,一個(gè)住在租界上,因?yàn)樯硖幃愖迦酥腥鄙倩橐鰴C(jī)會(huì),貽誤了青春的外國(guó)淑女。她的玩意兒也帶著工業(yè)革命的空氣,比如雙股的牛皮筋上,穿著一列機(jī)制線團(tuán)的木頭線軸,可以增添牛皮筋的彈性,隨著雙腳的舞蹈上下翻飛。再則,她會(huì)唱“小弟弟小妹妹讓開(kāi)點(diǎn),敲碎了玻璃老價(jià)鈿”……幸好有了她,我和男孩才不至于出現(xiàn)斷裂,而是有了銜接。我們?nèi)齻€(gè)人,接成了歷史的鏈條,就像小女孩子用樹(shù)葉的莖給自己做的項(xiàng)鏈——我們將一片樹(shù)葉,捋得只剩下一條莖,然后萬(wàn)般小心地折成一小段,一小段,段和段之間由拉出的細(xì)絲串著,如同蛛絲,在空中搖曳,一不小心就斷了。這就是我們身上的歷史痕跡。
在我們?nèi)齻€(gè)之外,自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小孩,也穿行在廚房里,可是由于缺少主要事跡,多少是模糊了,成為記憶的碎屑,彌漫在空氣里,改變著光影和色彩。所以,他們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其實(shí)他們也并不是那么沒(méi)性格,只是被我們這三個(gè)遮蔽了。他們不像我們?nèi)齻€(gè)那么有涵意,這含意在當(dāng)時(shí)不覺(jué)得,走過(guò)了漫長(zhǎng)的時(shí)間,漸漸地凸現(xiàn)起來(lái),這是記憶的選擇。當(dāng)然不那么公平,可是就像常言道: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記憶也是,誰(shuí)的記憶誰(shuí)有發(fā)言權(quán),誰(shuí)讓是我來(lái)記憶這一切呢?那些沙粒似的小孩子,他們的形狀只得湮滅在大人物的陰影之下了。可他們還是搖曳著氣流,在某種程度上,修改與描畫(huà)著他人記憶的圖景。
而我必須要說(shuō)一說(shuō)那兩個(gè)小孩子,一個(gè)是姐姐,一個(gè)是弟弟。他們是某一家的小客人,時(shí)常前來(lái)造訪,而我們彼此都沒(méi)有留心對(duì)方。當(dāng)時(shí)間進(jìn)行到某一個(gè)點(diǎn)上,也就是通常說(shuō)的契機(jī)的意思,我們和他們忽然地彼此注意。是一個(gè)寒假,天氣陰冷,已經(jīng)不適合做弄堂里的游戲,我們都蜷縮在廚房里。朝北的廚房,又潮濕,談不上有多少暖和,可是認(rèn)識(shí)新朋友使彼此激動(dòng),親密的感情一分鐘一分鐘地遞進(jìn)著。轉(zhuǎn)眼過(guò)了中午,主人家留了飯,又過(guò)了下午,主人家也留了飯,夜晚降臨,主人家繼而留了宿。第二天,眾人又在廚房聚首。只有公用廚房,我們這些來(lái)自各個(gè)家庭的小孩子才可以聚會(huì)。來(lái)自另外的街區(qū),另外的學(xué)校,以及另外的不為我們熟悉的生活里的孩子,他們,嚴(yán)格地說(shuō),只是他們中的一個(gè),那個(gè)姐姐,她身上異樣的氣質(zhì),強(qiáng)烈地吸引了我們。我們眼界很窄,沒(méi)什么見(jiàn)識(shí),他們,或者說(shuō)是她,是我們從未接觸過(guò)的一種類(lèi)型。
我應(yīng)該把她放在哪一個(gè)歷史階段上呢?上古,近代,或者如我,來(lái)不及創(chuàng)造歷史。好像都不對(duì),都不適合她,她兀自立于歷史之外。也許,原因只是,她不屬于我所認(rèn)識(shí)的歷史,而是來(lái)自另一個(gè)歷史。每一個(gè)街區(qū),每一種生活,甚至每一種房子的結(jié)構(gòu)里,都有著自己的完整的歷史,每一種歷史的體現(xiàn)都不相同,各有各的生動(dòng)性。她也是有光澤的,但不是琺瑯瓷,而是真正的貝類(lèi)。真正的貝類(lèi)在于它其實(shí)不像人工打磨的那么有亮度,也不夠鮮麗,而是有一些暗。但組織密度更高,于是有了深度和厚度。她就是這么樣散發(fā)著幽暗的光,這光仿佛來(lái)自一個(gè)活躍的源頭,使她有一種流動(dòng)的性質(zhì)。她就像舟筏,被記憶載著,穿越時(shí)光而來(lái)。
她習(xí)慣用一塊頭巾裹著頭,頭巾沿了發(fā)際向兩邊去,在下頜交叉,再繞到頸后,打一個(gè)結(jié)實(shí)的活結(jié)。透過(guò)圍巾的形狀,可看出她纖巧的頭顱,頭顱上梳得很光的頭發(fā)和編得很緊的發(fā)辮。她就這樣裹著頭巾,手插在棉襖口袋里。她的裹在紅格子棉襖里的身子,骨骼勻稱(chēng)。她直直地站在我們中間,與我們說(shuō)話。她的臉色和身姿,一點(diǎn)沒(méi)有寒冷的樣子,不像她的弟弟,嘴唇青白,瑟縮在煤氣灶旁邊。倘若煤氣灶上正好在燒煮東西,他就將手伸過(guò)去取暖,很快又被燎著,趕緊縮一下。這是一個(gè)孱弱的男孩,她卻很健康,不僅她不感到冷,而且令別人也熱烘烘的。這是一種格外結(jié)實(shí)的體質(zhì),內(nèi)分泌平衡。我們熱情地看著她,懷著欣賞和羨慕,不放過(guò)她的一舉一動(dòng)。而且很奇怪的,我們女孩比他們男孩更受她的吸引,在這個(gè)年齡階段,女性氣質(zhì)更為同性所敏感,男孩還沒(méi)有開(kāi)蒙呢!
一天過(guò)去了,我們還不想放她走,又過(guò)了一天,下一天,依然沒(méi)走。顯然她在我們中間也如魚(yú)得水,臉色越來(lái)越紅潤(rùn),神氣越來(lái)越飛揚(yáng)。在此同時(shí),她的弟弟卻日益萎縮,蒼白和虛弱。他就像一個(gè)雪人,在爐火邊上消融下去,他的人都小了一圈。主人家終于發(fā)出逐客令,女孩子只當(dāng)耳旁風(fēng),她的鎮(zhèn)定也是少見(jiàn)的。就在此時(shí),寒流來(lái)臨,風(fēng)在弄堂里激蕩,暴冷使我們更加興奮,好像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要發(fā)生了,連她弟弟的眼瞼下面也生出紅暈,漸漸蔓延了整個(gè)臉頰。最后,事情的結(jié)束是,姐弟倆的父母來(lái)到,將他們帶走了。此時(shí),弟弟已在高熱中,其實(shí)他從一開(kāi)始就病了,卻沒(méi)有人發(fā)覺(jué),注意力都在姐姐身上。在魅力四射的姐姐的陰影下生活,他必須要有隱忍的性格。誰(shuí)知道呢,在他弱小的身體里,正進(jìn)行著一場(chǎng)什么樣的抵抗。他幾乎要消失了蹤跡,他無(wú)聲無(wú)息地,沒(méi)有一點(diǎn)響動(dòng),要不是后來(lái)發(fā)生的事情,他就算完全地退出記憶。后來(lái)發(fā)生的事情是,他死了,不是在這一場(chǎng)病中,也不是在他身歷的無(wú)數(shù)病中,這一個(gè)多病的孩子,很平靜地死于無(wú)病無(wú)災(zāi)之中。兒童猝死至今還是一個(gè)謎,沒(méi)有謎底。他的死,在人們的記憶中砸開(kāi)一個(gè)窟窿,邊緣迸裂,猶如金石相撞。
這是小孩子里的死者,大人呢?你們不會(huì)猜到,大人中的死者是那個(gè)最年輕結(jié)實(shí)的奶媽。顢頇的她,就這樣夯進(jìn)記憶,形成一個(gè)凹坑。這就是死亡的永恒性,死者就此停滯在時(shí)光中,占領(lǐng)了空間。要是依那幫傭的女人的宿命論來(lái)說(shuō),廚房這地方不干凈,出現(xiàn)過(guò)黃鼠狼,還有老女人來(lái)抱怨鬼叫擾了她睡眠。然而,這又說(shuō)明廚房是有淵源的地方。有淵源的地方,總是生生息息,于是,萬(wàn)象生羅。所以,我說(shuō)它肥沃,那油膩泡軟了的地板,什么長(zhǎng)不出來(lái)!
有幾次,房管所木工來(lái)修地板,他們拆去腐朽的木板,鉆進(jìn)地板下面,敲打修理龍骨。里面黑沉沉的,堆積著漏進(jìn)地板縫的陳年舊物,筷子,勺子,發(fā)卡,頂針,肥皂頭,白菜頭,肉骨頭,這就是廚房的地質(zhì)層。再后來(lái),連龍骨也朽爛了,房管所徹底拆除地板,推來(lái)碎石,鋪上了水泥。廚房里的木質(zhì)的膏腴的霉氣味換上了水泥的涼森氣,別小看氣味了,氣味改變了這間廚房的屬性,它不再是柔軟的肉感的屬性,而是冷和硬。這就像是一種蛻,從此,小孩子都長(zhǎng)大。大人呢,趨向老,然后,是死亡,不是那樣不期然的夭折,而是壽終正寢。
2007年5月18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