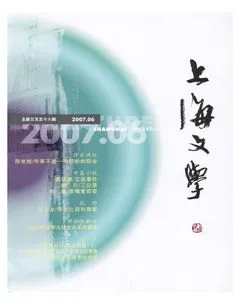在小說彌留之際
時間:2007.2.6
地點(diǎn):上海青松城大酒店1430號房間
聊天者:蘇童 陳村
陳村:隨便瞎聊。聊到可以寫出一萬字就行了。今天吃飯的時候在想,我對一個問題很感興趣,我會碰到一些寫小說有障礙的,就是你覺得哪些地方很擅長,很會寫,哪些地方不大會寫。作家們不怎么說自己哪些地方寫起來要頭痛的。就像我這種人,人物一多我很頭痛。寫小說,我弄出三四個人蠻好的,要是弄出十三四個人我就太頭昏了。像一個導(dǎo)演啊在舞臺上就不知道讓那些演員干什么。每個人都應(yīng)干事兒嘛,你不能讓一個演員站上去就不動了,總要給他一點(diǎn)任務(wù),那么人一多我就犯糊涂。還有一個呢就是遠(yuǎn)不如你了,你是很少見的能夠?qū)懩杏謱懪摹R话隳腥藢懩腥伺藢懪恕E藢懗鰜淼哪腥艘膊缓谩0ィ悄愫芷婀帜軐懗瞿腥艘材軐懗雠恕N铱吹綄懪祟^也痛。
蘇童:這頭一個問題其實(shí)要分開來說,首先與年齡有關(guān),比如說我年輕的時候確實(shí)血?dú)夥絼偅瑥膩頉]有感覺到小說會有寫不下去的時刻,所謂障礙幾乎是不存在的。
陳村:那個時候從來是不怕,也沒去想“應(yīng)該”怎么寫。
蘇童:那個時候是天不怕地不怕,主要是魯莽的寫作沖動決定了一篇篇小說的開始,其實(shí)對小說最后的面目是沒有預(yù)期的,也沒有過多精細(xì)的設(shè)計。小說的人物,基本上是由敘述者決定,他遇到誰,誰就粉墨登場,敘述者不需要了,那人物有可能突然消失。現(xiàn)在看那時候的作品,一方面對人物是弱化處理,另一方面,對自己塑造人物的能力,也是沒什么自省的。所以盲目自信,開了頭就可以寫下去,唯一的破壞性的舉動就是這一頁稿紙覺得涂改太多了,我就把它撕掉。那個時候都是稿紙么。
陳村:我也是,改得看不清楚了重寫。我最怕抄稿子。
蘇童:那個時候我是部分重寫。寫不下去的記憶,這是幾乎沒有的。即使有的寫到中途你覺得,唉,不是這個味道,哪不對頭,那先放在一邊也有,但是這種現(xiàn)象不是太多。有時候這個稿子就是說扔了就扔了。有時候過了一陣找來再看,發(fā)現(xiàn)一個角度,或者拉一個人物出來,一下子感覺小說又獲得活力了,可以推進(jìn)了,那么又會寫下去。我有幾篇小說就是這樣。好像《南方的墮落》就是這樣的。扔掉了很長時間,那年1989年正好我女兒出生。我太太產(chǎn)假滿月了,滿了要去上班了,我回去要盡一點(diǎn)義務(wù)啊。那個時候我在南京。請了幾個月產(chǎn)假回蘇州去搖孩子。孩子睡覺我就在那邊寫,就是把以前一個扔掉的稿子接起來寫,但是這個例子很特別。現(xiàn)在看起來,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一旦扔下,再拿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因?yàn)橛锌赡軘⑹龇较蝈e了,這個一錯就錯到底了,一條道走到黑,是無法修正的吧?只好等待收獲錯誤,收獲意外了。
陳村:寫長篇的時候要維持統(tǒng)一的敘述語調(diào),有時候還靠信心。寫著寫著會覺得這樣寫下去對嗎?
蘇童:一部長篇小說自然要依賴所謂大構(gòu)思,對長篇的信心其實(shí)就是對“大”的信心,“大”不排斥精巧和細(xì)膩的敘述,敘述是有技術(shù)含量的,姑且把敘述叫做“小”,但是再美好的敘述也可能會被這個“大”構(gòu)思歧視的,不是敘述背叛構(gòu)思,就是構(gòu)思否定敘述,長篇的辯證法就是這大和小的辯證法。長篇的麻煩,就在于“小”做成“大”的麻煩。如果寫不下去,那就是你發(fā)現(xiàn)“小”越來越小,不能壘起“大”了。最終無所適從,最終你不知道是大出了問題,還是小出了問題,干脆不管了,什么大和小,也許沒什么長篇的辯證法,只有一個直覺的引導(dǎo)。
陳村:所謂舒服不舒服。
蘇童:對,就是舒服不舒服。我有一個毛病,就是不能忍受連篇累牘的對話,哪怕對話的功效再好。在我的所有的小說當(dāng)中,長篇小說當(dāng)中,我不能忍受人物之間超過一頁的長時間的對話。這個是毛病。就是不覺得小說可以這樣子。用這么長的篇幅去對話,讓敘述一邊站著。
陳村:寫兩個人的對話。
蘇童:寫兩個人的對話,篇幅也嚴(yán)格控制。這肯定是我的偏見。沒有什么依據(jù)。就像我到現(xiàn)在不知道為什么特別怕用雙引號。已經(jīng)養(yǎng)成這個習(xí)慣了,到現(xiàn)在也不想改。人到中年以后自己對自己會有比較清醒的認(rèn)識,現(xiàn)在會寫不下去,要勇于承認(rèn)障礙,學(xué)會對待這種障礙。寫不下去往往有一些原因,很多時候,倒并不是因?yàn)閷θ宋锏那巴竟适碌淖呦蚋械矫H唬『檬锹吠咎啵悴恢滥臈l路是最好的。
陳村:歧路亡羊。
蘇童:對,就是這么一個感覺。或者說是因?yàn)轭^緒太多了,纏線了,突然覺得每一個頭緒都有可能精彩,那么也就不知道哪個是最精彩的。具體說,你自己營造一個故事,一個人物,結(jié)果使他們造反,在挑戰(zhàn)你的控制。你就慘了,似乎有亡國之痛,一切似乎一下走得很遠(yuǎn)了。是你的一部分,卻不在你控制之中了。
陳村:一放出去就出去了。
蘇童:對!他脫韁了,你本來以為是可以駕馭這匹馬。他媽的,一個不小心,怎么了,是個野馬!你收不回來,這時候會造成你的問題,你突然要停下來了。
陳村:短的呢容易掩飾這些。
蘇童:對,這些困境在短篇小說里頭不太容易出現(xiàn),因?yàn)槎唐≌f,首先我要的不多。要的不多,是一個局限,也是一個自由。它就是一唱三嘆。所謂的嘆是余音繞梁,你只要負(fù)責(zé)唱好。一唱,就那一唱。因?yàn)楫吘故悄且怀旧喜蝗菀着苷{(diào)。
陳村:它容易控制。
蘇童:短篇把你壓縮在某一個平靜安寧的軌道上。我覺得習(xí)慣了那種文字運(yùn)動,如果說短篇也是一種運(yùn)動的話。事故不會太多,享受就比較多。
陳村:那么覺得什么地方比較難寫?
蘇童:一堆人物攪在一起寫,最難,但是舉個例子,如果人物是鐵,如果能有一種磁石一樣的場景,人物就都自然聚攏了,一個個在一起比拼性格。當(dāng)然你要說寫一堆人物的,我覺得最完美的小說就是福克納的《我彌留之際》,是人物組合集體出動,一個最成功的范本。因?yàn)檫@個故事也很簡單,但是用母親的棺材做了磁石,家庭成員們就都被吸了上來,很自然攪合在一起。
一個家庭的人物組合在當(dāng)時是蠻吸引人的。用人物命名來做一個章節(jié),而且每個人物就是這樣展開,連環(huán)的,素描般的。
陳村:它的命運(yùn)呢其實(shí)是有一點(diǎn)脫軌的。但是它也不走遠(yuǎn)。
蘇童:像這樣的作品有時候你要做一個很漫長的構(gòu)思。有時候小說很順暢,其實(shí)是你本身的構(gòu)思天衣無縫。就是沒什么漏洞,它不會進(jìn)水,它不會滲水。就像福克納的構(gòu)思永遠(yuǎn)能繁能簡,《彌留》要寫很多人物,但是他的故事的推進(jìn)的力量其實(shí)非常單純,就是要給母親去送葬,眾人的一段旅程。這個線索這樣扯出來,行云流水,圍繞著這個線索,人物就一涌而上了。
陳村:而且要求還很高,因沒什么故事,如果說你人物寫不好那就什么都沒有了。
蘇童:對。我們現(xiàn)在的興趣,無論如何轉(zhuǎn)變,不能離開人物。我一直在說我在后退。這個跟進(jìn)步、退步、先鋒、古典什么的是無關(guān)的。我說的退是敘述上的后撤,撤回古典陣營,扛起一面人物的大旗再說,就是說你對人物的依賴程度,有時候基本上是一個生命之水。我覺得像我也好外面我們這幫同行也好,在寫到一定的時候都會有一個強(qiáng)烈的意識,就是為自己的人物擔(dān)憂。這個人物可能不可能是一個新的,或者是有意義的,有文學(xué)史意義的經(jīng)典形象。第一要會做這個審閱、盤算或者是覺得推敲我寫的人物到底……
陳村:到底有意思嗎?
蘇童:對,意思大不大。尤其當(dāng)你要寫一個長篇小說更是在這樣。世界上這么多人,你卻還要找人,這個人物在你周圍,只是隱蔽起來了,所以對你來說永遠(yuǎn)是在找一個失蹤者。問題就是在于找的時間或者是找的方向。找,就是推門,黑房間“啪”那么一推。進(jìn)去都是黑房間,沒有燈,你要把他揪出來,打扮好了,才有燈光,別人也好,你也好,才可以判斷,這個人物是不是大家需要的失蹤者。
陳村:像馬原講得蠻有意思的。馬原講他寫小說呢,他說第一句話非常要緊,他說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它第一句話出來,第二句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跟著一圈一圈的倒下。
蘇童:對。對第一句話的依賴其實(shí)是對節(jié)奏的依賴,怎么說呢,是對一種基調(diào)的依賴。
陳村:基調(diào),非常好。
蘇童:是基調(diào)。
陳村:有時候會非常不一樣。如果你一開始寫的一句話錯的,寫著寫著就會越來越不舒服。
蘇童:我覺得以前的古典作家不在乎的,上來就是某某年幾月幾號,某某人在某地點(diǎn)干什么。現(xiàn)在的作家,我發(fā)覺對第一句話的依賴程度有點(diǎn)瘋狂。就像現(xiàn)在最火的帕慕克,第一句話都很講究,都特別特別的講究。
陳村:第一句話第一個場景出來的時候好像都賦予它更多的。
蘇童:對。第一句話我覺得就是找調(diào),調(diào)一下找到了,他才能有信心這樣寫下去。
陳村:以前是啊,像剛才講的那個《我彌留之際》,我開頭看了好多頁,我不知道他們要干什么
蘇童:但是到最后我們發(fā)現(xiàn)其實(shí)是可以概括的。其實(shí)到最后是一個背叛。從愛到背叛,從哀悼到遺忘,冠冕堂皇。父親最后是去娶了一個新媳婦,所有的孩子送走死去的母親,迎接了一個陌生的母親。這個我覺得是整個構(gòu)思,他到最后很牛的這個。你看這個小說從結(jié)構(gòu)上來說典型的是樹枝式的。這個事件,那口棺材,其實(shí)真的是一個樹干,這個樹干不需要很關(guān)心嘛。只要很簡單的送棺路線,事情自然發(fā)生。然后旁邊就是那些樹枝,就是那些孩子和丈夫。最后樹枝樹葉拋下樹干,背叛了樹。
陳村:我想問的是,我們換個場景講,比如說紅軍長征,我們寫長征的那么多作品,寫的都是怎么過大渡河啊過瀘定橋啊強(qiáng)占臘子口啊,都是一路的艱難險阻,有點(diǎn)像《西游記》里面那種九九八十一難。打過去怎么樣怎么樣。但是在我們所描寫的路途當(dāng)中,這么漫長的路途當(dāng)中很少看到一些鮮明的形象出現(xiàn),人是虛的。我們用一些總體的概括而不是用個體的描繪來講一個事情。福克納的作品中,其實(shí)像一個由頭一樣,就是說給他一個好像虛假的出發(fā),就叫你完成這個主線的任務(wù)。就像足球場上有一個球一樣。沒球大家亂奔你覺得大家很荒誕啊。有球,那么他們就走過去了。
蘇童:對。眾多人物在一部小說當(dāng)中均衡塑造,我覺得是非常非常耗腦筋,但是《彌留》恰好是第一步走好。用單純的一個事件做一個樹干,然后把所有的故事人物掛在樹枝上。這種很簡單的結(jié)構(gòu)方式,產(chǎn)生了一個很震撼的作品。
陳村:有一些小說比較虛一點(diǎn)沒它那么實(shí)。像《紅樓夢》那樣,《紅樓夢》賈寶玉好像是要跟誰談戀愛一樣,其實(shí)不是這個東西。
蘇童:曹雪芹這個小說牛的是從虛到實(shí)。現(xiàn)代小說的筆法它引導(dǎo)人們從實(shí)到虛,是不是?然后這個小說就是倒過來,我就覺得大家之所以這么多年來贊美《紅樓夢》,確實(shí)是一個無法逾越的經(jīng)典。
陳村:而且它在兩界的措施非常自然。
蘇童:但是你也不能說曹雪芹的此前此后,因?yàn)槲覀儾恢溃麤]有第二部么。所以像這樣的小說想法,怎么說呢,有可能一個飛來峰,飛來的一個想法,你也很難說他的出手就是牛逼成這樣,因?yàn)槲覀儾恢浪侨绾蜗褚粋€當(dāng)代作家一樣,他要寫第一部然后第二部第三部。我們不知道會不會寫,因?yàn)槲覀兛础度远摹返哪欠N事。當(dāng)然我們不能說像《三言二拍》沒意思。但是《三言二拍》確實(shí)就是一個世俗生活,就是用世俗的腔調(diào)和世俗的態(tài)度去對待所有的關(guān)于世俗生活的,就是這樣的。所謂高低之處就在于此。
陳村:就是在《三言兩拍》中最后最多有點(diǎn)道德訓(xùn)誡。
蘇童:那時候最虛的境界就是鬼怪玄靈。但是這個《紅樓夢》的境界是講出路的,是自覺的靈魂探索。它從一開始就是暗示了關(guān)于生死問題。現(xiàn)在我們沒有辦法研究曹雪芹作為一個職業(yè)小說家他的心情,或者說當(dāng)他坐下來寫的時候的心情。是一種作家的心情還就是一個普通人的心情。這個是需要研究的,是因?yàn)樗鳛橐粋€作家的心情才導(dǎo)致他寫了這么一部非常牛的《紅樓夢》,還是我們說的有這樣一個身世的一個普通人的心情,記錄自己的人生,結(jié)果弄出來這么一個警世之作。所以像王朔老師說:一不小心寫了一個《紅樓夢》。我老覺得是曹雪芹一不小心寫了《紅樓夢》。
陳村:一開始,也許是一個真的事情,有根的,也許不便寫要把它模糊了。
蘇童:對,很懷疑當(dāng)時,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在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的時候他在開始寫這個八十回的時候,他到底是把自己看作誰,當(dāng)然那個時候沒有作家那么神圣的價值體系在他心里。他到底是要干什么,他是寫著好玩的,還是要傳世的,還是因?yàn)槲覀円郧罢f的有感而發(fā)。我覺得這不是一個他精心謀劃出來的東西。
陳村:它不是一個推理出來的一個東西。
蘇童:對。
陳村:我們評論家論文經(jīng)常是推理出來的,因?yàn)檫@樣所以那樣。寫小說的時候常常不是推理。因?yàn)樾≌f它是不可以用形式邏輯將它推理了的。我們還不大明白人的邏輯,小說也就難以邏輯。這個人因?yàn)闅⒘巳怂砸优堋L优苣噩F(xiàn)在交通發(fā)達(dá)所以他跑得很快,但是警察很多,所以又把他抓住。因?yàn)樗浴_@個推理出來的小說變成木乃伊小說了。它里邊必定會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因果,有符合我們?nèi)说奶幘车姆先说奶煨缘囊环N東西。小說中有些好,就比如你寫那個叫《妻妾成群》,你那個《妻妾成群》后來拍電影。對這個兩面我不講優(yōu)劣。其實(shí)一個是很干的電影,一個是很濕的小說。你那個小說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里面的感覺是濕漉漉的,有一種晦暗的,在墻角上長一點(diǎn)青苔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種情景,江南的。在這個小說里面我覺得做得比你后來的《我的帝王生涯》都要好,就是說,它里面似乎可以看到一種活的東西在滋生。
蘇童:它看得見。
陳村:很潤的就是,不是說我要去把它……
蘇童:因?yàn)樗喿x的愉悅帶來的很少,我覺得對于我來說也是,我也要求看得見。但小說在看得見之外更多的要想得透,想得通,想得到。這個是想。小說因?yàn)楦軐W(xué)跟這個別的什么東西不一樣。
陳村:它本來就是寫具體生活、形象的。
蘇童:對對。小說不要把它弄得那么高,把它無限地高端化。小說是一個什么東西,回歸傳統(tǒng)來說,我們都知道。以前的話本是干什么的,它就是完全給民間的消遣品么。完全是針對民間的。從來沒有說達(dá)官貴人文人雅士是小說的服務(wù)對象。
陳村:而且寫了小說還不敢署名。
蘇童:當(dāng)然這個我們是中國小說的那種源頭,那么西方小說一開始也是有非常大的輿論和娛樂功能的,是吧?你比方說法國小說它當(dāng)時的所謂所有的騎士小說浪漫小說。這個東西它完全就是消遣品,小說只是在發(fā)展過程當(dāng)中異化了,變成我們?nèi)缃窭斫獾男≌f,顯示它比較強(qiáng)大的功能。從某種意義說是意外。
陳村:我曾經(jīng)寫過一段文字,我就說其實(shí)從講故事來說呢,《十日談》啊《三言兩拍》就夠了。那時的手段技巧,對表述一個故事來講就足夠了。
蘇童:從小說的世俗性上來說這個已經(jīng)做到。我們當(dāng)然后面都是在重復(fù)。
陳村:就像我們現(xiàn)在喝茶的杯子。我們這個杯子呢其實(shí)它的功能也蠻好的。它沒什么太不好看也很有光澤,可用,它工藝已到一定水平了。但是做杯子的人是不甘心這樣的。我們就是做杯子的人。就是你總要想耍點(diǎn)花招,還要有些變化,或者說多一點(diǎn)點(diǎn)東西,所以呢一代一代的人在小說的敘述上花了很多的力氣,想逼近“人”,所以變成了現(xiàn)在這樣子。
蘇童:換句話說我們家具永遠(yuǎn)是家具。當(dāng)然我們現(xiàn)在說明式家具多么的好多么的大氣,清式家具多么的雕琢。這也是一個時代貼給另一個時代的標(biāo)簽,但它家具永遠(yuǎn)是家具。就像我們現(xiàn)在一樣的,對小說我想差不多也是一樣的,所以我一直比較反對這個,反對把小說的教化功能跟別的各種功能無限的提升,然后給小說施加壓力,給作家施加壓力。我覺得好像不是那么合理。
陳村:在這個里面有些困難就來自于那個所謂的俗的雅的,我加工到什么地步才是對了?當(dāng)然小說有很多寫法,也可以把它寫成不一樣,比如某一類人看到這語言很喜歡,另一類人看到故事喜歡,像那個《基督山伯爵》,覺得那個故事很過癮。
蘇童:小說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其實(shí)一直是個人見解。我一直比較相信,真正的作家其實(shí)你的終極目標(biāo)就是面對一個讀者,就是一個剎那一個相遇而已。我們不要把它細(xì)分了。那個布魯姆,寫西方正典的那個。我看他對經(jīng)典的解釋說得非常好。他說經(jīng)典就是也不可能讓你變得更好,也不可能讓你變得更壞,下面一句話就妙了微妙了,他說就是讓你更好地知道如何來利用和品嘗一個人的孤獨(dú)。他說經(jīng)典教會你這個。這個話我覺得是有道理。他完全否定了所謂對某一部經(jīng)典小說無限的要求,他最后落實(shí)到一個人對一個人。而且甚至落實(shí)到孤獨(dú)上面。有大量的文本可以說明。卡夫卡,你現(xiàn)在讀卡夫卡,我們現(xiàn)在給他生發(fā)出無限的后現(xiàn)代派的意義。其實(shí)這就是一個孤獨(dú)到頂?shù)囊粋€人的文本。
陳村:而且那個也就是說,一個好好的作者在跟你談的時候,他談的必是一個人的感受。
蘇童:對對。最后經(jīng)典的意義很明顯,還是從個人到個人。這個空間其實(shí)非常非常之狹窄。遠(yuǎn)遠(yuǎn)沒有我們現(xiàn)在所描述的那么一種宏大意義,其實(shí)并不存在那種意義。所以我覺得這個話說得特別好。
陳村:我技術(shù)上講,覺得寫過那么多年小說,大家用心一點(diǎn),從技術(shù)上講都沒許多困難。你要編一個故事兩個人物,把這個故事編圓了,這個大家都會做。但有一種我們不能掌握看不見的東西。說大師吧不講我們。大師也不是說一篇比一篇寫得好。按理說他經(jīng)驗(yàn)更多啊,他手法更純熟,他知道更多東西,他應(yīng)該在下篇更好吧。但就沒有。下篇跟那個劉翔跑一樣的,你不能指望他每次都破記錄。
蘇童:福克納的《圣殿》就寫得完全像是報紙上的。有時候也正常,一個大作家給小報寫,也是藝術(shù)探險,成功不成功是另一回事。我覺得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在他一生保持積極向上,有時消極和積極是混淆的。所以有時候我很理解你這幾年不寫作,因?yàn)閷懙胶髞砦窇衷絹碓蕉唷N窇衷絹碓蕉啵且环矫妫€有你自己各種各樣生活當(dāng)中實(shí)際原因。我覺得還有一個最令人憔悴的,就是寫到后來你會覺得空虛。
陳村:問自己,你為什么要去寫它呢?
蘇童:會有這個空虛。然后這樣的一個空虛還會造成自我質(zhì)詢,你寫這一部或者好多年前這一部,哦,這個短篇我自己現(xiàn)在看了真喜歡,那你再來第二篇它的意義在哪里?好多是來自于這樣的疑惑。那種疑惑,最后讓你陷入虛無。
陳村:是有一種慣性。比如我一直在寫小說,一直寫一直寫一直寫呢,我明天不會問我為什么要寫小說。反正就是慣性就寫下去了。
蘇童:對。
陳村:當(dāng)你停下來的時候,再開始,就問為什么。
蘇童:所以作家真的要干什么不能多問為什么。為什么是一個非常害人的事,對于一個人的生活來說,問為什么是悲劇。不要問為什么,學(xué)會不問為什么這才牛逼。
陳村:你我第一次寫小說的時候也沒有問為什么。
蘇童:所以我覺得好多地方是生理需要,我覺得寫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生理需要。生理需要不要問為什么。
陳村:中間有一個差別,就是當(dāng)年有一種要把它寫下來的強(qiáng)烈的欲望。今天這種欲望不一樣了。對我來說,今天就沒有一種強(qiáng)烈的愿望要把什么東西……
蘇童:我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因?yàn)檫@個意義是壓倒一切嘛,或者你覺得這個故事是太輝煌了。太偉大了。
陳村:我就講那種我自己的經(jīng)歷。年輕時候你什么都不問了,什么技巧啊什么語言啊什么的你不管,你只想把這個事情這個人寫出來。到后來呢,你寫著寫著就來東西了,有產(chǎn)了,你覺得應(yīng)該有一個合理的結(jié)構(gòu),然后用一個什么什么的。開始將一種技術(shù)的東西加進(jìn)去,再寫下去呢再加。我在停掉小說的以前,大概80年代末……
蘇童:《鮮花和》是最后一篇了。
陳村:《鮮花和》其實(shí)已經(jīng)是一個例外了。我在那個以前,到1989年以前幾乎不寫小說了。后來寫過一兩個短篇,都是被人家逼出來的。人家《收獲》說要什么的,我就給人家寫一篇吧,《臨終關(guān)懷》。那個時候的我有點(diǎn)作怪。我蠻喜歡那種不太寫實(shí)像西方有點(diǎn)抽象意義的小說。可這種小說再寫再寫,你會發(fā)現(xiàn)不對了。本來小說我就講是一個具象的東西啊,本來可以腳踏實(shí)地的。那種具象的東西都逐漸被我抽掉了,那么就變成了一個半幻想半真實(shí)的一個故事。我寫過一串這樣的短篇,寫到后來發(fā)現(xiàn)不對了。寫到后來比那篇《死》要遠(yuǎn),寫過《起子和他的五幕夢》、《上街走走》、《F,F(xiàn),F(xiàn)》等。其實(shí)寫到《象》的時候我已經(jīng)不愿意好好說話了。是用倒敘在說。《象》變成像一個人在說,其實(shí)你已經(jīng)無意好好講故事了。可能跟我這人性格有關(guān),寫小說老那么寫我會煩,我又不是巴爾扎克。
蘇童:對。
陳村:用一種辦法寫所有人的故事我會煩。寫那個《一天》,寫了一些后,這個稿子被我扔下一年多。
蘇童:但是《一天》還是很震撼,現(xiàn)在看起來。其實(shí)你還有一個小說更游戲的,比較游戲的就是拿很多歌詞串起來的。
陳村:《我的前半生》。我寫《一天》的時候我沒找到敘述方式,只好扔下了。后來有天我跑到昆山去閉門寫作,我就想起來應(yīng)該這樣寫,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弄得很聰明弄得詞匯很多,我用最簡單的句式來寫。不要覺得我可以弄出很多句式可以很花哨,可以用一種文人的士大夫式的一些腔調(diào),或者很書面語式的來闡述一個其實(shí)是很漠然的生活,應(yīng)該不動聲色。
蘇童:這是一個聽上去很簡單的,就是一個簡單的人生,一個很簡單的故事,用最簡單的方式。
陳村:有時候?qū)懼鴮懼鴷涝谀抢铮阒肋@個小說是有價值的,但是覺得你使不出力了,你不知道用什么辦法去對付它的時候你就會就傻掉了。但是寫小說,對我來說還是喜歡的,造人,我覺得很有意思。
蘇童:是。
陳村:因?yàn)樗翘摌?gòu)的。因?yàn)槲覀兩钪幸惶摌?gòu)就是吹牛啊,就是騙子。
蘇童:說實(shí)在的他媽的生活當(dāng)中就剩這一件事了,虛構(gòu),讓人跟現(xiàn)實(shí)生活可以拉開一個距離。說起來還是幸福,還是有一點(diǎn)幸福感的。
陳村:而且是可以給你一種幻想。
蘇童:確實(shí),我一直說這樣你一個人去尋找兩個世界很難,但寫作就是一種捷徑,寫作就是唯一一種捷徑,尋找兩個世界的捷徑。那么魅力也就在這里。
陳村:你尋找兩個世界,而且過了幾輩子的生活。
蘇童:過完了,人事滄桑,我替別人閱歷。你比方說《我的帝王生涯》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典型的就是我通過這個小說我完成了好幾個人生。
陳村:而且完成了你不可能的人生。
蘇童:對。就是這么一種狀態(tài),其實(shí)是掠奪的欲望。
陳村:有些小說很奇特,我以前說過好幾次。我說你的男孩寫得好,我蠻喜歡把男孩寫好,男孩是很難寫的。人家講女孩難寫,其實(shí)女孩或一個女人大概容易備受關(guān)注,或者寫得可愛或者寫得什么清純。男孩很難些。我覺得你今天再寫男孩可能就不如當(dāng)年了。
蘇童:對對。
陳村:就像小仲馬再寫《茶花女》。
蘇童:我寫男孩系列那個時候還是三十歲以前。因?yàn)槲易约浩鋵?shí)開竅蠻晚的,我就是這方面,晚。所以我覺得是我自己比較挽留那段所謂少年生活,是因?yàn)樽约旱囊环N性格啊各種方面原因,好像自己很無意的把它時間挽留得長了一點(diǎn)。所以我自己覺得在寫那些小說的時候,我其實(shí)在聞自己的襪子,我覺得有這種感覺。我是比較喜歡聞自己襪子的,這是怪癖。
陳村:哈哈。而且那個很好。我就講人大了以后呢也許可以深厚,可以遼闊,但是他不大純了。他很濁了。濁么那大海也是濁的,黃河長江也是濁的。但是你那些比較清新的比較容易受傷害的那種東西都沒有了。
蘇童:你剛才說什么關(guān)于寫女性?男寫男,女寫女?我一直不同意男女分治,我們現(xiàn)在所流傳在世的所有小說當(dāng)中最好的女性形象,是誰創(chuàng)造的。所以我們現(xiàn)在要說的女性形象,比如說《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妮娜》,《紅字》,這些女性全是男性作家創(chuàng)造的。
陳村:對。
蘇童:這個是一個非常奇特的自我縱容,男性作家逃避描寫女性,我從來不覺得可以給自己找理由。我從來沒覺得自己寫女性寫得好。但是這個外界都說了十幾年了,說得我自己都認(rèn)為我寫女性寫得好了。現(xiàn)在是這種狀況,感覺自己接受了一個古怪的榮譽(yù)。
陳村:寫女性呢,我覺得有一種愿意。什么叫愿意呢,就比如說我寫一男一女兩個人的事兒。那么我的立場很容易就是想把男人的想法表述出來。
蘇童:對。
陳村:然后就是壓抑了或者忽略了女性的想法。如果你好好去想女性在這個處境下會怎么樣,其實(shí)你大概也能想出來。但少感性的東西。
蘇童:其實(shí)我一直這么說,也就是說你不肯給她一個立足之地。就是思想上和創(chuàng)作過程當(dāng)中不肯給她一個立足之地。是你覺得是你要站在那,而且你有一個預(yù)設(shè)立場是男性立場。而且多多少少里頭有一個潛意識。不能說是沙文主義但確實(shí)是有男性優(yōu)先,覺得她的這個角色不要來沖淡我這個男性小說架構(gòu),男性的一個小說架構(gòu)。他有這么一種潛意識其實(shí)恐怕多多少少會存在。除非有一種現(xiàn)象,就是從一開始就走反棋。我就是寫一個《包法利夫人》,我就寫一個《安娜·卡列妮娜》怎么樣?我看你的立場能不能就是很固定的在男性架構(gòu)的。
陳村:就是不要男主人公的。
蘇童:男性角色是配角。可以試一試就是這樣。我覺得一下就可以順過來了。
陳村:因?yàn)橐呀?jīng)無能,就像一個房子啦,這根梁這根柱子沒有了就是只能用另一個柱子。這也是一個辦法。這種平衡是蠻有意思的。我在想我看那么多女性寫的也是。其實(shí)女性寫到的男人多半也不大像男人。
蘇童:我覺得我寫的女人也不是很那么女人
陳村:不,你有一個關(guān)注女性命運(yùn)的眼光。
蘇童:應(yīng)該關(guān)注。
陳村:有些人他不大關(guān)注女性的命運(yùn)。覺得女性命運(yùn)可能也是可以附帶在男人的……
蘇童:對。其實(shí)還是剛才我說的,他是有沙文主義的。多多少少有一點(diǎn)。
陳村:一個作品寫出來,自己讀作品的時候會有點(diǎn)不一樣。會看到那些過分了地方。我曾經(jīng)改過《鮮花和》。那兩年里,我因?yàn)橐粋€事情中掉了,斷過以后一看不對。這樣寫是不對的,你會修正一下立場。讓大家都講他的道理都做他的事情。當(dāng)然做的還不夠,不好,但是總算有點(diǎn)意思。就是說讓別人也要活一活,讓別人也要說一說,不要你一個話筒拿在手里都是你一個人唱。
蘇童:對。不要做麥霸。我覺得現(xiàn)在好多人自己給自己設(shè)置地位啊,或者說就是麥霸心態(tài)。麥霸心態(tài)就是要唱而且老唱,聲嘶力竭也要唱。
陳村:你們聽著。
蘇童:不聽不行,聽著。
[陳村按:每次做文本,最讓我痛苦的是被篇幅害了,只能揮刀自宮。只能等最后結(jié)集,一一復(fù)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