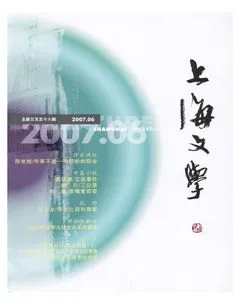其實是為了說另一件陌生的事情
1999年,有一次我問施勇:你的作品不完全是諷刺吧?他一臉正經地回答:就是諷刺。
施勇喜歡自我解釋,解釋是他作品的一部分。我說:如果刪除你作品的文字附錄,你的作品會有所缺損嗎?他說不會,他的作品通俗易懂。那么,看來施勇的文字解釋就是多余部分了。但是事實情況并非如此,如果我仍把施勇的作品歸入觀念藝術的范疇,他想表達的觀念并不僅僅體現在他作品的物質形態部分,還呈現在他作品的標題、計劃、提綱、簡述和長短不一的答問中。我喜歡讀施勇的文字,它讓我了解到藝術或反藝術與那個制造者之間的多重關系,盡管這種關系并非總是心靈的。施勇的文字充滿了時髦的術語正如他時髦的頭發和表情,也許,非個性化正是施勇所要表達的時代特征之一。在這個標準化的、通用的、四處皆宜的當今世界,不論是我們所要表達的想法或是我們所要塑造的自我形象,一切都有現成的范本擺在那里等著我們去選用。
如果現在的藝術史已經把反藝術也變成其中的一個章節,那么再來區分施勇做的究竟是藝術還是反藝術已經無關緊要了。媒介、復制、娛樂性,在施勇那里是以十足商業化的面目出現的。它們通常形象呆板、動作滑稽、表情做作,也許這就是施勇稱之為諷刺的理由。用某些大眾最熟悉的物質形態和符號去生產一件藝術作品再配上說明書式的陳詞濫調,使它和所有的商品及其代言形象處在同一位格,在我看來意義并不在于諷刺而在于接納的狂喜,這種狂喜恰恰是我們身處的時代給我們帶來娛樂的結果。正如媒介的“無邊界”一樣,媒介的娛樂性也是無邊界的——施勇隨手拿到的廉價形象周期短暫瞬息萬變,但他將這些廉價形象刻板化和媚俗化,諷刺已經無效正如批判走到了盡頭,玩笑和戲仿開始登場。
施勇那一系列減滅了個性的“新形象”因為貼滿了時尚標簽而獲得了時代感,這一時代感其實意味著一種“代際個性”的誕生。施勇的“真身出場”使代際個性具像化了,“假象”是這一具像的特征.同時又是真相所在,如同牽線木偶被操縱線掌控著。可以是任何一只木偶,每一只木偶都同樣真實,劇情是虛構的,劇本是生產出來的,所有的角色都服從于這背后的虛構和生產。在施勇的劇情片斷中,只有類型沒有自我,只有等待沒有目標,只有欲望沒有自由——有意思的是,施勇在處理這些有關異化的主題時,采取了一種刻板媚俗的平庸形式,而這種形式幾乎和我們耳聞目睹的現實相平行,它不是寓言,是蓄意的“鏡像”。
玩笑和戲仿,有時候在施勇那里是以“玩具”的形式出現的,霓虹燈、充氣物、錄音裝置和感應裝置,它們需要參觀者的介入,走近它們,傾聽它們,觸碰它們,甚至撫摸它們,使參觀者變成游戲者。也許施勇認為藝術應當在一種與人的多種感官互動中才能播散出其內涵,而并不僅限于有距離的觀看。在另一些由燈箱或攝影圖片構成的作品中,施勇營造出一種迷惑的、幻覺的和想入非非的氛圍,它時而是施勇本人形象的無限復制,時而是由上海高樓頂端霓虹燈組合成的海市蜃樓。施勇本人形象在他作品中的不斷登場是不能用自戀情結來簡單解釋的,它可能源于一種深度的恐懼,只有通過鋪天蓋地的自我復制才能得以緩解。但是就其表面的標題和文字解釋而言,似乎不過是開個玩笑,那么就讓我們把它當成一個玩笑吧。
向無所不在的商業社會妥協,甚至連諷刺都可以作為商品出售;向平庸的現實妥協,甚至連挪用和模仿都可以作為創造;向毫無想像力的潮流妥協,甚至連刻板媚俗都可以成為人人趨之若鶩的時尚——施勇的態度是雙重的也是含混的,既抱以輕蔑的態度對待這個熱鬧庸俗的世界,又興致勃勃的從中取樂;既假裝出一種幽默感,又使這種假裝變味成新的幽默;既措詞深奧地談論自己的作品以及作品與現實的隱喻關系,又因自己作品的物質類型和透明性讓人們從中看到一個沒有深度的現實如贗品一般不真實。這一切奇妙的混合,不僅源自施勇的模仿欲望也源自施勇經常離題的表達欲望,而成就其作品的,則是當今這個反智、低俗、不可救贖的全面商業化時代。
說一片葉子就是一片葉子,這種同語反復按羅蘭巴特的形容,即便在“正確的時刻里”也不過是一種昏厥或一種救贖的失語癥。需要找到另一個詞或詞組來定義,而這不但取決于定義者的興趣所在,也取決于一些偶然情況的發生。
當陳海汶站在投影儀前一張一張講述這一組照片時,我終于知道他在說什么,需要什么了。晨曦之上或暮色之下,街衢之側或深巷之端,老墻灰墁剝落斑痕累累,暗綠的深褶,通常是赭紅的暖背景,白色的幽靈,一個空箱子,或一排空箱子,鳥籠似的,靜謐中,一句格言從遠處飄來:一只籠子在等一只鳥,或等一瓶牛奶。它是牛奶箱,營養充足的、女人味的、摩髓的以及普通的。作為日常徽志、攝影刺點、無處不在的沉默主體,“牛奶箱”在此處具有唯一性。陳海汶用照相機抓住了它,這視若無睹的纖毫,低調市民生活之緩慢循環,如棄物般,任其日曬雨淋,又如鍥子般,打入照片中央,處在有待揭示的微明狀態;雖已呈現,仍然易遭忽略,早習慣湮滅的命運,瑣屑之物和瑣屑之美,卑微如斯,無聲地顧影自憐。世俗的,太世俗了。它們在等待考古學家,它們是任人利用的意象。考古!意象!恣情對一座現代城市進行影像考古,把一座功能城市通過幻覺轉換成意象城市,這種瘋狂計劃實在引人入勝,不需要詩人的介入……先是影像,影像,還是影像,最后輪到“后文字”,它緊隨其后,積極參與影像的拼貼與解說。影像是我們外置的意象和記憶。生活在一座真實的城市中對我遠遠不夠,必須另有一座不存在的城,它的倒影,反向的它,一個對形的城,負數的城,唯心的城,由能指構成,一切均為虛影,不能兌現,那里沒有現實,但所有的虛影無不返指我肉身親歷的這座城。那是天堂之城,也是深淵之城,遺忘之城,永逝之城,它已在彼岸。
影像即彼岸。影像是不在之在,作為被凝固的和被延時的不在之在,影像比稍縱即逝的此在更易于受到關注。存在一刻不停地消逝,浩浩蕩蕩地消逝,昏暗街角一季一會的花香,迅速衰老之時代,廚房話題千百次重復,去年出版的城市地圖已成為廢棄的迷宮圖……趕快創立城市歷史地理學會吧,用影像重建一座新的城市,開拓新疆界,印制新版圖,插上嶄新標志,以挽歌精神前瞻我們的城市未來,就從“牛奶譜系學”開始,一部多卷本的、唯美的、略帶傷感的、不乏沉思的《城市生活細節史》正呼之欲出,由影像沖鋒陷陣,文字殿后,具有互文性的諸般好處:豐富多彩,及物,充足儲備,開闔自如。好好享受它,一個使人著迷的美麗客體,別管她的出處……對此我將樂觀其成。
李梁約我去東廊,要把攝影家羅伯特-奧康納介紹給我。接到李梁電話的時候,我正逃會,逍遙自在地走在南京路上,那種感覺真叫棒:他們都在活受罪,只有我想去哪兒去哪兒。許多事在缺乏先兆的情況下發生,我指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即便是龐大的帝國和堅不可摧的政黨,突然的崩塌與解體都在一瞬之間;我鄙視過于龐大的事物,也討厭那些所謂的“宏觀”、“總體”和“歷史框架”。羅素在向年輕人推銷歷史書籍的時候講了許多讀歷史的妙處,他建議讀者“讀讀”幸存下來的日記、信件和回憶錄,因為那兒充滿詳盡的細節;另外一個妙處是,那些“歷史文件”的作者并不像事后聰明的歷史學家那樣知道接下來將發生什么。歷史學家的討厭在于,他們喜歡把一切說成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幸存的文件常常令人詫異地顯示,當發生重大事情時,人們竟然還有空關注者小事情。我非常熱愛這種歷史對比,我堅持認為個人接到的一個電話,意義遠遠要大于一條法令的頒布,或某次官僚會議的文件傳達。路易菲力普在隨著波旁王朝逃亡時所寫的信講的全不是公務,而是關于他孩子的哮喘與咳嗽。讓那些官僚會議見鬼去,一種注定要被迅速遺忘的東西,必須提前拒絕它……現在,我決定去東廊,去見羅伯特,一個靦腆的愛爾蘭人。
幾天后,李梁把羅伯特的簡歷發給了我,可我對羅伯特仍然所知甚少;就像羅伯特拿著中國旅游指南,憑這又怎么能知道真實的中國呢。也許真實的中國存在于另一個地方,幽暗之中或光天化日之下,也許它對絕大多數旅行社顧客根本就無關緊要:地球表面的某處,北半球,亞洲,東八時區,溫帶氣候,太平洋西側……指出它的確切地理位置遠遠不夠,不僅因為你沒有走進它內部,還因為你沒有找到合適的以及你最感興趣的觀測點。到中國來就是為了尋找不一樣,尋找時空差異,尋找化石與奇觀,這樣做一點沒錯,一次愉快的旅行就是對異國情調的片斷化攫取。雖然你可能真的看見了一些有關中國的特征,或者說,你用你的眼睛印證了觀光手冊為你描述的有關中國的特征,但它們早已被符號化固定化模式化了……羅伯特不是觀光客,對他來說,那種步人后塵的發現與印證毫無意義。在一次和羅伯特的談話中,我模仿電視專訪節目像刻板的記者那樣缺乏想像力地問他:你的第一次中國之旅結束后,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羅伯特回答說:剛到中國我完全沒有方向,后來我整理我拍的五百多張照片覺得非常迷惑,那一刻我才想起了最初的經驗,飛機落地我從上海浦東機場坐車走高速公路進城,沿途不斷看到巨大的廣告牌在窗外飛逝而過……
這不僅是羅伯特對中國之旅第一眼印象的倒敘,也是他作為藝術家對自己經驗進行反省的誠實告白:連綿不絕的巨大廣告牌,即羅伯特所看到的當代中國之表征。
巨大的廣告,在中國逐漸成為超中國的中國新意識形態象征之一:內容全球化,地域性越來越趨于模糊,跨國公司、形象生產和媒介在當代中國產生的持續影響大面積地改變了中國的城市規劃、建筑設計、物質生活方式以及人對自身的想像。廣告不僅是商業促銷的誘餌,它還是權力的封套,替身,面具,代碼。廣告點綴在道路兩旁、街心花園和高樓頂部,但在它背后不僅是被污染的天空、廢墟外的圍墻或熠熠生輝的商業區,它背后游蕩的是未來藍圖,欲望敘事和集體夢想。置身于巨大的廣告叢林之中就是站立在現實中國的基本真相之前,它延續了現代政治宣傳的偉大傳統并學習了現代商業宣傳的偉大發明:標語牌,口號,通俗短語;超級裝飾,擬真,鏡像。在中國東海岸及其縱深,超大型城市的劇增與瘋長和上述口號化廣告的虛張聲勢早就同步,現實和想像界限日趨含混。圖像和現實不加區別,廣告即真實,廣告即伸手可及的彼岸,它混淆于現實的裂隙,為霓虹燈照亮。羅伯特來自愛爾蘭,愛爾蘭沒有超大型城市,也沒有如此密集的廣告,可見羅伯特在中國看到有那么密集的樓房有那么密集的人口將怎樣驚訝。中國是他為了做《未來計劃》所到達的第一個亞洲國家,只走訪了北京、上海、杭州三個城市,這三個城市在我們中國人自己看來都非常特殊,但偏偏羅伯特視若無睹;他只發現他刻意要發現的問題,他只執意要通過有選擇的一組照片將他一直關心著的問題提出來,絕非為了全面了解一個亞洲國家,全面了解中國不是羅伯特必須做的工作,意欲全面了解當代中國(特別是處在他者的驚奇凝視之下的那個被簡化為突飛猛進的當代中國)則必須關注羅伯特正在做的這部分工作:一個不懂本地語言的陌生人,一個同我們的處境毫不相干的異國旅行者,一個背著照相機,懷里揣著一份與中國現狀抽象地有關的而事實上對中國不構成任何影響力的“未來計劃”,究竟所為何來?
全球化的廣告圖像就如此輕而易舉地俘獲了中國和它的城市,拆除了語言壁壘,為我們建立起世界大同的幻覺。在中國所有的公共媒介,那些至今不愿放棄單邊權力控制的大眾傳播機構,廣告收入幾乎是它們的基本經濟來源并構成了維持它們正常運轉的唯一支柱。權力和廣告的交易,它們的相互利用、合謀、摯時、滲透,終于在中國原有意識形態的沉重幕布上撕出一個大窟窿。地方性、局域空間和單一價值通過那個屏幕被打破了,出現了外部世界鏡像:另外的地方性,另類空間,另一種生活方式,從那個大窟窿里源源不斷地傾泄而出……當我們以為這個外部世界鏡像差不多已經占據了舊有舞臺的一切角落時,權力對我們的隱秘控制關系就可能被內化為一種欣然的游戲模式,在這種游戲中,控制者與被控制者的分工起源于某種偶然的抽簽,資本和雇傭勞動、政府和納稅人、導演和觀眾、暴力和服從、侵犯和忍受……階級對立與階級斗爭統統被所謂和諧社會的空洞承諾及未來大同世界的美麗藍圖所掩蓋,它們成為一塊掩耳盜鈴式的巨大新幕布。權力者和大眾都一致相信廣告的言說如同他們過去相信報紙的言說,權力者說他們代表了所有的人。矛盾最終被消除了,空間差異被抹去,思想不再有必要,對廣告的接受就是對現實的接受,就是將自己的判斷力和辨別力讓渡于他者,就是愿意將世界理解為一連串從廣告中拋撒出來的碎片組合,就是把自己的真實感受分離出現實境遇轉而投身到那個經過超級裝飾的虛擬空間里中去。
羅伯特的“最初驚奇”促成了他這些中國快照的問世,他的敏銳表現在他對普通印象的直接采用,而這種普通印象,在絕大多數人那兒業已司空見慣,延伸到世界盡頭的廣告對他們而言如同自然風景的一部分,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但羅伯特的意圖在于,他利用了廣告這一全球化文化慣例,在一個影響有限的當代藝術范圍內將它提上了議事日程。羅伯特的議題是:媒體、形象生產、城市設計和廣告,它們為當代中國帶來的重要性可能表現在它們已經改變了中國人對將來以及對生活方式的理解。對此我的回答是:是的,我同意,毫無疑問……但是我想強調另一面,即在不改變權力關系的條件下,任何有限開放和表面多樣性,都不過是對真實性的遮飾,以及對自由的改變了形式的繼續壓制。在跨國公司商業廣告全球化的背后,自由的全球化還遠遠沒有到來。
同顧起來,1989年對徐弘造成的創傷顯然不足為奇,雖然那個集體性的創傷似乎已被故意遺忘……當初沒想到的是,一個涉世不深的年輕人在這一特殊時間點所懷著的政治好奇與敏銳,加上以旁觀者身份目睹到的危機與動蕩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改變將在以后的十數年中一直反作用于他,不論是中途改行還是重操舊業,徐弘始終沒有擺脫政治思考的日常習慣。
我對徐弘的了解是回溯式的,是一種傾聽對記憶的召喚,它逆向地呈現出一條隱約可見的道路。時光一天天消逝,如果不是因為徐弘的畫,如果他沒有把自己的畫拿出來,我就無從知道徐弘除了和我們一樣在生活中忙碌,內心到底想些什么……一個人的內心在想些什么,這對今天的我們還重要嗎?
人在墜落中不可能跳躍,但墜落帶來的強烈感受,從狂歡喧嘩突然跌落到沉默無聲,也許給了措手不及的徐弘在漫長的90年代久久緩不過神來的致命一擊,他的改行并沒有使他完全放棄對現實政治與社會變遷的思考,哪怕只是斷斷續續的零星思考。這種持續的片斷化政治思考由個人秉性和日常興趣所推動,與責任無關,在一個政治資源被權力高度壟斷的非公民社會架構中,向無權者奢談責任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與敲詐。在整個90年代的精神侏儒化時期,政治只能以笑話、傳聞、流言和諷刺的語體被戲說,而不可能以嚴肅、理性、公開和透明的方式被討論。1993年,徐弘畫了一幅寬五米高兩米多的油畫《聚會》,男男女女笑容可掬地擁擠在廣場上,他們穿得花枝招展,那是對剛過去的歷史事件的反諷性緬懷嗎,或者是對未來烏合之眾的消極展望?在差不多的前后幾年,徐弘畫的基本上是一些嘻嘻哈哈的群像,《女人們》和《恭賀新禧》可能是它們中的代表作。人們被趕同到私人生活領域,喪失了公共空間,他們擠成一堆,表情雷同甚至連容貌都彼此相似,作為被抹殺了個性與自由的政治族類,這一群氓表征在當時的許多畫家筆下有著不約而同的描繪,不論稱之為狂歡、玩世或是呆傻,都已經被載入90年代的肖像史冊。而徐弘,不僅是見證者,也是記錄者和響應者。
徐弘再次拿起畫筆時已經是2004年以后了。整整十年,當然,徐弘在干些別的,他不會閑著,畫冊上空白的年份或許就是生活中最忙碌的年份。不過對我們來說,還有什么比看一個蟄伏了十年之久的畫家的新作品更令人期待的事情呢,我們不能分享朋友的生活,但我們可以分享朋友的作品:他在思考什么,在想像什么,最終又描繪了什么。“思考如果沒有朋友分享,生活會成什么樣子?”連尼采也這么說……我們看到了什么?一種陰悒、荒誕、超現實的圖像出現于徐弘的筆下:身著盛裝的狗,奧威爾式地手執紅旗和利斧,或雙拳緊握,目光如炬;還有豬,站在藍天白云之下,躺在搖籃里,或游弋于家庭泳池中。鐵幕換成布幕,依然是紅色的基調,最醒目的紅,符號般的,紅旗幟、紅書、紅座椅、紅地毯,肅穆嚴厲,沉悶僵化,象征體制威權的一貫冷漠與凜然。標題與時俱進,在《西部大開發》、《明星夢》、《矩陣革命》、《大南瓜》、和《肉聯廠的春天》里,欲望成了新的意識形態,權力者換了門面和穿戴,改天換地,野心勃勃,與宏大敘事一脈相承。這些畫散發出一種偽古典的莊嚴氣息,紅色的固有象征意指被動物傀儡的荒誕感完全顛覆,成為死板陰悒的“紅色幽默”。
欲望和時尚的關系如同生命和政治的關系。生命是神圣的唯一的,所有的政治都是“一種例外”,所有的時尚不過是“例外中的例外”。當人們被排擠出公共的政治生活,私人生活漸漸由時尚來接管,隨著一半是缺席一半是內爆的畸形雙重空間的出現,加上雙重的隱形宰制,一種被“例外”和“偶然”的制度化任意支配其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的新烏托邦和新無神論時代就來臨了。烏托邦發生了大轉移,生活看似繁花似錦,表面多樣的意義和目標將人作為欲望主體納入消費的單一軌道,一方面有關欲望的時尚說辭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時尚計劃由于它自身的規模化和代際更替,使得那些為其籠罩與裹脅的人們越來越生活在一套僵化的模式之中。徐弘說,“當初我們所唾棄的正是我們現在所擁有的,包括我們自己。我們反叛誰?我們沒有目標,也沒有敵人、”政治疏離,隨收入增加而擴張的欲望,謹言慎行,維護私人空間,按部就班,勤勉,向上爬,更多更好的物質享受,世界旅行,一點點品味加一點點愛,差不多就是生活的全部,這就是目標,有礙于這個目標的就是敵人,不過也說不定,如果力量來自超級權勢……憤怒不僅已經無效,且早已喪失了內在動力,人們為各自的私人生活藍圖而奮斗,一個被稱之為中產階級理想的“景象”誕生了,美好人生,體面,高雅,無可非議,它正迅速形成新的生存空間,生產出自己的模式與符號。符號!“符號引誘比任何真理的顯現更為重要”,我想徐弘對鮑德里亞的這句著名警言一定比我有體會。在他不再畫畫的那些日子里,干的就是廣告這一行:符號、櫥窗、虛擬、仿真,景象取代了現實!
矯揉造作的置景化了的中產階級生活,如家居雜志插圖一般,被徐弘挪用,放大在了畫布上。像大衛霍克尼那樣去觀看,冷漠,刻板,別有機抒地,徐弘從別墅花園、客廳、泳池、露臺等等人工布景里除了重復和無聊,還發現了荒誕和不安。2006到2007年的《紅色搖籃》、《晚餐前的時光》、《捕鼠記》、《雙休日》、《告別的詠嘆》、《大船》、《遠方》、《上岸》和《探園》,場面寧靜而平庸無奇,不經意中突然出現裂隙,詭異,兇兆,馬格利特式的幻像甚至達利式的狂想:搖籃里的嬰兒被熟睡的豬置換,一只拎在女孩手里的貓將從二樓陽臺墜落,重心偏移的假山石,灰蒙蒙的云層下幾個廚師在泳池邊觀看溺水的豬,人工湖邊沉默佇立的女人、客廳里赫然駛入一艘游船,天鵝的身軀如丘陵般龐大、來歷不明的潛水闖入者……這些癥候是偶然的,還是來自精心設計、或兒童期的惡作劇情結、懸疑電影記憶?我不確定,我傾向于把這些癥候解釋為徐弘對中產階級生活場景危機的內在揭發,由忐忑、覬覦、窺伺、輕度傷害和恐懼構成的未來不明之夢魘,是出沒在徐弘作品中的一個幽靈,這個幽靈比徐弘對自己作品的政治解釋提供了更為復雜與詭秘的歧義,正是這種歧義最終吸引了我,它好像在提醒:那些類似的或迥異的場景,其實是為了說“另一件陌生的事情”!
從表象摹仿到通往表象背后的秘密,找到這扇暗門,那個由一開始的政治圖騰和大場面諷喻轉變為庸俗生活小場景之冷漠描繪,徐弘的意義終于突破了他為自己設定的政治概念框架,進入一個隱藏在所謂中產階級豐裕生活背后的陰悒世界;它是當代生活一般形式的反面和倒置,對它而言,政治體制不過是偶然的“例外”,烏托邦朝私人化方向的轉移正好遇到了一次當代機會。從紅色矩陣的幽默反諷,到鄉間別墅超現實主義陰悒之綠色迷霧,印證了曼海姆的一句話:一種社會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為置身其中的人所了解。而藝術,以及徐弘的作品,正是重要的“特殊情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