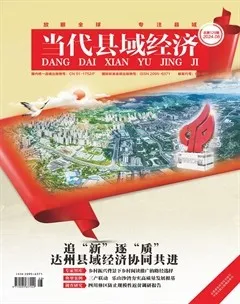守望相助 仁壽民富村鎮銀行支農支小顯情懷
“支農支小是我們的初心也是使命,在助力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們有能力也有責任貢獻一份力量。”釆訪中,仁壽民富村鎮銀行黨支部書記、董事長鄒玉敏語氣堅定地說道。
正是堅守這份初心,近年來,作為扎根縣域的地方銀行,仁壽民富村鎮銀行始終堅守支農支小主責主業,鍥而不舍、步履不停,一路陪伴、見證、支持“三農”和小微客戶發展壯大。
守望相助,助力企業創業共成長
“今天我們一是來看看你們的生產經營情況,二是來聽聽你們未來的打算,有沒有擴產計劃,有沒有資金需求。”近日,記者與仁壽民富村鎮銀行員工一道走進仁壽縣龍正鎮四川廚豐食品有限公司調研。
“多年來,你們傾情關心企業發展,總能在關鍵時候雪中送炭,讓我們很感動。”公司財務總監蔣衛東立即放下手上工作前來迎接。一番寒暄之后,帶著眾人深入企業車間了解生產經營情況。
蔣衛東告訴記者,四川廚豐食品有限公司與仁壽民富村鎮銀行結緣始于3年前,當時公司物流鏈條幾乎斷裂,原材料進不來、產品出不去,這讓公司上下如坐針氈。得知這一消息后,仁壽民富村鎮銀行主動上門對接服務,為企業定制了“疫應貸”金融產品,短短兩天,首筆信用貸款50萬元就發放到賬,解了企業燃眉之急。建立起合作關系后,貸款金額從50萬元逐步增加到300萬元,累計金額上千萬元。如今,該公司發展迅猛,其旗下“臻鮮”等品牌在川內、西安等地享有較高知名度,同時正通過電商銷售等渠道快速占領全國市場。2023年,該公司銷售額近億元,是仁壽乃至眉山食品行業的“排頭兵”。
守望相助,助力企業創業共成長,仁壽民富村鎮銀行不僅僅停留在貸款層面,更是把自身當作企業發展的一分子,共榮辱、同發展。
精細服務,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與仁壽民富村鎮銀行金融服務先鋒隊一道,走進位于方家鎮、青崗鄉的仁壽民富村鎮銀行“黨建+金融”服務示范基地,記者看到,基地里的仁壽縣騰贏量農業專業合作社承包的5100畝農田,碧綠的小麥、油菜長勢喜人,預示著豐收。
合作社負責人范琨正忙著和工人整理農機設備、溝渠修整、農資采購等工作,這些還需要投入資金300余萬元,對于金融服務先鋒隊送貸上門的“及時雨”,范琨喜出望外。
“他們總能在最需要的時候出現,一路走來,仁壽民富村鎮銀行是我們唯一的金融合作伙伴,合作社發展壯大離不開他們貼心周到的服務。” 據范琨介紹,自2016年合作社與仁壽民富村鎮銀行開始合作,多年來累計貸款金額達2680萬元,雙方結下了深厚情誼。
如今,在仁壽民富村鎮銀行的強力金融加持下,騰贏量農業專業合作社從種植面積僅幾百畝、農機4臺、年產值400萬元的“小不點兒”,成長為糧食種植面積5100余畝、年產3600余噸、農機36套的行業翹楚。目前,該合作社常年解決當地勞動力200余人,糧油產值1200萬元、農機服務產值2600萬元。
2021年以來,仁壽民富村鎮銀行累積發放助農振興貸2.925億元,支小惠商貸8937萬元,為1868個小微企業和“三農”實體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