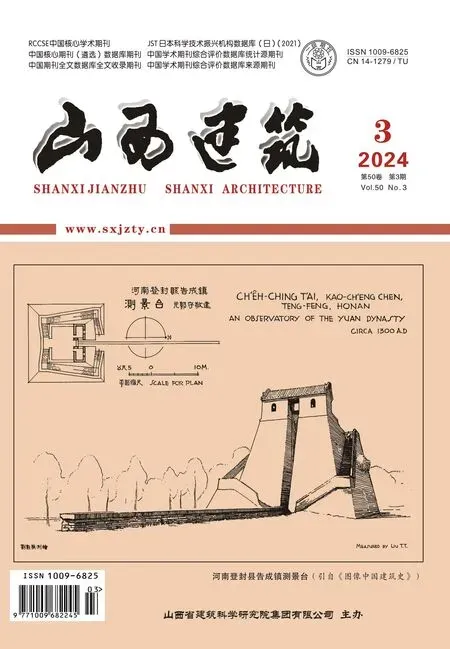基于比較視角的國土空間村莊規(guī)劃編制探討
唐 堯
(浙江省國土空間規(guī)劃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00)
村莊規(guī)劃編制是國土空間規(guī)劃機(jī)制建設(shè)重要組成部分,成為國內(nèi)學(xué)者研究熱點(diǎn)課題,對人與用地關(guān)聯(lián)、規(guī)劃效果探究、土地整治策略、落地實(shí)施方式等都有全面闡述,是村莊編制規(guī)劃權(quán)威參考標(biāo)準(zhǔn)。但是在這方面研究上,相關(guān)村莊規(guī)劃研究較少,特別是城鄉(xiāng)差異化分析,既能夠推動國土空間機(jī)制建設(shè)背景下村莊規(guī)劃編制明確性質(zhì),又能夠全面剖析國土空間機(jī)制背景下村莊規(guī)劃短板弱項(xiàng),成為村莊規(guī)劃編制成熟,付諸有效實(shí)踐的重要支持。
1 國土空間規(guī)劃與城鄉(xiāng)規(guī)劃體系比較
1.1 規(guī)劃編制
城鄉(xiāng)規(guī)劃體系組成較為單一,內(nèi)容為鄉(xiāng)鎮(zhèn)域村莊分布、縣域鄉(xiāng)村建設(shè)規(guī)劃。城鄉(xiāng)規(guī)劃體系對村莊規(guī)劃設(shè)計(jì)較為規(guī)范,核心是引導(dǎo)布局物質(zhì)空間,而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內(nèi)容為村莊設(shè)計(jì)規(guī)劃,并不區(qū)分縣域、鄉(xiāng)鎮(zhèn)域設(shè)計(jì)規(guī)劃特點(diǎn)[1-3]。兩者相較而言存在許多不同點(diǎn),主要表現(xiàn)在要求細(xì)致程度、適用范圍等方面,具體從表1,表2可見。

表1 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城鄉(xiāng)規(guī)劃體系比較

表2 城鄉(xiāng)規(guī)劃與國土空間規(guī)劃中村莊規(guī)劃編制方式比較
1.2 規(guī)劃管控
對于城鄉(xiāng)規(guī)劃來說,主要是發(fā)揮頂層設(shè)計(jì)作用,重在謀劃整體建設(shè)計(jì)劃,既包含規(guī)劃,又給予建設(shè)標(biāo)準(zhǔn)。其中包含農(nóng)村災(zāi)害的防御、環(huán)境衛(wèi)生的保護(hù)、農(nóng)房的選址建設(shè)以及產(chǎn)業(yè)分布情況等,作用范圍更大,管控界限更為寬松,實(shí)施存在更大困難。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設(shè)計(jì)覆蓋全要素、全區(qū)域,具有細(xì)化落實(shí)標(biāo)準(zhǔn)特點(diǎn),明確規(guī)定永久基本農(nóng)田指標(biāo)、耕地保有量等標(biāo)準(zhǔn),以圖斑地塊方式清晰呈現(xiàn),實(shí)現(xiàn)規(guī)劃圖、數(shù)統(tǒng)一,確保山水林田湖草生態(tài)格局得到充分保護(hù),實(shí)施剛性管控策略,保障村域空間管理筑牢底線[4-7]。國土空間規(guī)劃、城鄉(xiāng)規(guī)劃具體編制差別見表3。

表3 城鄉(xiāng)規(guī)劃與國土空間規(guī)劃中村莊規(guī)劃編制內(nèi)容對比
1.3 規(guī)劃實(shí)施
GIS系統(tǒng)作為國土空間規(guī)劃關(guān)鍵技術(shù),具有規(guī)劃設(shè)計(jì)、總結(jié)分析、后續(xù)監(jiān)督應(yīng)用一條龍服務(wù),以新一代系統(tǒng)應(yīng)用為核心技術(shù)的平臺中,能夠完成“一張圖”管理,控制線、邊界、圖斑等都能輕松獲取,管理過程更加簡單。表4為兩者落地實(shí)施情況具體對比。

表4 城鄉(xiāng)規(guī)劃與國土空間規(guī)劃中村莊規(guī)劃技術(shù)成果對比
2 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中村莊規(guī)劃主要特征
2.1 多層次村莊規(guī)劃
1)區(qū)域?qū)用?城市開發(fā)邊界外用地在城鄉(xiāng)規(guī)劃中沒有明確要求,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中郊野單元規(guī)劃,將郊野地區(qū)全域資源要素統(tǒng)籌安排,劃定郊野區(qū)域具體單元,實(shí)現(xiàn)系統(tǒng)修復(fù)、綜合治理、整體保護(hù)為一體,村莊居住地點(diǎn)、空間結(jié)構(gòu)得到充分優(yōu)化,鄉(xiāng)村空間管控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2)村域?qū)用?秉持跳出村莊看規(guī)劃理念,創(chuàng)新城市周邊村莊納入城市規(guī)劃,實(shí)現(xiàn)公共服務(wù)、基礎(chǔ)設(shè)施、產(chǎn)業(yè)要素一體化,科學(xué)規(guī)劃農(nóng)業(yè)、生態(tài)空間,充分發(fā)揮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作用,實(shí)現(xiàn)數(shù)字化、智慧化,確保規(guī)劃精準(zhǔn)落地實(shí)施,保證村莊管理更便捷、有效。
3)村莊層面:注重設(shè)計(jì)環(huán)節(jié),以反映鄉(xiāng)村大環(huán)境為中心,突出內(nèi)部細(xì)節(jié)管理,以及重點(diǎn)片區(qū)等內(nèi)容,實(shí)施村莊內(nèi)部統(tǒng)籌考慮、整體管控,實(shí)現(xiàn)村莊層面設(shè)計(jì)特色化管理。
2.2 多類型村莊規(guī)劃
1)搬遷撤并型村莊:部分村莊面臨發(fā)展困境,生態(tài)環(huán)境較為脆弱,生存條件比較惡劣,村域內(nèi)人口流失嚴(yán)重,自然災(zāi)害難以抵擋。通過搬遷撤并手段,實(shí)施村莊居住點(diǎn)嚴(yán)密管理,對擴(kuò)建、新建進(jìn)行有效規(guī)范,拓寬薄弱村莊發(fā)展渠道,引導(dǎo)農(nóng)村居民進(jìn)城發(fā)展、集中發(fā)展。
2)集聚提升型村莊:鑒于村莊各自情況分析,部分中心村莊具有發(fā)展優(yōu)勢,可以進(jìn)行單獨(dú)編制,發(fā)揮中心村輻射帶動作用,吸引周圍居民前來居住。科學(xué)劃定居民點(diǎn),持續(xù)提升公共服務(wù)水平,實(shí)施村莊多產(chǎn)發(fā)展模式,不斷深化綜合治理、數(shù)字服務(wù)能力,形成中心村公共服務(wù)中心格局。
3)城郊融合型村莊:城市化進(jìn)程不斷加快,村莊融合具有重要價(jià)值,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位置特殊,納入城市整體管理勢在必行,可以充分拓寬城市服務(wù),以“城帶鄉(xiāng)”推動農(nóng)村享受優(yōu)質(zhì)服務(wù),持續(xù)增強(qiáng)城市化程度,為城鎮(zhèn)化發(fā)展體系提速加碼。
4)特色保護(hù)型村莊:部分村莊歷史文化厚重,自然資源優(yōu)勢明顯,應(yīng)著重突出特色資源整合利用,實(shí)現(xiàn)文化資源有效傳承、利用。村莊規(guī)劃應(yīng)以原住居民生活狀態(tài)為根本,注重整體肌理維護(hù),對歷史資源、傳統(tǒng)建筑實(shí)施有效保護(hù)策略,突出環(huán)境景觀特色化,推動基礎(chǔ)設(shè)施優(yōu)質(zhì)化,持續(xù)推動鄉(xiāng)村可持續(xù)發(fā)展步伐。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對村莊規(guī)劃分析如表5所示。

表5 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中村莊規(guī)劃分類引導(dǎo)
3 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中村莊規(guī)劃內(nèi)容特色
3.1 全過程管理監(jiān)督,強(qiáng)化鄉(xiāng)村環(huán)保高效剛性實(shí)施
鄉(xiāng)村整體性在國土空間規(guī)劃中較為突出,注重頂層設(shè)計(jì)引導(dǎo)下層發(fā)展方向,提出清晰剛性管控標(biāo)準(zhǔn),制定嚴(yán)格約束標(biāo)準(zhǔn),采用環(huán)保紅線形式對基本農(nóng)田、發(fā)展邊界進(jìn)行具體要求,實(shí)現(xiàn)管控體系全覆蓋。
3.2 “一村一品一特”,分類推動鄉(xiāng)村特色化發(fā)展
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振興對于國土空間規(guī)劃至關(guān)重要,主要目的是推動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為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謀篇布局,挖潛鄉(xiāng)村區(qū)位優(yōu)勢、特色資源,實(shí)現(xiàn)鄉(xiā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一村一品”,呈現(xiàn)百花齊放姿態(tài),全力推動產(chǎn)業(yè)特色化、品質(zhì)化,助力實(shí)現(xiàn)鄉(xiāng)村振興。
3.3 統(tǒng)籌城鄉(xiāng)布局,推動城鄉(xiāng)公共服務(wù)均等化
國土空間規(guī)劃兼顧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堅(jiān)持城鄉(xiāng)發(fā)展“一盤棋”,集中體現(xiàn)城市輻射帶動效應(yīng),城區(qū)周邊鄉(xiāng)村實(shí)施公共服務(wù)均等化,實(shí)現(xiàn)鄉(xiāng)村道路、燃?xì)狻㈦娏Α⒔o排水等設(shè)施一體化,推動鄉(xiāng)村與城市對接,打造一體化管理運(yùn)營機(jī)制。
3.4 優(yōu)化技術(shù)總結(jié),深化規(guī)劃與管理銜接機(jī)制
國土空間體系技術(shù)成果清晰明了,關(guān)鍵在于“一圖一表一規(guī)則”。用途管理標(biāo)準(zhǔn)僅適用于搬遷撤并類村莊,系統(tǒng)規(guī)劃指導(dǎo)往往針對集聚提升類村莊,空間品質(zhì)提升主要對象是特色保護(hù)類村莊,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針對性強(qiáng)、指導(dǎo)性好。不僅如此,編制與規(guī)劃深度融合,有助于規(guī)劃管理具體實(shí)施,形成編制落地有效。國土空間體系應(yīng)注重管控區(qū)域、指標(biāo)、要求、邊界一體化管理,實(shí)現(xiàn)坐標(biāo)統(tǒng)一、圖數(shù)對應(yīng),突出國土空間規(guī)劃監(jiān)督體系系統(tǒng)化建設(shè),實(shí)施平臺化反饋機(jī)制,推動規(guī)劃擬定科學(xué)合理[8-10]。
4 村莊規(guī)劃編制建議
4.1 完善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體系
國土空間規(guī)劃以延伸性落實(shí)為主要特征,地區(qū)往往以上級部署為編制依據(jù),因地制宜發(fā)掘村莊編制特色。從當(dāng)前情況分析,技術(shù)方面尤為欠缺,整體機(jī)制建設(shè)并不完善。鑒于此,應(yīng)建立自上而下落實(shí)機(jī)制,依托更高水平頂層設(shè)計(jì),強(qiáng)化規(guī)劃體系標(biāo)準(zhǔn)化建設(shè),完善信息聚攏、監(jiān)督管理、用地區(qū)分等技術(shù)短板,以“多規(guī)合一”為最終實(shí)現(xiàn)目標(biāo),在規(guī)范化、科學(xué)化方面給予深入探索。
4.2 規(guī)范內(nèi)容成果體系
規(guī)劃編制技術(shù)成果方面,國家和各省市皆有具體標(biāo)準(zhǔn),但規(guī)劃編制仍然存在規(guī)范管理短板,村莊之間編制深度仍有差距。鑒于此,規(guī)劃編制技術(shù)成果完善應(yīng)注重因地制宜,區(qū)分聯(lián)合編制、單獨(dú)編制,制定特色化技術(shù)成果標(biāo)準(zhǔn),持續(xù)推進(jìn)編制規(guī)范化、科學(xué)化。
4.3 深化實(shí)施操作體系
實(shí)操性作為國土空間村莊規(guī)劃實(shí)施重要特點(diǎn),對于村莊規(guī)劃落實(shí)落地有重要指導(dǎo)作用,但當(dāng)前規(guī)劃內(nèi)容并未考慮村莊人文、治理、經(jīng)濟(jì)等方面內(nèi)容,規(guī)劃缺乏內(nèi)在邏輯,編制與監(jiān)督出現(xiàn)脫節(jié),仍要持續(xù)推動規(guī)劃計(jì)劃可行性分析。鑒于此,項(xiàng)目建設(shè)細(xì)化關(guān)系村莊規(guī)劃實(shí)施效果,建立起指標(biāo)、要求等完整流程體系,助力推動空間坐標(biāo)一致性建設(shè),充分運(yùn)用“一張圖”平臺,突出過程控制、監(jiān)督反饋,開展鄉(xiāng)村建設(shè)項(xiàng)目多層分析,確保項(xiàng)目實(shí)施合理有效,制定規(guī)劃實(shí)施遠(yuǎn)景目標(biāo),按照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深入落實(shí),推動理論走向?qū)嵺`。
4.4 探索實(shí)施評估體系
村莊規(guī)劃保持與時(shí)俱進(jìn)十分關(guān)鍵,原有計(jì)劃落地過程具有較大變數(shù),甚至產(chǎn)生矛盾,定期開展規(guī)劃糾偏完善,形成規(guī)劃實(shí)施成效總結(jié),打造村莊規(guī)劃動態(tài)體系,實(shí)現(xiàn)村莊規(guī)劃可持續(xù)性推進(jìn)。組織規(guī)劃實(shí)踐評估,能夠有效提升編制科學(xué)性,糾正編制存在問題,突出核心管控指標(biāo)優(yōu)化,預(yù)知村莊規(guī)劃修編前提,確保村莊規(guī)劃動態(tài)調(diào)整、持續(xù)優(yōu)化。
5 結(jié)語
面對“五級三類”國土空間框架體系,應(yīng)強(qiáng)化頂層設(shè)計(jì)引領(lǐng)效果,拓展城帶鄉(xiāng)一體化作用,村莊規(guī)劃編制走向規(guī)范化。文章深度闡述國土空間規(guī)劃與城鄉(xiāng)規(guī)劃體系不同,明確指出編制內(nèi)容、體系規(guī)劃、實(shí)施管理等存在差異。面臨新時(shí)期新變化,村莊規(guī)劃體系完善成為熱點(diǎn)課題,國土空間規(guī)劃體系呈現(xiàn)多元化發(fā)展格局,類型十分豐富,內(nèi)容簡單明了,能夠有效實(shí)現(xiàn)分類特色引導(dǎo)、全域全要素管控、融合落地實(shí)施、彈性戰(zhàn)略預(yù)留等目標(biāo),編制內(nèi)容凸顯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方向,注重以鄉(xiāng)村設(shè)施服務(wù)優(yōu)化、鄉(xiāng)村產(chǎn)業(yè)融合發(fā)展等為前提。國土空間規(guī)劃大背景下,未來村莊規(guī)劃進(jìn)程需要重視實(shí)施操作,突出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體系規(guī)范化,嚴(yán)格落實(shí)閉關(guān)管理,實(shí)現(xiàn)村莊規(guī)劃編制、實(shí)施一條龍服務(wù)[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