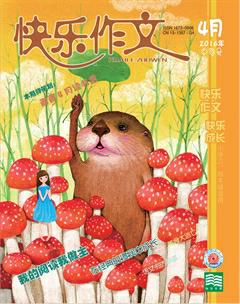難忘的一件事
徐璐
你們都有難忘的事吧?我也有很多。比如說第一次做蛋糕、給同學(xué)過生日、和爸爸下跳棋等,但我最難忘的是學(xué)騎自行車那件事。
我上三年級(jí)前的那個(gè)暑假,我要學(xué)騎自行車,媽媽拗不過我,只好讓我學(xué)。每次我騎車子的時(shí)候,媽媽就一直跟著我,在后邊扶著,每次自行車要歪的時(shí)候,媽媽使勁一扶就沒事了。
這樣騎了好多次。一個(gè)星期天,爸爸沒事,也陪我去學(xué)騎自行車。我想炫耀一下我會(huì)騎車子了,就一邊騎,一邊喊:“爸爸,我會(huì)騎車子了!”可是爸爸卻對(duì)媽媽說:“你放開手。”媽媽說:“不行,我放開她會(huì)摔倒的。”爸爸說:“可是你老不放手,她永遠(yuǎn)學(xué)不會(huì)的。”媽媽只好放了手,可是我沒蹬兩下就摔了一個(gè)“狗啃泥”。爸爸說:“學(xué)騎車,哪有不摔的。來,女兒,我們?cè)賮怼_@一次爸爸給你扶著。”我又坐上了自行車,開始騎了,爸爸在后面扶著……騎了一會(huì)兒,我又摔了下來。扭過頭看爸爸,爸爸竟然沒有在我的車子后面,而是在離我很遠(yuǎn)的地方,看到我摔倒了,才跑過來說:“很棒,你自己能騎這么一大截路了。”我說:“我要媽媽扶著。要不,我不騎了。”這時(shí)爸爸嚴(yán)肅地說:“你見誰騎車子,后面帶個(gè)媽媽的?你以后騎車能總帶著你媽媽嗎?有些事不能總想依靠別人,要靠自己。”媽媽也說:“寶貝,你爸爸說得對(duì)!”以后再學(xué)騎車,媽媽也不給我扶了,這樣又練了好幾次,也摔了好幾次,我才終于學(xué)會(huì)騎自行車了。
這就是我最難忘的一件事。因?yàn)閺哪莾阂院螅儆龅嚼щy的時(shí)候,我就會(huì)想起爸爸說的話:做事一定不能光想著依靠別人,要靠自己。
(指導(dǎo)教師:李秀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