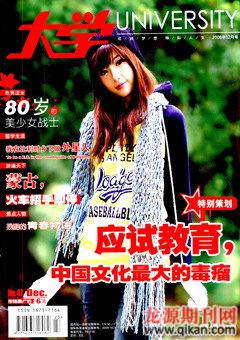那一年,我被困在大學城
楊 沙
大一開學時,一輛飛馳的校車把我從火車站直接拉到了現(xiàn)在的這片大學城。校園冷清清的,四處是黃沙和禿山。我高分考上重點大學的萬丈豪情一下跌到了谷底。
最近我和一些外校或在本部住宿和學習的同學有了些接觸,忽然發(fā)現(xiàn),這三年我白白度過了,沒有一點上大學的感覺。大學城的高墻斬斷了我求知的興致。
外人可能會說。大學城是一個學習研究的好地方,生活在大學城里,資源實現(xiàn)共享,各種學術講座、學術交流帶來一場場頭腦風暴,讓我們這些學生在通識教育的大道上行走。聽說,省教育廳還要建一批大學城呢!
事實上,這是個封閉的環(huán)境。
我們的活動范圍就局限在這個孤島之中。業(yè)余時間就是上網(wǎng)、睡覺、K歌、喝酒,連逛街購物都要坐校車到42公里以外的市區(qū),一路的顛簸讓人到了商場就喪失了購物欲望。我常常自嘲說,三年的收獲就是:體重飛快增加,打字速度增快,游戲段位提高。
大學應該是干什么的?哈佛大學校長說,是追求真理,是致力于照亮人性之美。很多人在回憶起大學生活時都提到,最大的收獲是文化的熏陶,是課上課下激烈的爭論培養(yǎng)出來的獨立思考能力。
為什么我們在這里只能背單詞,記憶書本上的知識點,應付老試?
好多人在大學城上了幾年,從來沒到隔壁學校走一走、看一看。當被人問起隔壁學校在哪里?大多同學都會搖搖頭,沒去過,不知道一墻之隔的兩所學校,卻仿佛地球的兩極一樣遙遠。
特別是我們這些文科生,就像是被高校學術氛圍遺忘了一樣。那些學術交流活動、國際學術會議基本上都在本部舉辦,從沒人通知我們參與。大一的時候,我還為此憤憤不平,校方到底還把我們這些新校區(qū)的學生當大學生嗎?漸漸就麻木了,自然而然就覺得無所謂,好像本部同學干了什么跟我們沒關系一樣。
在閉塞的西北,本來老師就容易“孔雀東南飛”。在我們這塊寂寞沙洲上,任教的老師就更容易跳槽了。我在這里的三年,眼看著老師走了一批又一批。現(xiàn)在可以到我們學校調(diào)查一下,剩下的教授級的老師根本沒有幾個。
學術理想破滅還是其次。作為文科生,不接觸社會,不參加社會實踐,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的生存方式。
大學城遠離市區(qū),周邊環(huán)境很不發(fā)達。做家教、到企業(yè)兼職、做社會調(diào)查這些其他大學生生活的一部分都似乎跟我們絕緣。跟我們接觸的社會人多半是賣水果的當?shù)剞r(nóng)民。所以,學長畢業(yè)以后給我發(fā)郵件,說到了工作崗位很不適應,一點社會經(jīng)驗都沒有,太不善于和社會人打交道了。
也是,生活在大學城中的我,觸摸不到社會的真實氣息,消息閉塞,導致了“唯我獨尊”,以為上了大學真的就是天之驕子了。盡管也知道當今社會競爭的殘酷性以及就業(yè)的艱巨性,但是因為從來沒到招聘會上感受過,所以總以為那些離自己還太過遙遠。用一位學長的話:“置身大學城,在安逸的生活下變得高傲懶惰,進入社會后一個個就變成了生活的小丑。”
編者按:也許,你也像這位同學一樣對大學城有諸多不滿,可是罵完以后,生活依然要繼續(xù)。我們可以盡情宣泄,宣泄完了,想想周圍有什么資源是自己沒用到的,沒用好的。大學年,無非比的就是誰能利用相同的資源得到更多立足社會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