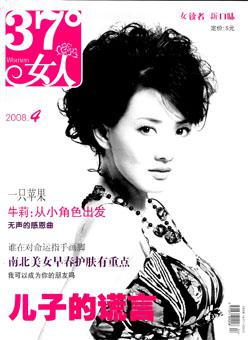搓搓你的手等
孫道榮
我看過不少醫生,但只有_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去年冬天,因為頸椎病,我去醫院診治。很多病人在排隊,好不容易排到我。他是個中年醫生,問我哪里不舒服,我告訴他,頸椎難受,可能是頸椎病犯了。他站起來說,我先按按,檢查一下。
他走到我身后。我伸長脖子,等待一只冰涼的手按上去。每次到醫院檢查,都不得不被醫生涼冰冰的手,伸到脖子里檢查一氣。雖然這令我緊張,感覺不舒服,但和所有的病人一樣,我已經習慣了。
奇怪,怎么沒有動靜?回頭一看,中年醫生正在搓手,兩只手合在一起,不停地來回搓動。見我回頭看他,醫生笑著解釋說,我的手涼,先搓一下,這樣熱乎一點。為了我的頸椎,我看過很多醫生,找過不少專家,他是第一個在檢查前把手搓暖的醫生。他這個細小的動作,讓我感動。
他的雙手按在我的脖子上,暖暖的。仿佛這只手也捂在了心上,感到一股暖流涌過。他說,冬天每次為病人聽診前,他都會用雙手捂住聽筒,直到將聽筒捂熱,才將聽筒伸到病人的胸前進行檢查。病人本來就難受,冰冷的聽筒伸進去,會讓他們感覺更糟。
搓搓手,捂捂聽筒,這些細微的動作,溫暖了一個個病人。這些細節,似乎與治病無關,與醫術無關,但它卻是一股暖流,使我們原本虛弱的身體和心靈,得到呵護、撫慰。給嬰兒喂食時,一個再粗心的媽媽,也會先將勺子送到自己的唇邊,感受一下溫度,適宜了,才會喂孩子,這就是母愛。同樣,從現在起,搓搓你的手吧,當你去握別人的手時,當你用手去撫摩愛人的臉時,當你為病人檢查身體時……將手搓熱,伸出去的,就是一股涓涓暖流。
站在窗口的父母含辛
我匆匆趕到家,客廳里空無一人。又跑到臥室。才發現他們跪在凳子上,像孩子一樣把頭伸出窗外東張西望。我趕緊喊了一聲:“爹,娘,你們干嗎呢?”
爹扭過臉看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哦。你回來了。天晚了,看你還沒有回來,我們就在這里看看……你瞅,你娘還在那兒看呢。”娘的耳朵基本上聽不見任何聲音,現在所有的交流都靠手勢。我上前拉了拉娘的手,娘回過頭看到了我,也笑了:“看了半天,咋沒看到你呢?”
我說:“我騎摩托車,戴著頭盔。跑得快呀。”也不知她聽懂沒有,她舒了一口氣,把身子抽回來,又一點點挪下凳子,攙著爹,一步步搖回客廳。我跟著他們走回客廳,把電視機打開,眼里竟有一種酸酸的感覺。
這是我參加工作16年第一次將父母接到身邊住。剛開始是沒房子,后來有了孩子是沒地方住,再后來他們年齡大了不愿意動。在我的極力勸說下,他們終于勉強答應和我住上半個月。
來到城里后,他們極不習慣,手腳都不知道該怎樣放。除了睡覺,只能在客廳里看電視。
81歲的爹已經“返老還童”,基本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他的脊椎關節錯位,使腰不得不彎成蝦米的形狀。走路已經像嬰孩一樣步履蹣跚。一搖三晃。
娘的耳朵將全世界的聲音置之耳外,但眼睛和手腳尚好,就想幫我們干點兒家務活。可做飯是液化氣罐、電磁爐、微波爐,洗衣服是洗衣機,她在農村積攢了大半個世紀的經驗,在這里幾乎一無所用。我們還一遍遍地告誡他們:不要亂動電,不要亂動氣,不要隨便出門,不要……于是,他們被“囚禁”在56平方米的小屋里,只能規規矩矩地坐在客廳里看電視。
干坐著的滋味不好受。爹還好說,他白天看書,晚上看電視,還能抽煙。娘就不知道怎么辦了,于是就拖地,擇菜,做些不需要技術含量的活兒,地拖了一遍又一遍。菜洗了一次又一次。可娘已經78歲,眼神不濟了。地拖了,總不凈;菜擇了,總有泥。私下里老婆說,別讓娘干了吧,她干了我還要再干一次。我說,你不讓她干,她會憋出毛病的。于是,娘就津津有味地干,老婆就不厭其煩地返工。
一個下午,太陽很好。爹娘在樓下曬太陽。可到了傍晚,爹娘竟還沒有回來,我就趕忙下樓找。剛到樓下,就看到娘攙著爹在另外一個單元樓道口上下打量,四處張望。我趕快迎上去說:“這么晚了,怎么還不回去啊?”
“啊……啊……我們找不到咱家的樓道了。”爹有點兒羞赧地說。“我說是那個樓洞吧,你非說是這個。”娘還在一邊添油加醋地羞他。此后,他們就再也不下樓了。
有一天上班時,路過樓下,我無意間抬頭看了一眼,忽然看到了爹娘:他們擠在靠路的窗口,正朝我揮手。我朝他們揮一下,他們再朝我揮一下,如此重復了好幾次。下班回來。我有意識地抬頭看了看那個窗口,果然看到他們在探著頭,朝我下班回來的方向張望。看到我時,他們又開始興奮地朝我揮手……從此。站在窗口的父母就成了這棟樓一道風景:兩個老人像一對老鳥一樣依偎在一起,目送著或目迎著我,朝樓下的我不停地揮著手。
也許,他們知道,自己的雙手已經無法像翅膀一樣張開,無法再將兒女護在腋下,為他們遮風擋雨,就用目光和揮手的姿勢,織一張網,將他們的孩子依然包裹在濃濃的牽盼和親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