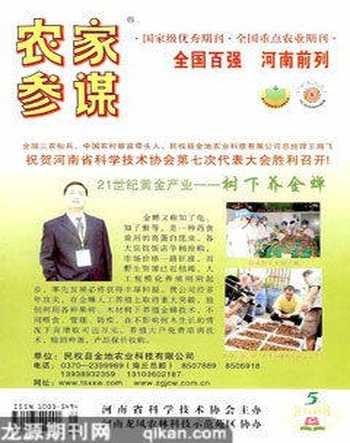浪費秸稈就是浪費資源
秸稈通過綜合利用,可以還田、漚制沼氣、作飼料肥料、生產板材等等,只要加以研發,秸稈的用途還不止這些。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孫振鈞說:“盡管國家及地方采取了許多措施,但當前秸稈資源利用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這既需要國家政策、資金的進一步支持,也需要專業技術研究的突破,更需要人們真正把秸稈作為一種寶貴資源來看待,別讓秸稈成為‘放錯了位置的資源,要形成浪費秸稈就是浪費耕地、浪費水資源和浪費農業投入的經濟意識、生態意識。”
秸稈污染及浪費問題未根本解決
調查數據顯示,我國作為農業大國,各種農作物每年產生秸稈6億多噸,其中可以作為能源使用的約為4億噸。
供應量如此可觀的農作物秸稈究竟有何“妙用”?孫振鈞說:“農作物秸稈作為重要的生物質資源,具有多種用途。利用其生產燃料乙醇。可以緩解我國能源供應緊張狀況;利用其堆肥,可以減少化肥的使用量,減少污染;利用其發酵生產沼氣或利用沼氣發電,可以顯著改善幾千年來農村能效極低、煙熏火燎的直燃式能源消費方式以及偏遠山區農村至今無電的狀況;綜合開發秸稈資源,可以提高農民收入,全面推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并大量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
盡管秸稈具備如此多的用途,然而現實狀況卻并不令人滿意。其中一大問題就是焚燒秸稈所帶來的浪費與污染。近年來,一些地區秸稈過剩問題日趨嚴重,隨意堆棄和無控焚燒成為處置秸稈的主要方式。秸稈的回收利用已成為“政府頭疼、農民心疼”的一大難題。
當前秸稈利用格局未有實質突破
孫振鈞說:“秸稈綜合利用一般可歸納為燃料、飼料、肥料、基料和原材料這‘五料。目前總的情況是,能源和飼料利用仍是主要方向,而秸稈還田、增值利用等則成為重要的發展方向。”
孫振鈞通過調查研究認為,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能源結構的優化和農村閑散勞動力的減少,農村秸稈利用表現出了五大趨向:養殖業特別是牛羊養殖的快速發展,對秸稈的消耗量不斷增加,秸稈青貯及微貯規模在不斷擴大;秸稈燃料化正由已有的農產層次的直接燃燒向規模化的集中燃料生產和供應過渡,許多新興秸稈氣化、秸稈發電等項目相繼建設并投產;隨著農田機械化作業和保護性耕作的實施,秸稈直接還田呈上升趨勢;各地環保政策特別是新農村建設的推進,拉動了秸稈作為重要物料與畜禽糞便等生產有機肥的發展;食用菌、栽培基質、環保材料等的發展也刺激了秸稈用作基料的發展。
“趨向是好的,但要轉化成現實生產力。我們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我國農村地區秸稈綜合利用比例仍很低,秸稈利用格局并未出現實質突破,秸稈因‘放錯位置而造成的浪費令人痛心。”孫振鈞分析原因說,秸稈利用仍是一個公益性很強的項目,農村地區秸稈收集困難,時間緊,運輸存放成本高,產品價位又低,必然導致秸稈利用項目綜合效益很低,不足以單獨依靠項目實現規模化和產業化發展。
他還說,秸稈綜合利用途徑多,技術層次復雜,技術研發及推廣體系尚未普遍建立。此外,目前許多企業僅能應用常規技術進行秸稈的初級加工和利用,產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高,輻射帶動作用不強。
秸稈綜合利用研究要少走彎路
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迫切需要開展相關技術攻關和政策研究。“但秸稈綜合利用研究要少走彎路,要把秸稈‘放對位置,國內的科研院校應擔負起相應的職責。”孫振鈞說。
“科研院校在秸稈綜合利用研究上應做政府的參謀、農民的朋友。”孫振鈞概括為五個“要”:要在技術層面整合不同學科的研究力量,為國家及各地開展重大工程建設及推廣服務提供技術支撐;要在政策和產業層面構建全國性信息交流平臺,為國家秸稈利用政策制定提供決策支持;要推動秸稈轉化及增值產品開發,增加農民收入;要從農業農村生態環境及物質循環的角度探索生態一經濟一社會協調發展的有效途徑;要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少走彎路。
秸稈綜合利用作為循環農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直接參與了沼氣、堆肥、氣化、培肥等不同的環節和工程。在國外,秸稈利用研究及商業化生產已獲得多項突破,充分說明了農作物秸稈用途多得驚人。“我們必須快馬加鞭,迎頭趕上。”孫振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