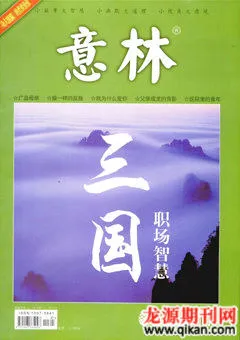一個日本人的“雙文化生活”
“跟你在一起,我幾乎忘了你是日本人。”曾有很多中國朋友跟我說。
我父母都是日本人,我從小受日本教育。我的文化背景肯定是“日本人”。學會了中國話,了解了中國文化,并不等于我丟掉了日本文化。所以,每次有中國朋友說“你跟中國人一樣”時,其實我心里不是很好受。因為我知道在骨髓里,我永遠是日本人。
麻煩的是,連日本人都開始跟我說,“你不是日本人”。回到東京老家,我母親和妹妹半開玩笑地把我稱為,“我們家里的外國人”。
后來,我移民到多倫多去,有幾年我非常努力要做加拿大人——學會加拿大口音的英文,天天吃加拿大口味的西餐,跟土生土長的加拿大人來往。結果,我變成了加拿大人嗎?沒有。人家最多把我當做“同化成功的移民”。我越來越不明白我為什么要被同化?能夠跟其他文化背景的加拿大人和平共處不就可以了嗎?
在多倫多,我也有不少中國朋友。中國移民保持自己的生活習慣,其他民族絕對比不上。去他們家里,一定能吃到中國菜,能聽到中國音樂,講的又全是中國話了,于是讓我有“回家”的感覺。我有點兒像父母親重復地結婚、離婚的孩子,還記得出生在哪一個家,但后來也有了別的家。中國文化的環境對我來說亦是家園。
不過,當那些中國朋友來我家,一定會說:“沒想到你這么西化。”因為我愛喝咖啡。只是,西方朋友來我家發現我早上吃稀飯時,一樣吃驚地說:“沒想到你還這么東方化。”
語言跟文化的關系很深,但不完全一致。人可以過雙語生活。那么,有沒有“雙文化生活”這種東西?我在和西方的男朋友相處時,盡量把生活西化:早上不吃稀飯無所謂,晚上偶然帶人家去有“異國情調”的日本、中國餐館,默默地嘗到“回家”的味道就可以了。未料,當我在家里用日語或漢語接電話的時候,男朋友難免感到“異化”,好像我從一個人跑到另一個世界似的。因為西方人不能分清日語和漢語,他都不知道我到底跑到哪一個世界。
我曾經以為,會講的語言越多,能交的朋友越多。這一方面是真的,另一方面卻不一定。好比換了好幾次小學的孩子,同學的總數當然很多了,可是他會有幾個真正要好的朋友呢?也許,有過類似經驗的孩子才能理解他的感受。
幸虧在香港有講英語的香港人,學廣東話的北方人,還有像我這樣的外國人。香港的文化環境不純,但有文化“雜種”的生命力,所以我在香港才感到孤獨得舒服。
新井一二三,一個用中文寫作的日本女作家。她出生于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畢業,后到中國學習中文和中國近代史。此后,她又曾在加拿大、香港等地生活。并于1997年回到日本,目前擔任明治大學講師。《櫻花寓言》講述了新井一二三在各國的故事,對我們了解全球化頗有助益。
(三七鳥摘自《櫻花寓言》江西教育出版社 圖/遲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