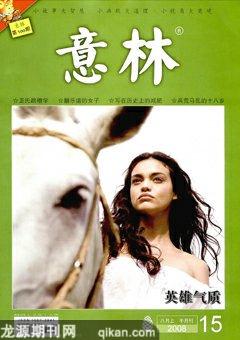2008,中國NGO元年?
雷曉宇
一夜未眠。四川地震第二天,希望工程的創意人、南都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上網搜索日本阪神地震和臺灣9·21地震的信息。
他發現,1995年阪神大地震是日本NGO成長的一個里程碑——在最初的兩個月內有100萬人,在12個月內累計有135萬多志愿者參加救援,在日本救災史上被稱為“志愿者元年”。而在1999年之前,中國臺灣沒多少人關注志愿者和NGO,在9·21之后,臺灣被稱為“志工島”。
恩格斯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巨大進步為補償的。”伴隨著一次8.0級大地震到來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慈善總動員,全國的慈善基金、民間組織、普通公眾史無前例地積極行動起來,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2008年,自5月12日之后,會成為中國的NGO元年嗎?
徐永光很樂觀:“在一個常態社會,政府是強勢的,NGO似乎可有可無。但是災難來臨的非常態社會,NGO一定是可以發揮作用,幫政府排憂解難的——災難反倒是NGO發育成熟的一個非常時機。”
李連杰帶著物資、心理醫生和審計師到了前線,他告訴《中國企業家》,壹基金成立一年來遇上了5次天災,最大的經驗就是,“一個非政府組織一定要配合政府做一些盲點工作。”他形象地把善款稱為“炸彈”,“如果你不能有效完成所有重托,你會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
這也許是災難留下的一個“遺產”:地震為NGO帶來了活力,也在嚴格檢驗它們;給官方慈善機構增添了壓力,迫使它們更加開放、透明和問責。已有分析家開始辯論,是否會產生政治上的“余震”,給予民間組織更多的空間。一位網友說:“痛定思痛之后,中國商界和政府能否借團結奮進的氛圍,切實推進一種更市場化、更持久的慈善機制建設呢?”
然而,“災難激發了民間的志愿性和參與的熱情,但是它能不能形成一個現實?隨著災情緩解、重建開始,NGO會更多地參與,還是反而逐漸退出?我覺得現在還說不好。”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說。
“恰恰相反,”中國人民大學NGO研究所所長康曉光說,“如果這次NGO在災難中沒有經受住專業和道德輿論的考驗,中國NGO的發展反倒可能有一個大的后退。”
各界對善款使用和流向的關注,已經隨著捐款額一同上升。截至5月26日12時,國內外捐贈款物總計308.76億元,實際到賬230.20億元,已向災區撥付捐贈款物90.54億元。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秘書長王汝鵬向《中國企業家》承認,這是有史以來中國整個紅十字系統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接受捐款最迅猛的一次。針對公眾的質疑——從“網易變更捐贈合作方”到“萬元帳篷”事件,處于風口浪尖的紅十字會做了一些妥協,不收取任何管理費用(國際慣例是10%)。王汝鵬解釋說:“捐贈大部分用于災后重建,使用有個滯后的過程。”
足球記者李承鵬在博客上提了一個建議:“中國慈善能不能在技術操作方面更加靈活、更加有效率?無數的人們想參與救援,但從民政部門和紅十字會的人力、精力、程序上難以完整組合他們,為什么不能建立更多的國家授權的慈善平臺?美國有無數私人慈善機構……”
“沒有什么災難是不可避免的。”科普巨匠艾薩克·阿西莫夫說。當我們擦干眼淚,重拾理性,應該承認:四川大地震給所有中國人上了一堂“災難管理”課。南懷瑾說:“以血和生命的教訓,對中國人完成了一次精神重建。”
光明天使基金理事長楊福梅在美國生活過40多年,“看到的都是人家說中國不好的東西,就算李安,所謂‘中國夢,也只是一部電影而已。”她參加過亞特蘭大奧運會的工作,知道奧運會就是一個生意,一個月之后大家都忘了,而且花的錢一定能賺回來。“但是,這次地震,中國的收獲一定比奧運會還要大——這件事情才啟發了人性的愛,啟發了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種族、不分國籍的愛心,這才是無價的,這才叫做‘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王京京摘自《中國企業家》2008年第11期 圖/孫勝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