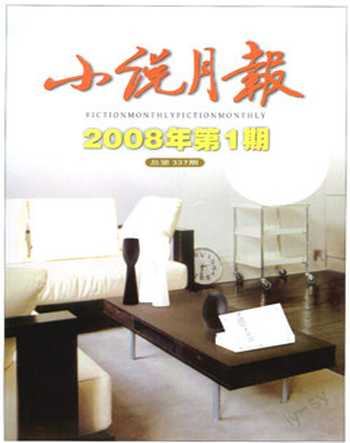在你傷口微笑
镕 暢
一
“我同意分手。”毛閃閃笑著說。
之前無數次,我一說分手她就哭。淚如雨下,淚如泉涌,淚飛頓作傾盆雨,梨花帶雨,一夜吹落星無數。有時在她宿舍,側身坐在沙發上,手拿遙控器,邊哭邊把電視聲音隨意調大或調小,以配合她的哭聲。有一次在她值班室,扭轉上身伏在折疊椅背上,無聲地抽泣,還有一次趴在公園的一棵楓樹上,邊哭邊跺腳,厚厚的楓葉在她的軟底鞋下發出清脆的干燥聲。雖然每次哭的地點和角度不同,但有一點相同,就是她不愿意和我分手。
開始看到她淚光點點、淚水漣漣或淚雨滂沱的時候,我是非常心疼的,請相信我是個男人,沒幾個男人看到女人流淚會無動于衷,況且是與自己相愛過的女孩子,但就在她哭過幾次或十幾次,也就是我正面側面假裝真裝明示暗示必須與她分手之后,我逐漸對她的眼淚視而不見。
人的心腸是怎么練硬的?第一次拿手術刀時我二十歲,那還是面對一具用來給我們做實驗的死尸,哆嗦得自己都要手腳冰涼四肢僵硬,到后來看到一個個或讓車撞得血肉模糊,或被我們像麻袋一樣縫上又拆開的活生生的人,漸漸就視為家常便飯。現在每次手術前問患者想要局麻還是全麻時,如同酒吧里的助唱小姐問客人:“請問先生您喜歡聽流行歌曲還是美聲?”
所以從一開始我對毛閃閃說“寶貝別哭別哭”,到“你動不動就哭,有話不能好好說?”再到從頭到尾看著她哭完,才說:“和我分手真就這么痛苦?”
毛閃閃拿我的手放在她左胸:“你摸摸看,我的心都碎了。”
我立即把手撤開:“干我們這行應該有超出常人的耐受力,在我看來,病人做個心臟瓣膜手術也就是被蚊子叮一下的感覺,一點都不疼。”
“我同意分手。“毛閃閃笑著說。
這次,我沒從她嗓子里聽到一絲嗚咽,沒見她眼里泛起一滴淚花,相反她一直微笑。我們站在中醫院樓頂的天臺上說話,兩只鳥兒穿著暗褐色羽衣,沉默地在落日余暈里轉來轉去,然后頭朝下,一前一后沖一株色澤深郁的橄欖樹飛去。
毛閃閃實習時是我的助手,說第一次見到我愣了很久,我穿了一件再普通不過的白大褂,但領口露出里邊的天藍色的襯衫,眼鏡的邊框部分有一點橘紅,她說就這兩點,讓我整個形象熠熠生輝與眾不同。毛閃閃后來和我約會時常常不厭其煩地提到初相識的情景,并且問我:“你還記得我當初的樣子嗎?”
毛閃閃當初的樣子?我早就記不起來了,我當時盯著她的胸部看,好半天目不轉睛,連旁邊還有別的人也忽略了。
“你這個人好色哦!”
我從不加以反駁,認為情人間這種戲謔中含有褒義。
毛閃閃對病人出奇的好,查房或是打點滴從不直呼姓名或病床號,按照年紀的長幼,分別叫他們“小帥哥”、“小美妞”或是“帥大伯”、“美阿姨”,說話時嘴角上揚,每兩個字都拉長尾音,似乎來住院的都是他們家親戚。
“人病了真可憐,任你是什么高官大亨,一樣孤獨無助。”
“時間長你就麻木了,現在還有精力發揮你殘存的愛心。”
“你干嗎老盯著我的胸和嘴,我其他地方不漂亮嗎?”
“你身上這兩個部位最美。”
毛閃閃抓著天臺護欄,看著醫院對面幾百米的地方,那兒有一所私人承包的養殖場,東邊,奶牛小羊叫上一陣,西邊,小孩子在湖里摸魚,還有人正在脫掉外衣準備下水游泳。“我要飛過去。”她說。
我走過去把她的身體扳正,看著她的眼睛:“聽到什么閑話了嗎?”
“嗯。”
“我有老婆孩子。”
“嗯。”
“我不能離婚。”
毛閃閃兩臂上揚,一腳朝后抬起,一副乘風飛去的樣子。“病人都叫我微笑天使,他們說,只要看到我的笑,就暫時忘掉了身上的病痛。我記得頭一天跟你上手術臺,病人麻藥勁兒過了,痛不欲生撕心裂肺,我整個人嚇得直往地上出溜。”
“由于個體差異,這個病人對麻藥過敏,所以不能一次足量注射,只能分時段給藥,誰知術中出血量大,手術時間延長,疼是肯定的。”
“當時,你用手扶著快要軟癱的我,在我耳邊輕聲說,鎮靜,對,就這樣,始終保持你好看的笑容。”
二
我被一陣搖晃驚醒,睜眼就看到我老婆一雙眼角和眼中大而眼尾小的眼睛。
“到點了,你今天不是有個手術嗎?早餐在桌上,我得趕緊去醫院替宣琪了。”
宣琪是一個旅居芝加哥的華人,也曾是我老婆的閨中姐妹,這次專程帶老公回國看病,住在綜合醫院。我老婆以助人為樂著稱,凡是來本城大醫院看病的親戚老鄉朋友,她無一例外全部關照,能提供什么幫助就提供什么幫助,像個專門接待各地病人的護理專員,倒顯得我這個醫生不那么有愛心。
我坐起來,慢條斯理穿衣服,從床頭柜拿過手機。
“喂。”里邊傳出毛閃閃的聲音。
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老婆,她正拎著保溫盒朝外走,并用眼睛示意我別忘了吃早餐,隨后防盜門在她身后“咣當”一聲關上了。
自從正式和毛閃閃分手,這是她第一次打電話過來。
“方治,你知道嗎,昨晚急診室那個老人,去世了。”
我沉默著。
“這老人是個老紅軍,一生戎馬槍林彈雨,沒死在雪山草地,沒死在解放戰爭,卻被我們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不費一槍一彈就殺死了。”
我右手拿著手機,左手套上褲子。
“老紅軍九十高齡,兒子去年過世,其他親人遠在國外,生病時只有一個還在讀大四的重孫女在身邊照料,他重孫女忙著寫畢業論文,我就幫他打飯買水,舉手之勞嘛,所以,他逢人就說,我也是他的重孫女。上周,他要求出院,可出院沒幾天,舊病復發,昨天半夜被送到急診。本來他那種心衰的病癥,搶救起來也不復雜,先輸氧,再靜脈注射洋地黃針。但是,急診的大夫卻不由分說給他注射白蛋白,你想啊,他當時上氣不接下氣地喘,大口大口吐血,那白蛋白根本就打不進去,就這樣,沒挨到天亮老人就走了。”
“昨天急診誰值班?”
“宋銀珍。”
宋銀珍在中醫院轉遍了大半科室,從來都是一副眼皮抬不起、整天睡不醒的樣子。有次給一個胃出血昏迷不醒的病人打完臀部針,褲子都不幫人提上,讓人家赤裸著下半身在人來人往的急診室床上晾了半個多小時,病人大口吐出的鮮血浸得滿脖子、胸前、地下哪兒都是,她熟視無睹地走來走去,被取藥回來的病人家屬指著鼻子罵她是“屠夫”,只差脖子上掛塊皮圍裙,從地上搬起半扇豬,毫不費力地放在案板上,面無表情手持尖刀剔骨。這事被病人家屬不依不饒一直鬧到衛生局,院長下不來臺,就把她調到綜合醫院門診,因為她有個在省衛生廳工作的好老子,若不是仗著這層關系,就宋銀珍的業務水準,即使不當屠夫,至少也該下崗回家推著三輪車上街攤煎餅去了。
“當醫生算怎么回事,殺人不用償命?!上月那個眼神經被門框上的鐵絲掛斷的帥哥,也是宋大夫值班,隨便給他縫了幾針,第二天一早送往了眼科病房。結果,白白住了二十天醫院,花了三千塊住院費,出院后病人眼睛一直重影。”
“幸虧你讓他到我這兒復查,我一看,掛斷的眼神經根本沒縫上,所以導致重影。但是距受傷時間太長,眼皮外傷口已經愈合,而眼皮內斷裂的神經萎縮到右眼下部的臉頰皮膚內,唯一的辦法就是把愈合的外眼皮重新割開,順原路去找先前斷開的視神經。四十五分鐘的手術都是在患者很清醒的狀態下進行的,如果實施麻藥整張臉立馬腫漲得像發面餅,想尋找視神經就異常困難。一個二十幾歲的大小伙兒,居然在手術臺上痛得殺豬一般,一個勁兒大喊:這手術我不做了,我寧可瞎了,太他媽痛苦了。”
毛閃閃在電話里啜泣,輕柔得像羽毛一樣。“他這還算好了,畢竟那手術使他眼睛不重影了,不過多受了一茬罪,多花一次錢多住了一回醫院,那個老紅軍……”
“好了,大清早的,你不是為了報喪才給我打電話吧?如果每個病人你都哭,你有多少眼淚可以用?”
“那個老人太可憐了,我覺得他像我爺爺。”
“你可以讓他的家人告宋銀珍嘛。”我從坐便器上起身,順手按下抽水馬桶的開關閥。
“和醫院打醫患官司有幾個是病人能勝訴的?”
我默然。毛閃閃說得對,醫患官司勝訴的要點和癥結在檢驗報告那里,但不等進入司法程序,聞風而動的醫生就開始到處找關系,在病歷和驗尸報告上做手腳怎么也比患者更專業更捷足先登近水樓臺。再說宋銀珍的父親曾經在省衛生廳擔任要職,除非讓死去的人開口說話。況且,老紅軍無兒無女,一個重孫女,想必也是弱女子。普通病患家屬遇到這種事情都是認命。一句話,遇到宋銀珍值夜班掛急診的病人算倒了血霉,運氣好的熬到早晨被病房收走還有一線生機,運氣不好的只能像老紅軍這樣,一命歸西。
“上次老紅軍就不該出院,人老了就像大修車,醫院就是大修廠,這樣的車只有待在廠里最安全。也怪他運氣不好,遇到宋銀珍。”
“照你說病人來醫院看病成了算命,是死是活全靠運氣?”
我大口咀嚼著面包,把杯里的牛奶一飲而盡。
毛閃閃掛斷了電話。
三
“方治,你在看什么書?”
我扶扶眼鏡皺起眉頭看著毛閃閃。
她笑嘻嘻搶走我的圓珠筆,又把我的書拿在手上反復觀看,引得圖書館的其他人都往我這邊側目。
“注意點影響。”我把書奪過來重新放桌上,壓低聲音又補充了一句,“我們已經分手了。”
“我知道,”毛閃閃坐在我對面,雙手支起腮幫子,歪斜著頭對我說,“我不會和你死纏爛打,我現在只是當你的良師益友,不行嗎?”她伸出食指抵著我下頜。
毛閃閃的確很喜歡和我聊天,她在我們科實習時,我們常常聊到很晚。我所在的中醫院地處市中心地段,前幾年前被評為甲級醫院后,更是名聲大噪醫滿為患。院領導申請報批又在附近設了一家子醫院,取名綜合醫院,毛閃閃實習期滿后,就被分配在那兒的腫瘤科。
綜合醫院建院時間比中醫院晚十幾年,醫生護士大部分都很年輕,但七十二行里唯獨醫生這行不認年輕,越老越值錢,遇到重大的醫患難點,還得請我們中醫院的專家出馬一同會診。還有,綜合醫院環境優雅,醫療設備大都是進口的,建院時連回廊邊種什么顏色的薔薇花都想到了,唯獨沒把圖書館這事規劃進去,所以,那兒的醫生常來我們這兒的圖書館查資料,還好離得不遠,攏共也就過三個紅綠燈和四個拐彎抹角的距離。
我伸手捏住她食指從我下頜拿開,摁在桌上:“好吧,良師益友,直到你有了新任男友。但,僅限于像這樣說話聊天。”
毛閃閃笑,她笑起來似乎微綠色的星星互相碰撞,發出水晶玻璃般清脆的聲音。而我急于要離開這里,我怕有人看見告訴我老婆,所以一溜小跑上了天臺。
她緊跟在我身后,并且和每個擦身而過的醫院熟人點頭打招呼。我老婆有個身居醫療系統要職的姐姐,就和宋銀珍的父親同一級別。我畢業那年,所有的同學都在為分配的事情到處活動,我也不例外,拎著份厚禮去拜訪對我們分配有著生殺大權的我老婆的姐姐。結果,我的禮被原封不動退回來,并且還留在本省最好的醫院。地球人都知道,那是因為我老婆看上我了,想讓我給她當丈夫。
在很多人眼中,我老婆優點多于缺點,永遠穿著正統,頭發從不過肩,裙子從不過膝,常年涂深色口紅掩飾其發白的嘴唇。從基因上來講,教師和醫生是最佳婚姻組合,美中不足的就是日子稍顯死水微瀾,在行夫妻之事時她也保持其冰雕式的面容,但保險。我最近又要晉升職稱,這個時候,絕不能讓毛閃閃打亂我的人生步驟。
“方治,你說對一個人最大的報復是什么?”
“殺了他?”
“這種方式太極端了,而且還得負法律責任。慢性的那種,心理折磨,生不如死,再比如說,奪妻之恨,奪子之仇……”
我瞪眼看著毛閃閃。
她突然住嘴,咯咯笑著,眨眼歪頭看著我。
“怎么了你?一直說夢話,還出了好多汗。”
老婆下床給我拿來毛巾和水。
“我夢見我拿著手術刀給病人做白內障,打麻藥的時候我的手一直發抖,抖得拿不住針管,我用力扎下去,可是卻扎在我自己的身上。”我說,“可我又感覺不到疼,就像扎在一層厚厚的油紙上。”
我發現老婆的目光有些恍惚,她緊張地看著我,我更加恐慌,這目光我似乎只在新婚之夜看到過。
老婆把水杯端出去,不知為什么,她在客廳待了好久。她最近瘦了,睡衣裹在身上顯得空空蕩蕩,她幾乎一有時間就去醫院看望宣琪,把兒子送到了他姥姥家。
“我這周去看望一下宣琪的丈夫?”
“不用,真的。有我一個人招呼就足夠了,況且你最近因為晉升職稱的事,把自己搞得太累了。”老婆摸著我額頭,溫柔地說。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伸手將她攬進懷里,她笑了笑,一臉憔悴的神情。
這么說來,老婆還不知道我和毛閃閃的事,這讓我大松一口氣,如果之前的事她沒有所聞的話,那么之后她即使聽到什么,我也無所畏懼了,因為,我和毛閃閃已分手,我當機立斷在緊要關頭和她分手了。老天眷佑,毛閃閃也沒再表現出任何糾纏的行為,就是有事沒事愛打個電話,想拉我去天臺上聊天,似乎我們的關系真的一下子退到良師益友的位置。
這次是我打電話約她到天臺的,手機響了好半天,接聽的是毛閃閃的同事,按照我和毛閃閃以前的約定,我們在對方的號碼上分別輸入陌生名字,所以,毛閃閃的同事對著話筒說:“請稍等啊,她去洗手間了。”
從話筒里傳來軟底鞋“沙沙”地摩擦地面的聲音,聲音停在洗手池前,水龍頭擰開又關上,隨后才到手機旁,帶著輕微地喘息:“喂。”
和毛閃閃分手后,我整個人也空了一片,生活重又變得無驚無險,但魚和熊掌之間我選擇了后者,作為醫院最被看好的眼科醫生,我以思維精準果斷著稱,在手術臺上,片刻的疏離就能加深患者的痛苦和留下不可想象的后遺癥。
我問她干什么去了,手機怎么隨隨便便放在桌上讓別人接聽。
她笑著說:“無欲則剛啊,心地無私天地寬,既沒偷人存折又沒抱人孩子,誰想接誰接唄。”
剛上天臺,我就說我最近夜里經常做奇怪的夢,她電話又響了。
“自家人客氣什么,于公于私這都是我應該做的。”她對著電話里說。
“我說你能不能關機,我想安靜一會兒。”
毛閃閃聽話地把手機關掉揣進白大褂衣兜,“我表姐夫住在我們病房,表姐感謝我為他買了頂帽子。”她特別喜歡和人分享她病房的人和事,病人也特別愿意和她聊自家的事情,那些家長里短在她嘴里轉換成驚訝、悲傷、感嘆,再從她嘴里說出來時,又成了沉痛的總結和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悟,她應該去當主持人或是演員,當護士過于感性了。
“表姐夫很要面子,我提前為他買了頂鴨舌帽,比醫院的帽子好看,戴著還蠻帥呢。”
我側身靠著天臺護欄,斜睨著街上的人群,沉浸在自己的夢魘里,先任她自說自話。
“人生充滿了傳奇。表姐夫的生意破產了,表姐為治他的病,居然想出怪妙的一招,讓他的前女友為他負擔醫藥費,前女友已為人妻,況且,表姐夫當年為了跟表姐出國拋棄了她,就是表姐搶了女友未婚夫的俗套故事,這是奪夫之仇啊,表姐夫的前女友當然不干,表姐就想了一個高招。”
我無動于衷,毛閃閃的邏輯和話語有時讓人覺得像個小孩子,很多的事情只有一,她就能在此基礎上杜撰出二,甚至五。
“表姐夫當年出國時,前女友已懷了他的孩子,后來嫁了另一位男子,名正言順生下這個孩子,現在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表姐夫的父親還留下一些遺產,但在遺囑上注明,只有兒子和孫子才可享用,而表姐還沒為他生下一男半女,也就是說,倘若表姐夫真一命嗚呼,表姐就人財兩空,就這么著倆女人為保全各自的利益立了協議,表姐夫前女友出錢出力幫忙把姐夫治好,表姐負責為她保密到底。”
“如果你表姐夫病好不了呢?”
毛閃閃看著我,沉默了很久才答非所問說:“方治,我從一開始給你當助手,就覺得你身上有種冷靜的魔力,我很奇怪,病人在手術臺上痛得齜牙咧嘴,而你自始至終都在微笑。”
“醫生的笑是病人精神的鎮痛劑,我也咧嘴齜牙,他們心里就更加沒底。”
“在病人痛不欲生時笑得好壞,也是判斷一個醫護人員職業水準的度量儀?”
日落前一小時,微風把她頭上馥郁的洗發水味道散播在空氣中。起初我被毛閃閃吸引,因為她有跟睡蓮花一樣純潔的、充滿朝氣的心,迎著我逝去的童話開放。但人是現實的,過不了多久她就會想跟我生孩子結婚,而這些,我已經跟另一個女人做過了。從一個山里娃混成省城著名醫院的眼科大夫不是件容易的事,況且,那女人的姐姐還將主宰我的升遷。
“我最近常做些莫名其妙的夢,”我盯著毛閃閃的眼睛,“你是個好女孩兒,但我們沒有任何可能,這一點你很清楚,趁我老婆對我和你的事毫不知情,趁還沒鬧到滿城風雨,在我們的婚姻中,她是毫無過錯的一方,我們說好了分手,你就別再想用什么小聰明、小伎倆……”
毛閃閃笑,然后一句話沒說,轉身離開天臺,她軟底布鞋一層層拾階而下,直到靜止,我才慢慢走下天臺。一位老人在醫院林蔭道的小石凳上吹著他那悠長的小曲,干瘦的手指按著笛子一端的小洞,音符像刀片刮著玻璃器皿一樣單薄清脆,他年幼的孫子眼上裹著紗布,雙手撐在膝上,靜靜地聽。
四
昨天,艷美的陽光還把小區罩得金黃,一株株叫不上名字的緋色的花,粲粲于滿眼睛光之下,怎么一夜寒光,整個世界像冰窟一樣,顏色死白泛青,周圍的樹木現出陰森可怖狀,似有大隊人馬躲在暗處,一下子從陰翳的樹叢背后殺出,我猛地醒來。
我拽起枕巾擦干凈額頭的冷汗,赤腳下地,發現老婆一個人坐在客廳,我過去把手放在她肩上,她猛地轉身,受到驚嚇似的張大嘴巴看著我,嘴角微微顫抖,滿面是淚。
我用胳膊環住她,問她怎么了,她掙脫我手臂大鳥似的跑到廚房。我猜想,她一定是為宣琪老公的病和好友今后的處境擔心。上次有位鄉下大伯來醫院做膽囊切除手術,她也是跑前跑后半個月,也這么暗自替人家落淚。
老婆站在灶臺前用勺子輕輕攪動鍋里的湯,我在她身后用雙臂圍攏她,讓她尖瘦蒼白的臉埋在我的頸窩里。我們是那種在家里很有默契的夫妻,但她很少和我一起逛街或出門,有一次她說:“我們倆出去,都以為我是你姐姐,其實你是我老公,我無意間繳獲的戰利品。”
我把車子停在圖書館門口,環顧左右沒人注意,一貓身進了對面的樓道,毛閃閃正揮動胳膊做向前、向上下、向左右的抻拉動作,聽到我上樓猛地回頭,秀發在風中甩了個漂亮的弧型。
“你怎么知道我在這兒啊?”
我慢慢走過去。
“哎,你又做怪夢了?”
我緩緩點頭。
“我剛剛在圖書館看書看累了,上來讓眼睛放松放松。”她說,把一只腳搭在天臺邊沿開始壓腿。
天臺中央有個水塔,漆成墨綠色的木頭蓋子上擱著的一本書,翻在49頁,最上面一行寫著:“化療及手術后應以氣血雙補,增進食欲為原則,可飲用北芪瘦肉湯、蒸雞蛋豆腐……”
“哦,告訴你,胃鏡檢查結果顯示,我表姐夫的化療效果非常好,腫瘤縮小了很多,他幸運地成為了新輔助療法藥物有效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他從吝嗇打開的三分之一的窄門之中擠了過來,又看到了一片陽光。”
“哦,這么說,他生命沒危險了?”
“是啊,這真是奇跡。看來,兩個女人的齊心協力就能挽救一條男人的生命。”
“但愿這樣愛的奉獻多在醫院里發生。”
“你真的這么希望?”毛閃閃哈哈大笑,故意把頭一歪,其模樣仿佛凝視谷粒的麻雀,她詭譎地看著我的眼睛,突然唱起歌來,“你傷害了我,卻一笑而過,你愛得貪婪我愛得懦弱,眼淚流過,回憶是多余的,刻骨銘心就這樣的被你,一笑而過。”
“別唱了,聽你唱歌我還不如從這兒跳下去。”我指指馬路上像甲殼蟲一樣的車流,以及在地面上像螞蟻般蠕動的蕓蕓眾生,“給你個忠告,可以多說話,但是少唱歌。”
“高興嘛,我表姐夫生命沒危險了,我當然開心。唉,方治,你想過沒有,如果是你的老婆拿著你掙的錢去給她前夫治病,并且,你在毫不知情中把她那個男人的兒子當寶貝似的養著,供他上學、成長、出國,對了,沒準出了國就能去認他的親生父親,愛的奉獻到這種地步,真是可歌可泣。真的你設想一下,倘若你要是那位丈夫會怎樣?”
我一把捏著毛閃閃的后頸,這姿勢迫使她不得不直視我的眼睛:“你恨我也不用舉這么個例子,但恐怕要讓你失望了,我和我老婆的關系像長城一樣牢不可破,堅不可摧。告訴你沒有倘若,我老婆嫁給我的時候是處女。”
然后我丟下她大步走向天臺側門。
“方治,這年頭連性別都能隨時更換,處女也凈是假的,你是醫生你應該知道。”
毛閃閃在我身后喊。
毛閃閃勇敢地在前面跑,隨手掠過身邊的灌木叢和樹梢,到了山口的高處。我站住腳,往下的道路通向兩側,水也向兩邊流。毛閃閃驚喜的聲音像遠方山谷里的鐘聲向我傳來,我微笑了,不是用嘴,而是用我手中的針尖,扎向她送給我的微笑。迎著山澗吹送來的芳香,我注射麻醉的針法和手術刀法更細膩、更沉靜、更老練,一聲呼叫墜入山崖。我醒來,冷汗淋淋地跌在床下。環顧四周,家里只有我一個人。
毛閃閃很久沒給我打電話,也沒約我去天臺,直到宋銀珍兒子舉行婚禮。
中醫院和綜合醫院三分之一的人都來賀喜,這人數不算少,因為有三分之一在上班,三分之一去世或退休。自打宋銀珍進醫院上班的頭一天起,就沒人見過她漂亮過,現在上了年紀更是像水發的海參,一對腫眼泡像兩條蜉蝣蟲趴在她臉上,腳面高出皮鞋二分之一,像船舷似的。據說新婚沒幾天就從她家窗戶傳出吵鬧,丈夫說她:“屁股像磨盤,腳像土豆蛋,腿肚粗得扭不轉。”婚后不到一年男的就援藏去了,先是說修龍郎公路,后又說修青藏鐵路,青藏鐵路修好后又說想留在那兒建設更加美麗的新西藏。所幸兒子遺傳了其父的英俊高大,帥氣挺拔鶴立雞群。新娘是個小圓臉的可愛女孩子,嬌羞地依偎著新郎給大伙敬酒。
宋銀珍磨盤似的肥臀擦著餐桌的邊緣,挨桌兒囑咐來賓吃好喝好,這個一輩子沒遭過艷羨的女人,終因生了個好兒子而揚眉吐氣了一把。有人起哄讓新郎自曝一下戀愛經過,再讓新娘當大伙面保證一下以后怎樣孝敬婆婆,宋銀珍樂得肥肉亂顫快倒在座椅上了。
新娘隨新郎走上飯店中央用紅毯子臨時搭的臺上,剛環視大伙一圈臉就又紅了,她說:“今天是我們大喜日子,也是我們和親戚朋友告別的日子,我要和我的丈夫宋樂去國外發展,這一走,或許就是遙遙無期,我們的媽媽就拜托大伙照顧了。”說完她和新郎朝大伙深深地鞠了一躬。
大伙鼓掌,有人說,年輕人有志向,去國外發展,好啊。有人說,瞧宋銀珍,今天可把一輩子藏在背后揣在腋下的臉全露盡了。但宋銀珍表情卻成了豬肝色,她從座椅上站起來,使勁揮舞著一只粗胳臂,大聲說:“不行,我不同意,你們要出國這么大的事我怎么不知道?我一輩子含辛茹苦,守活寡似的養大兒子,就是為享天倫之樂。不許鼓掌,都跟著瞎起什么哄!”她用手指著新娘說:“要走你一個人走,只要我活著,絕不讓我兒子出國。別說出國,出省也不行。”
婚禮現場一下啞了,新娘柔情款款看著新郎:“親愛的,你抉擇吧。”
新郎幾乎連想都沒想,昂著頭隔著幾排桌子干脆利落地對宋銀珍說:“媽,我想好了,我離不開小滿。”
宋銀珍肥胖的軀體和椅子一同倒下。
婚禮現場變成急救現場,新娘的花車充當了救護車,同事忙著給盛裝的新娘婆婆做人工呼吸,來賓們不歡而散。毛閃閃站在飯店門口和那個名叫小滿的新娘雙手相執臉對臉說話,我站在幾米開外,朝毛閃閃打了個手勢,她就跑過來對我說:“有什么事嗎方醫生?那天你發那么大脾氣,我以為你徹底和我絕交了。”
“怎么,看上去你和新娘很熟啊?”
“哦,你說小滿啊?她就是被宋銀珍誤診致死的老紅軍的重孫女,我們早就是好朋友了。”
我思想開始游離,不由回頭去看,新娘那雙水汪汪的眼睛,笑得像矢車菊,新郎雙手撫著她圓潤的肩,微風將她白色婚紗的邊緣吹得向一邊飛起,她身后的天很藍,藍得像要把她頭上的滿天星花朵揉進去一樣。
五
宣琪的丈夫就快出院回國了,我才和老婆一起去探望。
我家的外交策略,女主外,男主內,女管政治,男抓經濟,必要的時間必要的事情我們才一道出面。再就是我前段時間忙著滅火,除了晉升、工作、吃飯和睡覺,要騰出空來清理來自于毛閃閃方面的遺留問題,聽她講她在病房聽到見到的秘聞趣事。在我看來,無非是她對我余情未了,借題發揮。而我也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扶她上馬,拍一拍,然后輕輕揚鞭,滿懷眷戀之情目送她走遠,這叫善始善終。
今天,陽光很給面子,照著我們一家三口高高興興地走進綜合醫院。之前我擔心會遇到毛閃閃,這也是我不愿探望宣琪丈夫的原因之一,若當著我妻子露出破綻,后果可不堪設想。但現在不怕了,屈指一算,我跟她分手已有一陣子。多大的眼科手術,時間久了也會平復得像沒開過刀,至少從外表上很難發現。OK,風平浪靜,我家庭事業又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我站在病房窗下,老婆和宣琪坐在同一張病床上,我兒子被宣琪擱在膝蓋上啃一只蘋果,宣琪的丈夫眼角嘴角都是笑意。如果帶個相機拍下來就好了,簡直就是一幅友情親情交融的合家歡圖。
毛閃閃就是這個時刻進來的,手里拿著一支較大的針管。
“方醫生來了,上次在圖書館借你圓珠筆沒還你呢。”
“一支筆而已,不用還了。”
她咯咯笑著:“你當我是感謝你呢,就是一支破筆嘛,還沒寫幾個字就沒油了,害我筆記還是沒做完。不是想還你的筆,是想讓你賠我沒做完的筆記。”
我老婆和宣琪微笑著同時從床上站起來,給毛閃閃騰地方,看來她們和這個愛說笑的女護士的確混得很熟了。
毛閃閃走到病床前,伸出一只食指在病人胳膊上探測了一番:“今天再抽個血,如果你各項指標都很穩定,就可以出院。”
她選中病人前臂中央最粗的一根血管,用酒精棉消毒,頭也沒抬又說:“方醫生,忘了給你介紹,這是我表姐夫,”又回頭看了一眼宣琪,“那位是我表姐。他們專門從芝加哥回來看病。”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在藍色防菌帽和口罩之間朝我眨了眨。
病人上臂的止血帶“啪”地松開,鮮血涌進針管,我兒子“嗖”地從我老婆懷中跳到地下,靠近床沿,仰起小臉看著病人,而那位毛閃閃的表姐夫,極其自然地伸出另一只手,摩挲我兒子的頭,輕柔地說:“小寶。”
慣性使我的微笑暫時停不下來,但臉部肌肉開始痙攣,大腦空白了一會兒,又以每秒三十下急速旋轉。窗外的云在向后倒置,把剛剛包在云絮里的毛邊向外層翻卷。
毛閃閃干凈利落地拔出針管,將針頭朝上,一雙盈滿笑意的眼睛直視著我,說:“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的感覺,一點都不疼。”
【作者簡介】镕暢,女,生于山西陽泉。著有長篇小說《花影》、《2008》等。有多篇小說被多種選刊選載。曾獲2006~2007年度《小說選刊》優秀短篇小說獎。《芭蕾第二十三拍》在《韓國月刊》文學雜志發表,并被美國某刊物連載。山西省文學院首屆簽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