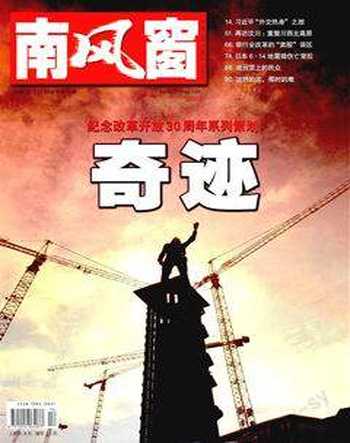彌合經濟利益的分化
郭 凱
一個政黨走向現代民主政黨,它在調和所代表的不同群體、階層的經濟利益訴求中,會形成相對平衡的經濟分配政策。3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為考察這一過程提供了充分的現實樣本。
當中國經濟改革即將走過而立之年,人們發現仍能夠支撐對繼續改革之樂觀情緒的最大歷史共識,就是當經濟生產從政府之手分離出去,過往國家、單位和政黨組織對個人從政治、經濟到生活的全面控制力,也一起消解了。
30年的改革,相對客觀地證明了有了生產自由,一部分人有更大的能力創造更多的財富,且不論這個“能力”是否要求附帶政治、出身和機會的條件。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國呈現出巨大的貧富差距和新的等級差別;執政黨體制內的政治經濟代表立場出現了分化,它與體制外的社會分化相互重疊,彼此強化。政黨的人格
過去的30年,本質上是執政黨運用國家權力推進改革,盡管30年中許多重要的變化與執政黨的主觀意愿并無關系。
一個政黨作為集體政治行動的組織形式,使它與其他政黨相區別的黨性本質或者政治經濟人格,往往有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政黨,代表哪個社會階層或者階級的經濟利益,二是作為執政黨,執政國家的政治目標。由《資本論》、《共產黨宣言》這些理論綱領奠基的共產黨,作為政黨,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代表勞動者階級的經濟利益,作為執政黨,要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
上個世紀70年代曾在中國駐英大使館工作的于日在2002年的《旅英十年——重新認識資本主義》一文中披露,上世紀70年代末主管工業的副總理王震在英國訪問時對英國的感觀,可以從一個側面刻畫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目標:英國搞得不錯,物質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我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對照此,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所說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帶動其他人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標,與共產黨一貫的政黨人格相當一致。
在這個朝野耳熟能詳的改革定位之外,國家包括執政黨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精英群體,也熟知鄧小平所規劃的另一更完整的改革目標:“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并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于實現這三條來檢驗。”——這是1980年8月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的講話。之后,中央政治局將這一講話向全國公布。
分裂與彌合
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考驗后,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講話中“三個有利于”的標準——“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對于之前的版本,發生了調整。
1992年的這“三個有利于”仍然沒有遠離執政黨的經濟利益代表基礎,但民主改革規劃的褪去,加上之后產權私有化改革和私營經濟孵育的新資本階層出現,最終在21世紀初引發了一次執政黨黨內的裂變。
其實,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上,就可以看出改革的變化:在最早的改革目標的排序上,先富、先富帶動后富和追求共同富裕的公平性中間是沒有“優先”性目標的。但是為了更大的致富效率,改革目標隨后被變更,“公平”被排到了第二位。
在共產黨2001年歷史性的“七一”講話開放新興資本家階層入黨通道之前,黨內對新興階層的政治爭論從學界到高層政界,達到了白熱化的地步。當時有若干省委的主要領導同志甚至在雜志發表公開文章反對資本家階層入黨。但是作為剛剛邁向現代化道路的執政黨,中共并沒有在黨內對綱領改變等重大政黨政案進行發起、辯論、投票決議、發布、再發起修訂等的民主程序。在各方討論并沒有結束的時候,“七一”講話最終定調。事實上,這也是符合當時的社會政治現實的。
事后,有中共黨員對此繼續表達不同意見,其中流傳最廣的就是學者胡鞍鋼的一封公開信。而中央在“七一”講話之后組織中央宣講團進行會議討論時,據當事人回憶,與會人員決定對資本家階層入黨與共產黨政治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避而不談,因為解釋不清楚。
即便如此,歷史不再回頭。資本家階層成為共產黨員的數量漸漸增長,執政黨以及其管轄下的政府機構,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中開始越來越明顯地反映出資方的利益。過去對各類企業中和國企改革中的勞動者保護缺失、多年阻撓勞工組織成立,還有最近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勞動合同法》中的立場遭遇的圍剿,以及黨內持久不散并且延伸到黨外的左右派矛盾,都清晰地記錄著執政黨在經濟利益基礎和權力組織上的分化。
對于執政黨而言,民主改革能夠提供民主程序和渠道,讓新興資本集團中的精英進入非政黨控制的權力分立的組織體系,并且在整體上服從執政黨的制度安排。
但缺失了民主改革的執政黨,面對經濟改革釋放壯大的新勢力,為了維護執政地位,在沒有開放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只有習慣性地從中央機構直接修改政黨代表基礎,實現接納新勢力強化執政地位的目標,并且使用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這樣的詞匯,希望彌合裂痕。
可能的途徑
而當執政黨接納新興資本勢力導致自我裂變自我革新后,經歷改革的中國新興精英群體,同樣需要反思自己在中國改革中的歷史角色。
雖然馬克思把他的社會政治分析奠基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并且在當時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民主發展有限的情況下,忽視了其他影響社會秩序和社會公平的組織系統,甚至對其他系統的分析出現紕漏,但西方社會確實一直在沿著修復馬克思所分析的資本主義生產矛盾的道路上前進,并且在二次大戰后向“自由人的聯合體”這一目標大步邁進。
尤其在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那里有著自由的經濟生產,但是民選的公共權力深度介入分配公平,企業和個人的稅賦可以高到50%,不同行業之間,比如金融分析師、公務員和餐廳服務員之間,繳稅后的實際收入差距有限,國民享有和高稅賦相匹配的高福利。北歐的精英群體,享受著生活富足、社會尊敬、優良治安、相對和諧的社會關系,但是生活的奢侈程度遠不如亞洲和美國的富豪。
關于起點平等、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概念,在中國改革消解極“左”思想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解構作用。但是究竟一個社會的哪種平等應該被追求,有很大的哲學因素。部分受惠于改革的新興精英階層,價值觀發生了從排斥市場效率與相信嚴酷革命的極端,到排斥公平、追求物質的另一極端。這種轉變和這些精英走上被政治特權吸納,一起壟斷權力的道路直接相關。
無論是執政黨內的人格分裂,還是中國社會的群體分裂,在2001年之后都逐漸明顯化。執政黨中央在新一屆胡溫執政以來,努力向黨內、黨外推薦了“和諧社會”的概念。但目前“和諧社會”整體上還是一個人文詞語,如果它意在概括政黨人格,就需要明確的政治經濟內涵和政策綱領來“真實化”這一人文詞匯的意圖。
當一個執政黨存在亟需彌合的自我分化,這個黨就只能直面問題,重塑自己的政治經濟人格。如果可以用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對中國和政黨改革的規劃目標解釋“和諧社會”,執政黨自身和中國社會就都有希望誠實有序地向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執政黨既認可平等民主的政治權利要求,又認可獲得自由經濟與平等福利的經濟權利,在理論上彌合左右派別的分裂;而在具體民主權力的實行上,必然要求過去的政治特權和新興的資本特權一起受到約束和限制,整體大幅提高對財產性、資產性和報酬性收入的稅收調節,以及財富再分配的水平,使民主政府有從事公共福利安排的能力。
也就是說,當一個政黨走向現代民主政黨,它在調和所代表的不同群體、階層的經濟利益訴求中,會形成相對平衡的經濟分配政策。精英訴求與大眾訴求的折衷,就是中間道路。
目前,執政黨依然需要在自身和國家層面上進行政治改革。黨內的分化,體現在政黨和政府政策的各個層面,混雜在一起,彼此消耗、削弱執政的合法性。這樣的局面要求執政黨下一步在黨內保持中共中央最高權力形式的情況下,對黨內機構進行系統化改革,逐步調整和政府機構對口設置委員會的政黨機構形式。允許自由根據代表勞動者利益或者資本方利益、代表地方或者中央利益的分別,重組不同的權利代表機構,比如分別壯大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工商聯,另組建全國農會等。政黨機構放手行政機構的具體行政事務,黨內不同組織達成妥協意見后,再對行政部門的政策進行政治審查,逐步實現對執政黨權力機構和執政方式改革的目標。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如果執政黨黨內和社會的分化得不到修復,社會就可能滑向瓦解的邊緣。這還可能帶來特殊精英群體和暴民群體的結合,黑社會化的政權將瓦解一個民族的文明,相信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責編/劉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