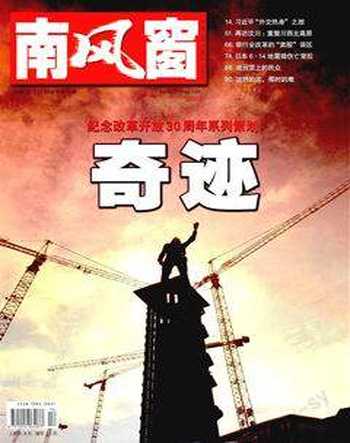陸游眼中的動物
劉 陽
1170年,陸游從故鄉浙江山陰,赴任夔州通判。農歷閏五月十八日啟程,經京杭運河至鎮江,船拋長江,十月二十七日溯行到夔州(今重慶奉節)。一路邊走邊玩,留下一部六卷本的旅行日記《入蜀記》。
書中第一只出場的動物是綠毛龜。在今安徽當涂境內,陸游寫道,“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不可勝數”。現在,安徽各地已鮮有提及,人工養殖綠毛龜則很普遍。只有江蘇常熟仍把野外原產于虞山山澗之陰處的綠毛龜,視為當地特產。
之后,陸游讓人大吃一驚——“江中江豚十數,出沒,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
先說江豚,俗稱江豬是也,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尚存千只。比它有名的白暨豚,從極度瀕危到絕種僅用了28年。兩者同屬我國特有的鯨類,但與白暨豚相比,江豚確實長得更像豬,因為它沒有背鰭,腦袋前面也沒有帥氣的長吻,整個一憨憨的大頭棒槌。據專家估計,不出50年,江豚也要絕種了,那時它的名氣應該會上漲。至于令人倒吸一口涼氣的“長數尺,色正赤,類大蜈蚣”的東西,卻完全無法想象,怎么都覺得是好萊塢用電腦做出來的,似乎,人的想象力就這樣和其他物種一起瀕臨滅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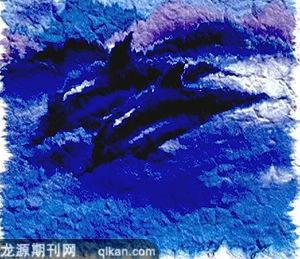
這段江面,在今天的蕪湖境內。
上世紀90年代,我國第一個江豚保護區在安徽銅陵成立。而陸游當日船發蕪湖過銅陵之后,見“巨魚十數,色蒼白,大如黃犢,出沒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成白浪,真壯觀也”,不敢妄猜是否為白暨豚。2007年8月,就在被正式宣告絕種后的幾天,有人竟在該段江面上發現了一頭白鰭豚。這個孤獨的家伙,像大江上的一個神話,在鏡頭里搖曳了幾下,就此消失。仿佛游回了《爾雅》,在里面,它曾被視為“江神”。
行至江西彭澤縣馬當山一帶,“忽有大魚正綠,腹下赤如丹,躍起舵旁,高三尺許,人皆異之”。這是《入蜀記》中第二酷的怪獸。陸游隨后記道,“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古人嘛,總會用一點迷信,幫助現代人維系心里對進步的一絲得意。
船過九江,在今赤湖附近,“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沒水中有聲”。讀到這,我再也忍不住對水生物專家的思念,如果他們碰巧讀到這篇小文,不知可否告知,這些可愛的東西,究竟叫什么?
進入湖北富池與黃石之間,“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可見,至少在南宋時,很容易拍到華南虎在湖北飲水長江的虎照。
過武昌,“得縮項鳊魚,重十斤……出鱘魚,居民率以賣蚱(用鹽和紅曲腌制的魚)為業”。鳊魚,古時叫槎頭鳊、縮項鳊。《湖北通志》記載:“鳊,即魴,各處通產,以武昌樊口、襄陽鹿門所出為最。”《辭海》里介紹,鳊魚“重可達4斤”,顯然,與先輩相比,它瘦了。
長江里的鱘魚,計有中華鱘、達氏鱘、白鱘三種。最有名的中華鱘,是世界現存最老資格的魚祖宗之一。作為洄游性魚類,中華鱘每年9—11月間,由海口溯長江而上,到長江上游和金沙江下游產卵。葛洲壩將洄游的魚媽媽攔在壩下,同時三峽工程每年10月開始蓄水,使葛洲壩以下流量減少,野生中華鱘的命運也就不必再問。老外曾想把它移到自家的河里繁衍,但拿到綠卡的中華鱘也要千里尋根,游回故鄉的江河生兒育女,應了那句話,“死也要死在中國”。
據稱,中華鱘的最高體重達500公斤。不知南宋是否有更大的塊頭?僅就陸游所見,尚足以支撐一個腌魚產業,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之后的水路旅程里,陸游先后看見“大黿浮沉水中”,“大魚浮水無數”,在荊江江面上又見“天鵝數百,翔泳水際”。黿,宋朝時廣為分布,現在屬國家一類保護動物。作為最大的淡水龜鱉類,它曾在青海玉樹通天河里馱唐僧師徒四人外加一匹白龍馬過河。
臨近目的地,陸游登岸游巫山神女祠,該地“舊有烏數百,送迎舟客”,“近乾道元年(1165年),忽不至。今絕無一烏,不知其故”。烏鴉突然消失,原因不明,發生這起“生態事件”的地方,如今已在蓄水線之下。
這就是陸游從鎮江一路到奉節,小半年的時間里,夏秋季節沿長江所見的動物。除了人之外,盡錄于此,仿佛長江之上,一座已經消失的動物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