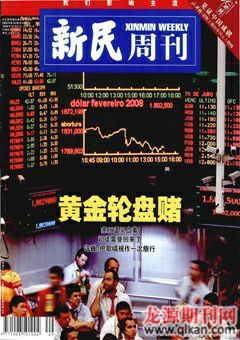故鄉的墓碑
黃 平
作家內心的搖擺、猶疑與痛苦,注定了這部作品敘事的尷尬:一部為家鄉立碑的史詩性作品,選擇了由一個瘋子來講述。
賈平凹是本次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中最著名的一個。他的《秦腔》出版于2005年,距離前一部長篇小說《病相報告》,已經有三年的時間。某種程度上,進入新世紀的賈平凹,一直面臨著一個嚴峻的問題:寫作資源的緊張。這幾年,他很確信自己“怎么寫”,反而不好把握“寫什么”了。
畢竟,從70年代末初登文壇以來,賈平凹所創作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是面對家鄉商州寫作,敘述“鄉土中國”與“現代中國”的相遇。80年代的賈平凹,相對樂觀地以《小月前本》、《浮躁》記錄“改革開放”的鄉村,“城市”扮演著“鄉村”的拯救者,主人公困境中的選擇往往是“到城里去”。90年代以后,自《廢都》開始,賈平凹更在乎的是城鄉之間的緊張關系,《廢都》、《白夜》分別從社會上層、下層兩個層面記錄著“鄉下人進城”的悲劇故事;《高老莊》、《懷念狼》反向地敘述了“城里人返鄉”的失落與茫然;夾在二者中間的《土門》,更是直接地揭示城市對鄉村的吞噬,由于土地改造,“西京”郊外的“仁厚村”化為烏有。
在這樣的敘事譜系上,經歷了《病相報告》轉向革命歷史與傳奇愛情的失敗后,《秦腔》注定是賈平凹三十年寫作生涯集大成的作品——誠如賈平凹在作品后記中所說的,這部作品是故鄉的墓碑。作為高度自傳性的作品,《秦腔》的主要人物以賈氏家族為原型,而且,作家通過家族的命運,記錄城市文明不斷擠壓下的棣花街,土崩瓦解的鄉情風俗與禮教世界。
一個大作家一生總要寫這樣一部作品,向被歷史埋葬的童年與故鄉致敬。不過,這一類作品容易沉溺于充滿自戀的回憶中,任由軟弱的抒情戕害作品的藝術價值。幸好,寫作鄉土命運三十年的賈平凹,對故鄉的“真相”有深切的體味,“樹一塊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一方面,作家懷念著幼時“腐敗的老街”與“濕草燃起熏蚊子的火”;另一方面,作家哀悼著當下故鄉的塌陷,悲憫地注視著那些下煤窯、撿破爛的男人與打扮得花枝招展進城去的女人。賈平凹沒有回避自我的分裂:“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與痛苦,我不知道該贊美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
作家內心的搖擺、猶疑與痛苦,注定了這部作品敘事的尷尬:一部為家鄉立碑的史詩性作品,選擇了由一個瘋子來講述。小說第一句話是直接干脆的表白:“要我說,我最喜歡的女人還是白雪。”不過我們隨即得知,這個叫“引生”的“我”是個瘋子,小說開始白雪就嫁給了當地望族夏家最出息的后代,大學畢業后留在省城從事創作的夏風。瘋狂的引生偷來了白雪的紅色胸罩,又在靈魂的譴責中出于懲罰閹割了自己。就是這樣一個陷入無望的愛情中的癡漢,一邊念念叨叨著內心的愛戀,一邊絮絮敘述著清風街的歷史,以及他所見到的荒唐混亂的現在。在引生的瘋言胡語中,清風街家家戶戶的“生老病離死、吃喝拉撒睡”漸次展開。
在這個意義上,賈平凹有意將《秦腔》寫成了“敘述人”不可信的“偽史詩”,或者說,以反諷的方式完成了當代文學的史詩寫作。這種分裂同樣制約著故事的編織,賈平凹始終懷疑那類結構清晰技巧嫻熟的“故事”,能否呈現復雜的故鄉生活?在《秦腔》中,賈平凹繼續著《高老莊》開始的“無序而來,蒼茫而去”的筆法,以“細密流年”的敘寫,“盡量原生態地寫出生活的流動”,紀念著“秦腔”所代表的傳統與鄉土的消亡。畢竟,面對日益荒蕪的世界,除了勉力講好故事以外,作家何為?故鄉已死,不朽的是文學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