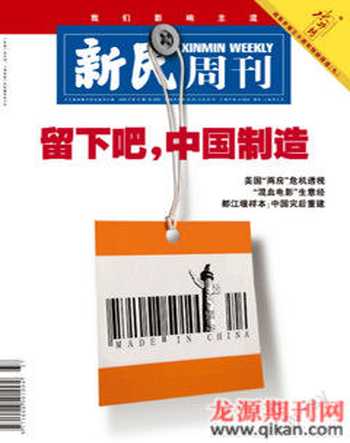當太陽從左邊升起
王曉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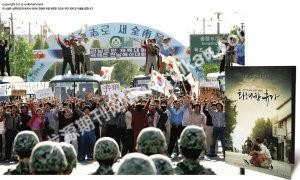
我對這部電影的藝術表達有所不滿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細節。
凌晨時分,大批士兵全副武裝登上軍用飛機,長官告訴他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終于到了向敵人復仇的時候。眾所周知,他們的敵人在北方,于是一個士兵問:“我們是去攻打北方么?”長官嚴肅地回答:“攻擊地點是高度機密。”飛機繼續飛行,太陽從左邊升起,士兵突然意識到他們是攻打南方的先頭部隊。他們的敵人是他們自己國家的人民。這是《華麗的休假》的開篇,接下來的情節證明長官多慮了,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只要把人民說成敵人,軍人就可以把人民打得落花流水,沒有絲毫仁慈之處。
電影的原型是韓國民主運動中的標志性事件——光州起義,但我接下來談論的主要是《華麗的休假》,我試圖把電影和事實區分開來。《華麗的休假》長達兩個小時,我覺得最好的就是“太陽從左邊升起”的片段,這個細節像飛往南方的軍用飛機,輕盈然而壓抑。還有兩個片段,我曾感動過:一個是已經解甲歸田的前軍長,重新拿起武器射向昔日的部下;另一處是出租司機默默升起黑色的旗幟。可是,這更多的是觸動了我的歷史感,而不是藝術感。
從敘事上看,這部電影基本還是“官逼民反”和“革命加戀愛”的模式。我對這部電影的藝術表達有所不滿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細節。阻攔學生上街的老師,轉變態度,幫助學生抹上保護眼睛的藥膏;男醫生決定冒死上街營救傷者,大聲呼喚有誰愿意同去;女護士在最后時分,發出凄涼的呼喚:“親愛的光州人民,請不要忘記我們。”——這些都很悲壯,可是我總覺得有些似曾相識。看到被妻子勸回家的市民,趁妻子睡熟重新回到最后的陣地,我甚至有一點懷疑,那么一個不眠之夜,妻子怎么可能如此熟睡?更讓我不滿的是,整部電影缺乏來自“敵人”視角的細節。
對于光州起義,我并不反對涇渭分明的判斷,一邊是獨裁者的軍隊,另一邊是贊同民主的市民。但是,一部電影如此涇渭分明,這不是我所期待的。我特別喜歡“太陽從左邊升起”的片段,因為這個細節來自“敵人”的視角。可惜這種視角隨后消失,不僅士兵被簡單化,反對學生上街的人物也被臉譜化,最初阻攔學生上街的老師,就像一排面具,他們的內心是被忽略的。反對士兵的市民則被英雄化,他們得知軍隊即將撤退,跑到軍隊面前做出各種挑釁行動,電影再現這種情景,這沒有問題,可是以贊美的方式再現,這是我無法認同的。士兵列隊保持沉默,市民的挑釁就是多余動作,這個時候還不如拿出相機,記下這個時刻。
由于缺乏細節,尤其是缺乏來自“敵人”視角的細節,電影對于街頭運動和武裝抵抗幾乎是完全的正面歌頌。歌頌也沒有問題,我當然不會站在人民的對立面。但是,街頭運動和武裝抵抗不是民主運動的專利,尤其武裝抵抗幾乎是民主運動的特例。在電影中,我只看到了街頭運動和武裝抵抗,如果不是對于電影背景光州起義的了解,很難看出其中的民主理念。重新回到光州起義,當年市民曾經圍繞是否武裝抵抗產生很大分歧,可是這種政治觀念的區別在電影里變成了家庭觀念的區別,妻子紛紛勸丈夫放下武器,回家是岸,這使得《華麗的休假》更像一部大片,卻難以成為經典。
士兵發現飛機南轅北轍,沒有阻止他們執行命令“太陽從左邊升起”不會妨礙“太陽照常升起”,這就是我看過《華麗的休假》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