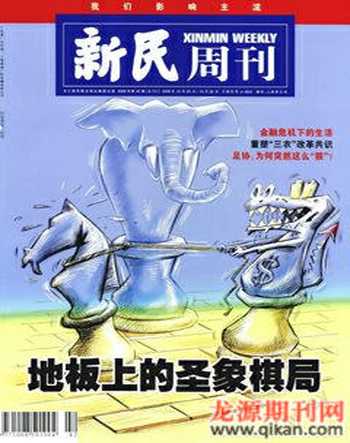浮生一記,三世三生
王悅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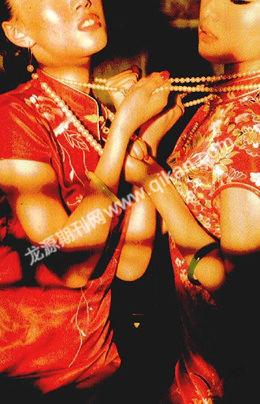
從話劇《浮生記》開始,M50將從視覺藝術走向全方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為繁榮和發展上海的文化做出新的探索。
整整200年前,那是清代嘉慶十三年,長洲文人沈復(字三白,號梅逸)用飽含深情的筆觸寫下了自傳體小說——《浮生六記》。一時間,作者和妻子陳蕓之間美好卻哀婉的故事迅速流傳開來,令人唏噓不已。文學大師林語堂甚至將此書翻譯成英語,并由衷地評價說:“蕓,我想,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在1943年的上海,戲劇電影大師費穆又把這部小說編導為同名話劇,并由喬奇、劉瓊、沙莉、盧碧云等明星擔綱,整整連演了342場。時人評論該劇“在人倫的立場上作起了美麗而又感傷的詩篇”,并稱之為“一首哀婉悱惻的抒情詩”,“不知會使多少的讀者或觀眾激起心靈上悲戚的共鳴而一掬同情之淚!”
65年后,又一部名為《浮生記》的話劇誕生于上海舞臺。所不同的是,這部源自200年前古人小說的話劇,已沒有蕓那樣可愛的妻子,更沒有沈三白式的完美丈夫。觀眾看到的是懷才不遇的畫家、風姿綽約的女鬼、紅杏出墻的妻子、貌似忠厚的丈夫、橫刀奪愛的閨蜜……輪番登場的角色,構成生生不息的人物關系。將兩對男女穿越百年時光隧道的悲歡離合,通過曲折生動的故事與主人公的情感糾纏,活潑而多情地演繹了出來,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一段滬上百年滄桑變遷的側影。
走進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實驗劇場,只見整個舞臺與觀眾席融為一體,幕墻延伸到劇場的第一排座位邊,屋頂的上方則橫貫一根管道,不銹鋼擋板如鏡子,映出人影幢幢,熙熙攘攘。觀眾置身其間,仿佛走進蘇州河畔的莫干山路M50藝術村。此刻,這里既是當代藝術家的派對場所,又或許是曾經某家紡織廠的一個車間,還可能是當年淪陷時期的一個破敗舞廳……《浮生記》的劇情時間是倒著走的,最后一幕才是故事的開始,而第一幕展現的反而是結局。這樣的因果顛倒與輪回,讓戲劇充滿懸疑和意外,也緊緊抓住了觀眾的心。“我們今生遇見的人是否都前世有緣?你能否輕易對一個人說:來世我們還要在一起?”導演周可的設問,被具象成整整120分鐘的離奇故事,一一呈現于觀眾眼前。
一個密閉的空間、一個工廠的辦公室、一張不變的長桌,《浮生記》中的每個故事發生在這樣一個場景之中;但它們卻分別發生于2008年、1978年、1938年和1908年四個不同的年代,每一段人生都只是歷史中的一個小小片段。通過一些裝飾與細節的改變,并利用燈光和音樂的不同,展現著時代的變遷。“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空間,讓我們去體味生命的脆弱和生命之間的奇妙關聯。”編劇喻榮軍很滿意這樣的舞臺構思。他在《題記》中寫道:“生命并不是一種輝煌的奇觀或是一場豐盛的宴席,它是一種岌岌可危的困境。死亡并不是生命的毀滅,而是換個地方生存。”對此,喻榮軍解釋道,“生命宛若浮塵,不管是激情、生死、報復,還是欲望、情傷、輪回,到終了,還是塵歸塵,土歸土。這個劇表現的就是發生在一間陋室里的百年浮生,充斥著幾段扯不清的情緣,表現了四世的輪回與追逐以及面對生死的態度與糾纏。觀眾會帶著種種意外和疑惑,與演員們一起體驗生死輪回。劇里的一些情節都是點到為止,觀眾看到最后,可能會豁然開朗,也可能仍帶有思考,這是見仁見智的。”
作為上海著名創意園區M50進軍舞臺藝術,全方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新動作,《浮生記》的上演獲得了成功。“經歷過場地改造和規劃布局之后,拓展文化創意領域成了創意園區的新課題。為此,我們組織了年輕的團隊進行專題策劃和制作,最終決定在舞臺藝術中尋找突破口。”M50園區負責人、《浮生記》總策劃金偉東介紹道,“盡管《浮生記》是小劇場話劇,但在創制中處處貫穿著M50求新求變、關注人文的創意標準,圍繞這出戲進行了攝影、音樂、服裝等一系列概念設計和產品制作。這次立體化的創作積累的經驗,為M50的下一步發展開創了新路徑。”從話劇《浮生記》開始,M50將從視覺藝術走向全方位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為繁榮和發展上海的文化做出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