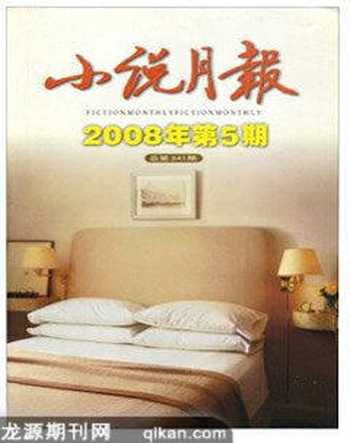陸小依
麥 家
陸小依屬于這樣一類女人,她們有令人羨慕的家庭,父母大人在社會上有響當當的名譽和地位,找個丈夫也是光光彩彩的,既有高雅的事業,又不乏生財之道——而且,他們的錢掙得絕不低級、黑暗,比如陸小依,她先生是個音樂家:一個名利雙收的職業,掙的錢沒有一縷銅臭味,香噴噴的。不用說,她們的生活從來不存在世俗的諸如行囊羞澀、位卑人微的苦惱。她們的精神也很少遭受無聊、孤獨的糾纏,因為她們受過上好的高等教育,音樂,繪畫,文學,她們或許缺乏創造的天才和熱情,卻不乏欣賞、品玩的興致和經驗。當周際出現某種痼疾,讓她們感到生活有那么一點生澀的苦味時,她們就親近藝術,步入夢想世界,與偉人和天才們細細交談,親親密密,如癡如醉。多年前,我寫過一則短詩,其中有一句話是從她們身上提煉出來的:
她們的肉體完好如初
她們的心靈也完好如初……
這是我曾迷戀過口語詩的證據,如今我總是想把它藏起來。因為,這其實是一條假裝貂尾的狗尾巴,不光榮的。口語詩讓我們已經平庸、弱智的文學變得更加平庸、惡俗,我為自己曾經迷戀過它感到羞愧。但是陸小依,嗬嗬,由里到外都完好無損的陸小依們,看到這句話一定會感到親切的,因為這說的就是她們——她們的鏡子!這樣的人,你想她們一定有一張快快樂樂的面孔,咯咯的笑聲每天從她們喉嚨里播出,像只受寵的小鳥。在沒有見到陸小依之前,我就把她想象為這樣一人:每天像朵花一樣在微笑,收藏不盡的笑容使她顯得格外甜蜜可愛。
但是那個夏天,在那個帶點兒魔術氣息的演播廳內(眼前的一切隨時都可能發生面目全非的變更),我第一次見到陸小依,我詫異地發現,我對她的想象純屬“胡思亂想”。風馬牛不相及。毫無疑問,這是個美麗的女人,而且由于年齡和閱歷的關系,這種美麗顯得尤其成熟。沉甸甸的,像果子一般可以摘下來。她個兒不高,但身材勻稱、豐滿,面容精致典雅,有一種高雅和從容的氣質。
微笑?
我要看到微笑。
沒有。
確實沒有。
我從她美玉一般溫婉的臉上未能捉到一絲半縷的歡顏笑跡。除了美麗和優雅,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流散于她貌外的那份寧靜和神秘的神情。后來我覺察到,這多半源于她那雙閃亮卻又憂郁的眼睛。這雙眼睛似乎有近視的嫌疑,因為其目光總是蓄在眼眶內,被一團霧狀的毛茸茸的東西所困擾,少有遠放。凝視這雙眼睛,你會陷入一種水草般柔軟的沉思和空想。我還要說,從這雙眼睛中,你很難看到陸小依幸福的家庭和優越的生活。坦率說,我感覺陸小依不是這雙眼睛的主人,因為它過于潮濕了。
我記得,在我們出于禮貌而作的簡短交談中,她不是沒有一點笑容,而是有一點,那也許是想給我一點隨便和親切吧。不過,事實上這笑容并沒有讓我感到親切或隨便,反倒使我有種為難于人的尷尬和不安,好像是我迫使她做了件她不情愿做的事似的。最后,我們以僧尼的做派,很謹慎,也是很潦草地分了手。就像見面時沒有握手一樣,分手時我們也沒有互道再見。
作為同事,以后我們倒是經常見面,偶爾也站下來聊聊天。時間和距離讓我們倒是變得隨便了,同時我也執拗地認定,只要我以文學的目的,以一個小說家的目光,去審視陸小依生活里的某些細節和情思,我一定可以獲得一些做小說的材料——它們不一定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小說和驚天動地有什么扯不斷的聯系呢?
想不到的是,我好像很快就得到了這種“材料”。
事情發生在2005年2月5日上午,這日子離我初識陸小依那天還不到半年,它容易使人導致錯覺,好像事情的發生,正是為了滿足我寫小說的愿望而專門安置的。當然,這不可能。事實上,這就是生活,和小說不是母子關系,而是兄弟關系。別的不說,就說小說中有的離奇、荒誕的事,生活中其實比比皆是,俯首可得。
2005年2月5日對陸小依來說是這樣一個日子:她久違的大哥從美國回來了,她心情很好,同時也有很多事情要做,要辦理。大嫂家在重慶,一家人決定回那邊去過年。現在火車提速了,從成都過去不到十個小時,而且時間很好,夜里10點發車,次日7點到達,剛好睡一覺。大哥決定坐火車去重慶,把買票的事情交給了小依。春節臨近,買票不是件容易事,好在陸小依在火車站有朋友,昨天聯系好了,今天去取票。這是件大事。此外,她預備晚上做東,宴請大哥一家人和父母大人。因為先生不在家(被中央電視臺邀去張羅春節聯歡晚會,年三十都不回來過呢),這事總讓她心歉歉的,腦筋里老有種大事未了的雜音,嗡嗡響。昨夜她顯然沒睡好,一則是和家人歡聚回來有些晚,睡遲了;二則也沒睡踏實,甜蜜的痛苦的夢做了一個又一個,一夜間幾乎將她一輩子的苦樂都濃縮地體驗了。她曾擔心今晨會睡誤時的,睡前專門校了鬧鐘,但當早晨的第一片陽光剛搭落在床頭時,她就像被陽光觸摸了似的,醒了。
她沒有馬上起床,不是由于疲倦和慵懶,而是出于習慣。成都的冬天潮濕陰冷,沒有暖氣,被窩兒內外兩重天,離開被窩兒是一件要勇氣的事情。只要可能(時間允許),陸小依喜歡等空調暖了房間再起床,這個時間一般需要五六分鐘。其間,她就鉆在被窩兒里麻木地望著窗外,任憑陽光和城市的早潮聲,一絲絲涌入房間,匯聚著,逐漸又逐漸地舔舐她的臉面和耳膜。以前她總以為自己鐘情于淅瀝雨天,其實陽光也從來沒有讓她感到吵鬧。尤其是早晨初始的旭日,不論是冬天或夏日,每每面臨她都欣悅而想擁抱。插一句,我覺得,躺在床上親臨早晨的第一縷陽光是一件滿足虛榮心的事,仿佛陽光唯你獨有,光芒的手撫摸著你——只撫摸你——又不索要回報,使你恍惚擁有了世上最溫柔無私的朋友。今天,陸小依就有這種感覺:感覺尤為清晰,強烈。她知道,這是由于心情好的緣故。
從床上起來,除了個人私事外,慣常陸小依要操持兩個人的早餐,丈夫的和孩子的。倆人的就餐內容無論主食和副食都是不一樣的,孩子是兩只雞蛋,一杯牛奶,丈夫是油條和稀飯。雞蛋,牛奶,稀飯,都是現存的,只要稍作加工即可,但油條要下樓去買,好在就在樓下,舉步之勞。眼下先生離家在外,人走嘴走,陸小依只要照顧一頭,馬上就感到了輕松和親愛。不過,今天陸小依甚至連孩子的那份也想省略掉。這是突然間決定的,原來她打算吃過早飯去父母家,現在看來利用做飯的時間趕去父母家當吃客不失為上策。就這樣,一個早晨的時光就變得松松寬寬,于是,她一反以往簡樸的作風,在梳妝臺前坐下來,準備好好美化一下面容。
其實,這是個過分的愿望,因為我們知道她貌美出眾。
梳妝臺是組合式的,分臺面和支腳兩部分,支腳是锃亮的不銹鋼,形狀是個倒立的“丫”字,左右分立,支撐著整個臺面。臺面是一只抽屜,但這只“抽屜”是別致的,聰明的,隨時可以分解出四面明亮的鏡子:正面、左右兩面及底面。平時,整張梳妝臺就如一張充滿現代氣息的簡單別致的小桌子,使用時,只要掀開面蓋,上下左右四面鏡子便競相鋪開,各式艷具一并紛呈,或臥,或立,你只管操使,不必收藏,因為它們馬上便可成為屜中之物(只要放下鏡面)。若要外出旅行,只需收起支腳,將兩個倒立的“丫”字壓縮成兩管手電筒般的鋼管,置于屜中,這時整張梳妝臺又魔術般地變成了一只裝有滑輪的手提箱。如果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梳妝臺(隨著你不可粉飾的歲月的到來,梳妝臺終將被摒棄),你可以伸縮兩只支腳,讓梳妝臺變成床頭柜,或茶幾,或寫字臺,或小餐桌,都可以。
嗬嗬嗬,多么聰明的一只梳妝臺哦!
兩年前,當音樂家先生從大西洋那邊提著這只梳妝臺回家時,陸小依除了感到新鮮和昂貴外(價值300美金),同時還感到了些許憂郁的苦惱。因為她敏感地想,丈夫這么在乎她梳妝,是不是暗示她天生的麗質已如煙云一般無情地散失?直到有一天丈夫告訴她,這梳妝臺其實是他的獎品,他謊稱重金購得只是想博她高興一場。這么說,原來是個誤會——布萊克會說: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就這樣,些許“敏感的苦惱”最終演繹成了一種可以玩賞的回憶。這種回憶常常像流水一樣,把她內心撫摸得干干凈凈、甜甜蜜蜜。她喜歡這樣度過每一個白天和夜晚。
現在,陽光已經大面積鋪張在陸小依的四周,陸小依自己也在幾面鏡子的幻影深處鋪張開來。此刻,房間里遠不止一個陸小依,而是三個、四個、五個,有時候是無數個(只要人在幾面鏡子中取得一個恰當的角度)。這使她油然想起了博爾赫斯的那句具有魔鬼氣質的名言:
鏡子和交媾都是污穢的,因為它們都使人口數目增加。
鏡子能幫助你看到自己的美貌,同時也讓你發現自己的瑕疵。在一個三十三歲女人的眼里,美貌正在發生陌生的衰退和變質,她們的目光仿佛中了邪似的,總是尖酸刻薄地撲在瑕疵上,并無情地將瑕疵一再放大,再放大,以致害怕地閉上雙眼。這兩年來,陸小依每每打開梳妝臺(她很少打開),總是沒什么困難就發現了自己新生的瑕疵。今天,她從底面的銅鏡里又驚駭地發現,一只半弧形的肉團正在她下巴底部隱秘地崛起,像一個危險的水雷;在正面的鏡子里,褐色雀斑已由月前的七粒增至九粒,像幽靈的眼睛在窺視著她。起初,她有點委屈,覺得這太殘酷。但當孩子的一聲夢囈,讓她從左邊鏡子里看見那只肉鼓鼓、也是香噴噴的小手時(它剛從被窩兒里甩出來,鮮嫩的樣子像一枝剛破土而出的筍),她波動的心仿佛被這只小手撫平了。她想,這只小手不是從被窩兒里鉆出來的,也不是從泥土里,而是從我肚子里,從我身體里鉆出來的,是我生命結出的果實。世上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勝利往往連接著一系列的失敗、死亡。
但在陸小依心中,這個小小的勝利絕不是那么渺小,她甚至從這個小小的勝利中預見到了自己最后的勝利。她相信,以后她所要的一切,孩子都將通過某種神秘的魔術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地給予。兒子就像是她長在身體外的一只手,一只變形的因而更有力的手,扯住了她所需求的一切。這是一個秘密的念頭,一個女人的私密,陸小依將它藏在心中的心中,常常連自己也看不見——因為藏得太深了!但是有此念擱置于心中,猶如在銀行擱著一筆秘密款子,用不用是一回事,有沒有又是一回事。有就是一種存在,一種力量,一種希望。
因為時間充裕,化妝被一再精細、強化,發型,面頰,眉毛,眼線,唇線,頸脖子,腮幫子,陸小依一一關照,認真細致,耐心又開心。這時候,她才體會到有這么一個聰明的梳妝臺真是難能可貴,幾面鏡子各有分工,又互相呼應,為她立體地、全方位地指明瑕疵,而各式艷具就是她抹殺瑕疵的最好武器,她謹慎又勇敢地操作著,不慌不忙,用心用功,就像在耕耘一方養生寶地。
梳妝完畢,兒子尚未醒來。但不行了,要弄醒他了。
兒子才兩歲半,小名叫安安,突然被從被窩兒里拽出來,東倒西歪的,真像一團沒有氣力的肉,散發出暖暖的肉香。香氣襲人啊,陸小依醉了似的撲在這團肉上廝磨,一邊模擬兒子的嗓音叨叨:
“哦,親親,媽媽親親……”
“肉團”仿佛被母親的熱氣焐活了,彈放出咯咯的笑聲,掙扎著要爬開去。陸小依一把抓住,正言道:“快起來了,我們要去看大舅舅。”
一句話立馬將兒子豎起來,惺忪的睡眼發出驚疑的光芒,“媽媽,我們什么時候去看大舅舅?”
“就現在,起床就去。”
這句話使兒子起床的時間比往常足足減去一半。一個兩歲的孩子,你別以為他真是一團肉,他也有心靈,期望,恩愛,情仇。昨天,大舅舅送他一套玩具槍,他回贈給大舅舅的是一捧熱騰騰的愛:他惦記著大舅舅!
那套玩具手槍是絕對的美國貨,共六支,大的跟安安人一般高,小的只有他半片巴掌大,就像一枚桃形鑰匙,卻依然跟真的一樣,可以呼呼射擊,子彈是蠶豆樣的金色塑料。昨晚,他把六支手槍玩了又玩,睡時手里還捏著那支桃形小手槍。剛才洗臉時,他慣常地伸出小手讓母親擦洗,才發現小手槍不翼而飛。
“媽媽,我的槍!”
兒子驚叫著,直奔臥室。
陸小依尾身跟去,袖手旁觀,只見兒子床上床下地翻找,一邊驚恐地呼叫:“媽媽,我的槍,媽媽,我的槍!”
陸小依再也看不下去,伸手指向床頭柜,做出猛然發現的驚喜狀:“安安,那是什么?”
那就是安安找尋的桃形手槍。
怕安安在夢中把小桃形手槍吞入肚中,所以才把它挖出來,放在床頭柜上。這是一個母親的細心,也是一個母親的幸福。
當郵電大樓傳來八點鐘的鐘聲時,陸小依抱著安安——就像抱著一個優美的念頭,從樓道里出來。當時我剛買了早點回來,遠遠看見她們從臺階上下來,陽光像水一樣一浪浪地打在她們身上,就像打在一朵并蒂蓮花上。
我們慣常地打了招呼。我很容易地從她臉上讀到一種節日氣氛,于是我說:“我從你臉上看到加林已經回來了。”
“不是的,是我哥回來了。”加林是她丈夫。
“是你在美國的大哥嗎?”
“對,你怎么知道?”淺淺一笑。
這笑容使我感到她在撒謊——笑容像沙子一樣企圖包裹謊言。但我又完全相信她說的是事實。說真的,我一向認為陸小依是個不會笑的人。我是說,她的笑常常丟失本意生出某種隱晦的意味,好像笑的根本作用就是無奈和開脫。
分手后,我沒有回顧她的背影,但回憶了她的話。我知道,她有個哥哥在美國,在我的印象里,他曾經繼承了父親的職業,是個作家——也許該說是不錯的作家,早期有一篇小說曾經轟動文壇,既博得了讀者的喜歡,也得到了官方的榮譽和獎金。問題不在這。問題在于——我想,一個作家離開自己的祖國和寫作語言,去美國干什么?我覺得前輩陸家的人都有一種讓人深究的神秘魅力。
前輩陸某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今天他們都簇擁在娘家。由于大哥的榮歸故里,他們擁有了自己的節日。這個節日已經醞釀三年了——大哥已經三年沒回國了。三年里,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陸小依也從一個少婦變成了一個母親。巨大的變化讓有些人的生活更窘迫困難了,有人為物質世界的貧富而受苦,有人為家庭情感的變遷而落難,陸小依覺得,她的生活是變得更幸福溫潤了,一大一小,兩個男人,像天上下來的兩個天使,各自牽住她一只手,讓她拔地而起,品到了一種飛翔的感覺。
我決定將陸小依在娘家和兄弟姐妹歡聚的過程盡量簡化。點到為止。一筆帶過。我對自己說,讓那些誰都可以想象的歡樂啰嗦的場面,那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式的洋洋喜氣從我指縫間流走吧,我不想了解美國風情,也不想涉獵家庭私情。我感興趣的是陸小依,是她的細膩、敏感、膽怯、脆弱的心靈,是生活之于她的一點一滴的意義。
時間過得很快——陸家的人今天都有這感覺,陸小依尤其如此,因為她十點鐘要去火車站取票。十點鐘,約好的。到了九點半,陸小依覺得再也不能留了,就站起來說:
“我要走了。”
“去干什么?”大姐用一種帶點兒兇相的口吻責問,“今天你還要離開我們?”
其他人跟著也擺出一種相同的架勢,紛紛響應大姐。
陸小依理直氣壯地:“干什么?取票唄,大哥不是要去見老丈人嘛。”
眾人這才恍然大悟,紛紛點頭稱是,唯獨小妹,尖銳地叫道:“但愿取不到!”
陸小依說:“保證取不到。”一邊從沙發上拿起外衣(一件藍呢子短大衣),穿上,又從母親手中接過圍巾(一條紫紅色的長圍巾),掛在脖子上,人因此也顯得更加風度翩翩,有種講究的城市氣,好像在墻上貼了道瓷磚的彩條似的——在鄉間人看來,這叫“砸錢”。
剛要走,狗子(大哥兒子的中國小名)沖上來問姑姑去哪里,他父親替陸小依答:“去火車站,給你去拿回外婆家的車票。”
狗子頭一伸:“我也要去。”
馬上,天然(大姐之子)也沖上來:“我也要去!”
沒人同意他們的要求,幾乎有五個聲道同時阻止道:“你們去干個么,外面風那么大。”
但他們置之不理,率先破門而出,一陣劇烈的夸張的咚咚咚咚的下樓聲便是他們的回答。
二哥想追出去把他們揪回來,卻被陸小依攔住了:“沒事,讓他們去吧,反正馬上就回來。”說著,抱起安安欲走。
二嫂說:“那安安就別去了,抱去抱來很累的。”她想把安安抱過來,安安做出的反應就跟他兩個哥哥一樣,恨不得從四只手里掙脫出來,插翅而飛。他的心已被兩個哥哥提出去,身體怎么肯留在屋內?
于是陸小依又說:“沒事,沒事,安安可以走的。”
大哥抽出一張大鈔,遞給陸小依:“努,打的去。”
陸小依回一句:“干嗎?”臉都紅了。
老頭子發表評論,嗡聲嗡氣地:“打什么的,走幾步路,乘17路,直達火車站。”
“就是嘛。”陸小依轉身離去。
帶著三個孩子上街是件麻煩的事,但由于心情好,陸小依一點也不覺得麻煩,她只是鄭重告誡狗子和天然,路上要聽話,不準亂竄。兩人都答應了,而且一開始就表現出很懂事的樣子,要幫她抱安安。他們一個十歲,一個九歲,在安安面前足以做個大哥哥。但安安并不要他們抱,他更喜歡自個兒走,邁著沒有多少底氣的腳步,走得輕飄又急促,感覺是一只腳在跳。
天氣很好,沒有風,一浪一浪的陽光使臘月的冷空氣像被用力摩擦了似的,變得不那么寒冷,甚至還有點春日的暖氣。要不是有事,陸小依倒是很樂意跟他們這樣散散步,走去火車站。她向來喜歡跟兒子一塊兒散步,當她和兒子手牽著手漫步在街頭時,她感到輕快,踏實,好像不是她牽著兒子,而是兒子牽著她。她覺得牽著安安像牽著一個優美的念頭,一個美好的未來,一種和諧、親愛的現實,是誰都要羨慕的。如果哪天加林在家(音樂家經常奔波在外),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這種優美,這種和諧和親愛,就是完美無缺的啦,她愿意就這樣度過一生。她經常暗自思忖:這就是我要的生活和幸福。她其實是個很現實也很容易滿足的女人。
父親的建議就像他的作品,已經過時,加上三個小孩,陸小依出門之初就不準備采納父親的建議,雖然公共汽車兩次在她身邊開過,她還是堅定地張望著出租車。出租車平時多得很,但眼下是年關時節,需要耐心等待。等待的時間比想象的要長,他們邊走邊攔,等走過一條街,還是沒有攔到車。好不容易攔到一輛車,司機是個臨時上陣的(真正的師傅回老家過年了),線路不熟悉,膽子又小,見了紅綠燈和警察就減速,一點也沒有出租車威風凜凜的派頭。這樣,當然不能準時去見人,下車時已經是10點07分,加上還要穿過一個偌大的火車站廣場,陸小依有點心急,一下車就抱起安安,催促兩個小家伙快走。
廣場上,人和物多得跟潮水沖積起來似的,遠遠看去,亂糟糟一片,無立足之地。陸小依懷抱安安,有點厭惡地走進去,東一腳,西一腳,時不時請人避讓,求人原諒,走得心急火燎。這是今天以來煩惱第一次侵擾她,她開始后悔沒把安安留在家里,而狗子和天然老是落后(他們老是被某些稀奇吸引著停下來)又讓她生氣,她不得不經常回頭召喚、訓斥。有一次,回頭過急,她失去平衡,一腳踩在人家腳上,那人劈頭蓋臉地罵她:“瞎眼了!”
由于氣惱,她沒有道歉,甚至不乏兇悍地剜了他一眼。
到車站門口,陸小依來不及地將安安往地上一放,深深地出了口惡氣,頓覺輕松百倍。
現在,她要從這扇窄窄的鐵門進去,這首先要博得守門人的信任,相信你不是出于逃票或接客。陸小依以為要做到這點很難,準備了一大堆解釋和討好的話——都是慣常的花言巧語。她不認為這樣就夠了,所以還作了其他準備,比如托人將朋友喊出來,或給朋友打個電話。可結果卻容易得使她驚訝,守門師傅一聽她找誰、二問她是誰后,便客客氣氣地放她進去,好像這兩個名字把他嚇倒了。
這一定是朋友跟師傅打過招呼的緣故,陸小依想。朋友的這種周到的歡迎態度讓她有點感動,同時她相信,車票一定是沒問題了。她的心情一下又回到了幾分鐘前,朗朗的,暖暖的,像頭頂的天空。
她沒有帶安安他們進去,因為她覺得帶他們進去容易被邀請而坐下來。她不想坐下來(她想快些回家,家里可熱鬧呢),把他們留落在外就是盡快出來的最好理由。她把安安交給狗子和天然,叮囑道:
“我進去拿票,一會兒就出來,你們看著安安,不要亂跑。”
兩個做哥哥的都爽快又堅決地答應了,各人扶著安安一只肩膀,一副忠誠司職的樣子。
進去前,陸小依專門叫安安給她看看那把桃形小手槍,她擔心兒子丟了。安安張開小手掌,手槍臥于掌心,在陽光下反射出潮濕的光芒,似乎動都沒動過。她開心地幫安安捏好拳頭,“別丟了,媽媽馬上回來。”
就別了。
事后陸小依再三表白,她離開的時間頂多只有五分鐘。五分鐘呢,確實是夠少了,但結果卻比一輩子還長。漫長的長。無休止的長。比天還長。比地還久……
出來時,陸小依首先注意到的是一個人群簇擁、混亂嘈雜的場面,場面的中心是一位席地而坐、號啕大哭的婦女,她的哭聲極其粗野、強烈,夾雜著呼天搶地的哀鳴,一下子驚動了她寧靜而歡喜的心——就像是被誰猝然緊捏了一把。驚動中,她目光格外急切地朝安安他們原來站的地方撲去,看到了狗子和天然:他們位置有點變化,但變化不大,似乎是朝前挪動了幾步。問題不在這里,問題是他倆中間空開著,倆人剛才搭在安安肩頭的手,居然無所事事地空閑著!
陸小依吃驚地跑過去,擋住了他們好奇的目光:“安安呢?”
倆人偏了偏頭,調整著視角,但不是為尋視安安,而是想繼續看到那悲慟的婦女。
陸小依放大喉嚨:“問你們呢,安安呢?”
狗子伸手向后一指:“在撒尿。”眼睛還是直直地望著前面。
陸小依向手指處看去,仍不見安安,又問:“在哪里?”伸手推了他們一把。
兩個家伙這才調轉頭來,往安安撒尿的墻角望去,看到白色的墻面上有一座山形的濕印子,那是安安撒下的尿水。但安安卻不知去向,好像已化作尿水,滲入了墻內。開始,陸小依還有耐心相信,安安不會走遠的,他就在旁邊,在這撥圍觀者中間,你左右看看吧。
她左右看了看:沒有!
換個方位又看:還是沒有!
喊一聲吧。
她大聲喊了四聲:還是沒有!
喊第四聲時,她已經感到兩眼發黑,雙腿發軟,喉嚨被卡住了似的吸不入氣……
安安不見了!
這不是真的,但又的的確確是真的。事情的開始就像奧古斯的悲劇,是一泡尿,安安要撒尿,兩位哥哥就帶他到墻角邊,狗子幫他扒下褲子——一層又一層。就在這時,一串尖厲的哭叫聲突然從他們背后幾米外拔地而起,狗子和天然一齊回頭看去,看到一位足以成為他們婆婆的婦女就像孩子撒潑賴似的坐在地上又哭又叫,周圍人紛紛聚攏,就像漩渦把泡沫和落葉都吸過去一樣。
天然率先擅自離職,加入圍觀者行列,然后是狗子。事后狗子開脫說,他本來不想過去的,只是看天然跑去了,怕他失散,就過去喊他。但這顯然是開脫而已,因為他過去后并沒促使天然退出圍觀,而是問天然:
“婆婆干嗎要哭?”
“一個‘三只手偷了她鈔票。”天然說。
“‘三只手是什么意思?”他離開祖國時太小了。
“就是小偷唄。”
小偷把兄弟倆的心也偷走了,他們好奇地注視著慟哭的婆婆,把安安拋出了心靈,拋在了人山人海的廣場上。我們可以想象,當陸小依明白這一切后,會怎么樣?她一定會繼續大聲地喊:
安安——!
安安——!!
安安——!!!
即使過去了那么久,即使是對著電腦模擬著喊一喊,我還是很容易就可以感觸到陸小依當時那種過分驚慌和無助的感覺,她看著偌大的廣場和嘈雜混亂的人群,心里頭一定害怕極了。恐怖干凈利落地抽走了她有生以來所有的高興和全部力量,她開始變成另外一個人:焦灼,驚惶,無助,悔恨,恐懼,魂飛,魄散……凡此種種,如煙似霧,來自四面八方,包抄著她,充塞著她,把她渾身上下每一個汗毛孔都塞得滿滿當當的。她身體僵了,硬了,心里空了,木了,仿佛恐懼將她釘在地上,變成了廢物,動彈不了了。她真想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一場,可放開喉嚨,卻又變成了一聲呼喊:
安安——!
聲嘶力竭,夾雜著悲痛、驚恐、祈求和可憐,從喉嚨里發出,又刺入耳中,陸小依感到像被抽了一鞭,渾身一個踉蹌,差點晃倒在地。也就順著這個踉蹌,她甩開腳步,撲進了人海中。
安安——!
安安——!!
呼號聲一聲比一聲尖厲、脆弱、哀婉,身體的各個部位在呼號和前進中就像枯萎的花瓣一樣,一片一片剝落。沒有走出50米,陸小依就感到渾身只剩下兩片鐵硬的腳板,在水泥地面上緊張地拍打著。
在廣場東南的拐角處,陸小依第一次發現了安安,在一個三十多歲男人的懷抱里,男人像蛇一樣在人群中躲閃著游竄,越竄越快,肩膀上時不時露出安安戴的絨線圓帽。陸小依瘋了似的追上去,像個潑婦一般一把抓住了男人的肩膀。男人轉過身來,她發現男人懷中的孩子是個女孩,只是戴的絨線圓帽和安安的相似而已。
陸小依第一次擦了一把汗,那汗冷颼颼的,仿佛是從冰塊上漲出來的甘露。她變成冰了嗎?不,不,是火!是汽油!此時的她就像一桶汽油,所到之處,人海驚動。安安——!安安——!!呼號聲一下接一下地拍打著廣場,人群一片接一片地攪動起來。她不但無法撲滅火勢,反而使火勢更旺了。人們競相圍觀她,問長問短,說三道四。
“小依,你怎么啦?”是小依老單位的一個同事。這樣的時候,她感激這樣的相逢。
“我把安安丟了。”說著,竟站不住地抓住老同事的手,嗚嗚地哭了起來。
“別哭,快去找。”朋友問清事情,二話不說,把提的背的三只包全往妻子、孩子跟前一撂,“你們在這里等我。”
“火車馬上就要開了。”妻子說。
“你放屁!”同事瞪圓了眼,似乎要破口大罵,卻一言不發,調頭拉著小依,“快走,我們快去找。”
倆人分頭喊開了。
安——安——!
安——安——!!
兩個人尋找,希望是雙倍的,但絕望也是雙倍的。朋友的出現和慷慨相助,曾使陸小依感到更接近安安了。但沒過五分鐘,當倆人在出站口空手相遇時,陸小依從朋友身上感到的卻是更遠離安安了。安安才兩歲半,如果他僅僅是走散,這么短時間不會走太遠的,如果能喊回來該早喊回來了。什么情況會使安安走得很遠,喊不回來了?在某個居心叵測的大人懷里!這個擔心陸小依開始就有了,這一圈呼號下來似乎是得到了證實。陸小依站不住了,靠著出口的鐵柵欄慢慢蹲下來,她覺得自己身體就像熱鍋上的一個餅,正在熱烈地一點點裂開來,四肢的感覺越來越麻木,好像它們率先從身體分裂了出去。
兩個小時后,我也加入了尋找安安的行列。那時,陸小依大概連頭顱也脫離了身體,我看見她時她一動不動地坐在地上,見了任何人都無動于衷,只是默默地流淚。沒有哭泣,只是流淚。
我想,那眼淚一定是燙的。
是的,日歷翻了又翻,覓尋的手段和人員及范圍增加了又增加,但就是找不到一絲安安的音訊。安安這孩子實在是太奇怪了,竟然以一泡尿的形式和母親作別,你想想這對陸小依來說有多傷心。據說,傷心的淚水是發燙的。
日歷又翻了又翻,轉眼又一個春節翻過去了,但陸小依卻再也無法翻過“那一天”。那一天,她丟掉了安安……我還是要說,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這一天竟像一道萬重山,把她的過去和以后徹底阻斷、隔開了。似乎誰也沒想到,這個偶然事件會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一個“完好無損的人”損得不成樣子。首先是大病一場,痊愈后人瘦了一圈,黑了一層,再不像以前那么豐滿、典雅了。這是可以想象的,我愛人因為丟了一輛自行車還蔫蔫的病了幾天呢。難以想象的,冬天還沒有過去,音樂家居然離開了她,走了!如果說丟失安安是個意外,那么他們離婚讓人感到意外的程度一點也不亞于安安的偶然走失。以前,我們單位的人都說,他們相愛篤深,他們用實際行動向我們宣告:篤深其實并不深,也許只有安安的身高那么深——不足一米,貌似很深而已。
他們離婚后不久,有一天,我看見陸小依把一個收荒匠喊回了家,收荒匠走的時候三輪車上裝滿了東西,其中有那只無比聰明的梳妝臺。這也是我們沒想到的,難道過去就這么不值錢嗎,只值一個收荒匠的行情?收荒匠哼著小曲,樂顛顛地走了,我想象陸小依一定躲在屋子里哭。
“我沒有哭……”有一天陸小依坦率地告訴我,她沒有為音樂家的走流過一滴眼淚。“很多事情是必然的,”她像一個智者一樣,從容、淡然地對我說,“既然是必然的,又有什么好哭的。”
我問她什么事情是必然的。她淡淡一笑,語義不詳地說:“這個時代速度太快了,誰都在往前跑,把過去都丟了。”
我注意到,她作笑時,臉上的雀斑很燦爛。一目了然。昭然若揭。我老婆也是一個滿臉雀斑的人,我知道像歐萊亞什么的,可以將這些雀斑抹殺掉,但她似乎更喜歡素面朝天。這樣,只要在一米之內,你總是可以看到黃褐色的粒狀雀斑像沙子一樣沿著她精致的鼻梁,向兩邊面頰洇開、散落。雀斑是個怪東西,一個女人臉上若干凈得沒有一粒雀斑,反而有點假——讓人懷疑是粉過的,美麗只是面具。一般有個五六粒,而且長在額頭上,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多了,而且是散落在鼻梁四周,那就慘了。如是對這些雀斑都不在乎,不裝飾,那說明這個女人內部就有問題了:不是自暴自棄,就是太自以為是。一個受寵、溫軟的女人是絕不會讓你看到這些雀斑的。什么叫不修邊幅?男人穿著豁口的皮鞋,女人面頰上亮著兩堂雀斑。陸小依現在就是這樣,鼻梁像只沙漏,把兩堂面頰弄得臟乎乎的,而且不以為恥。無所謂。換言之,我們不妨說她現在是一個不修邊幅的女人。
現在,說真的我在回避看到陸小依,因為每次看到她不修邊幅的樣子,總會讓我對生活勾起一種盲目的恐懼。我總覺得,在她的過去和現在之間落差太大了,她從一個幾乎人人羨慕的人,變成了一個幾乎要我可憐的人,為什么?就因為這安安離開了她。安安是她命運中的一只開關,開關開著,她一切都好好的,開關關了,她一切都完了。而哪個人身上沒這樣的開關?這樣想著,你就不會覺得生活是無憂無慮的。
有一天,陸小依在電梯里突然又像個智者一樣地對我說:“現在的生活就像坐電梯,上上下下你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覺得她說得蠻有道理的。
【作者簡介】麥家,男,1964年生,浙江富陽人。1981年入伍,畢業于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無線電系和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現轉業在成都電視臺工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說集《人生百慕大》,長篇紀實文學《血域雪情》等,部分作品曾在軍內外獲獎。本刊曾選發其中篇小說《陳華南筆記本》、《黑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