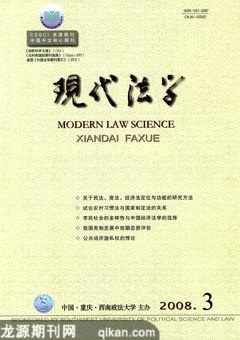試論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
摘 要:處理好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積極意義。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之間,既有法的目的等方面的一致性,也在法的規范、法的實施、法的價值等方面存在矛盾和沖突,習慣法對國家制定法在調整范圍、功能方面還有一定的補充作用。
關鍵詞:農村;習慣法;國家制定法
中圖分類號:DF092
文獻標識碼:Aオ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加強農村法制建設,深入開展農村普法教育,增強農民的法制觀念,提高農民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自覺性,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背景下,新農村建設中需要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增強法律意識,處理好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使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良性互動,真正發揮國家制定法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的引導和保障作用。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區域非常廣闊,農村人口眾多,農村習慣法在農村社區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國農村地區,存在內容豐富、功能全面的習慣法。[注:中國習慣法包括宗族習慣法、村落習慣法、行會習慣法、行業習慣法、秘密社會習慣法、宗教寺院習慣法、少數民族習慣法等(參見:高其才:中國的習慣法初探[J].政治與法律,1993(2):47.)。]我國歷史上廣大農村地區就依靠習慣法進行自治,形成了涉及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社區秩序的規范體系。我國農村的習慣法內容豐富,從社會權威角度看,有宗族習慣法、村落習慣法等;從規范對象來看,有農業習慣法、林業習慣法、漁業習慣法、畜牧業習慣法、狩獵習慣法等;從規范內容看,有民事習慣法、刑事習慣法、社會生活習慣法、程序習慣法等;從民族角度看,有漢族地區的農村習慣法、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習慣法等。我國農村的習慣法對于維持鄉村秩序、滿足個人需要、培養社會角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我國農村習慣法與國家法的關系非常復雜。總體而言,在中國的農村地區,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之間,既有其一致性,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矛盾和沖突,并且習慣法對國家制定法還有一定的補充作用。我們應當高度重視、客觀認識、區別對待、具體處理。
一、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一致
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在法的目的和功能、法的內容、解紛方式等方面具有一些內在的共同性。這主要表現在農村習慣法所反對、不容的某些行為也為國家制定法所禁止,農村習慣法所提倡、鼓勵、贊成的某些行為也為國家制定法所確認和保護。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具有共源、同生、并行的關系,客觀上互相支撐、相互影響。
在法的目的和功能方面,農村習慣法與國家法都是為了調整農村社會的社會關系,規范農村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解決農村社會的紛爭,維持農村社會的秩序。同為社會規范,同為人類法文化組成部分的農村習慣法和國家法,都是在吸收、繼承人類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目的都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促進社會進步和發展。特別在對于人的生存和人的尊嚴的關注和保護方面,兩者無疑有著某種共同和一致之處。
農村習慣法特別是成文的鄉規民約、村規民約,往往明確規定是根據國家法的有關規定和精神擬定的。習慣法一般要求農村社區成員遵紀守法,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如1983年的廣西龍勝泗水公社周家大隊的村規民約就規定:“全大隊公民必須嚴格執行黨和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做執法的模范。”[1]
在法的內容方面,農村習慣法與國家法在許多領域更有一致和共同的方面。如山東有村規民約規定:“凡戶口在我村的村民享有以下權利:憲法規定的權利;參加村務活動,提出建議和批評,監督干部工作的權利;選舉和被選舉權;享受各種公共事業利益的權利。”[2]可見農村習慣法注意與國家制定法的一致,維護國家法律的地位,保障國家法規定的公民權利。
農村習慣法大都嚴格禁止偷盜行為并給予各種處罰,習慣法保護村寨、家族以及家庭的財產所有權。如農村習慣法大多禁止偷盜,偷盜者根據偷盜物的不同除退出贓物外,并受按價賠償、加倍賠償、罰款、罰做公家工、開除村寨籍乃至處死的處罰。一九九九年通過的廣西金秀瑤族自治縣六拉村村規民約第一條就規定,“保護國家、集體、個人財產人人有責,發現偷竊財物應立即扭送村小組或村委會,見者不報,以參與偷竊論處”,并逐一進行了具體規定。 [注:六拉村村規民約系我于2004年4月在廣西金秀六拉村村委會搜集。]國家的《憲法》、《刑法》、《民法通則》、《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也保護集體、個人的財產所有權,禁止偷盜行為,違反者由國家司法、執法機關給予各種制裁。因此這兩者有著明顯的一致性。其他如禁止強奸、搶劫、殺人等,農村習慣法的基本精神與國家制定法也相一致。
各地農村有關保護農業生產、水利設施、生態環境的習慣法是相當豐富的,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長安營鄉通過鄉規民約保護10多株東晉時期人工營造的古杉樹群。在廣東恩平市,保護古樹名木的意識深入民心。有的農村地區把“保護古樹名木”寫進了鄉規民約,不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壞古樹名木,更不許把古樹名木賣給外地商人[3]。這些內容與國家制定法的規范、精神是不矛盾的,相協調的。
農村習慣法中有關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與國家憲法、婚姻法的規定也是一致的。尊老愛幼的習慣法亦與國家的憲法、刑法、婚姻家庭法的有關規定吻合。誠實守信的習慣法規范與現行的國家法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解紛方式上,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都重視調解的作用。農村地區的糾紛多發生在家庭成員、鄰居、村人之間,多為“家長里短”式的細故之事,運用調解方式既解決了問題,又節約成本,亦不傷和氣。如陜西省西安市雁塔2005年5月起在全區120個村推行由村兩委會干部、駐村指導員、人民調解員等10多人組成的鄉規民約評理會并邀請處事公道、正派、懂政策、有能力的長老、教師、回鄉退休干部等參與評理,對村民與村民、村民與村組、村組與村組之間的一些屬于鄉規民約、村規民約范疇及法律未明確規定的糾紛、矛盾、問題進行評理,并得出結論性的解決辦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4]。在我國農村地區,對于許多糾紛的處理缺乏明確的國家法律依據的案件,大多依照村民能夠普遍接受的鄉規民約等習慣法進行勸解,促使糾紛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
需要指出的是,國家的一些法律、法規、規章對鄉規民約等農村習慣法進行了確認。我國《憲法》、《刑法》、《民法通則》、《民族區域自治法》、《婚姻法》、《森林法》、《繼承法》、《收養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民事訴訟法》等法律都明文規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權根據當地民族的特點結合法律原則制定變通或補充規定。[注:參見《憲法》第115條,116條;《刑法》第90條;《民法通則》第151條;《民族區域自治法》第19條,43條,44條;《婚姻法》第36條;《森林法》第41條;《繼承法》第35條;《收養法》第31條;《婦女權益保障法》第53條;《民事訴訟法》第17條;等。]《合同法》規定了交易習慣的效力。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全民義務植樹的獎懲暫行辦法》就規定:“各地、市、縣綠化委員會要發動群眾,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由群眾自己制訂愛林護樹的鄉規民約,互相監督,違者按鄉規民約處罰。”《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護條例(2004修正)》規定,“古民居較多的村可依法訂立保護古民居的鄉規民約。”許多規范性文件也認可農村習慣法的一定效力,如四川省《梁平縣人民政府關于加強青蒿資源保護的通告》(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1條規定:“嚴禁踐踏毀損。嚴禁人、畜進入青蒿種植地踐踏青蒿,違者按鄉規民約處理,并賠償業主的損失。情節嚴重的,由公安部門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有關規定處理。”雖然這些規定都是比較粗糙的,實踐中也難以操作,但表明了國家制定法對農村習慣法的支持、承認。
二、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沖突
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曾提到一個國家制定法與農村習慣法沖突的例子:某地鄉間有某男子同某個有夫之婦通奸,被女人的丈夫抓住,打了一頓;奸夫居然到法院告狀,要求獲得國家法律的保護。費先生用這樣一個例子說明了當時國家法律與社會生活習俗的脫節[5]。在當代中國農村,這樣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沖突的情形依然存在。
這種沖突表現為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規定不一致甚至對立上。它既有民事方面規范的沖突和矛盾,也有刑事方面內容的差異,訴訟程序的規定兩者也是各有不同的。由于農村習慣法賴以存在的基礎、價值、實施等與國家制定法有異,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社會規范,其沖突和不一致是顯而易見、客觀存在的。
(一)在法的規范方面,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沖突涉及公共秩序、民事行為、違法犯罪等領域
1.公共秩序 農村村民在鄉村活動的空間,是一個具有自然性質的熟人社會,他們首先隸屬于特定的家族和宗族,在既定的血緣和地緣關系中生活。農村習慣法大多采團體主義,以屬人主義為原則,農村社會公共秩序的維護有著嚴格的內外之別,不同的主體、內部人與外面人之間在權利、義務方面存在明顯差異,這與以屬地主義原則為基礎的國家制定法存在矛盾。幾乎所有的鄉規民約都嚴格規定村內和村外成員的區別,外來人口即使是短期的,也需要辦理登記。農村習慣法對這種區別的重視,在于不同人享受的待遇(權利)或義務有異,村民需要進入某一個具體的管理單位,以便明確利益分享、受到保護、接受管理的范圍[6]。云南某市村民小組制訂的“公約”中明確規定:上門的姑爺和外來的媳婦如果有吸毒、販毒、偷盜、搶劫等行為,村里有權注銷其戶口,收回耕地,并將其趕回原籍。其配偶,要么離婚留下,要么走人[7]。這樣的鄉規民約、村規民約明顯違反了國家法律,侵犯了村民的法律權利。
在社會秩序維護方面,農村習慣法的許多規定與國家制定法出現沖突。如2005年 3月27日晚,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璜尖鄉嶺南村召開兩委黨員、各村民組長、村民代表會議,共同制定通過了有關森林保護的村規民約,其中第2條明確規定:“恢復歷史上殺豬封山制,按居住本村戶口每戶發一斤豬肉為限,以示提高廣大村民對護林的重視和警悟。”同時還規定一律禁止砍運杉、松樹進村,違者按偷盜給予每人每戶伍佰元罰款[8]。嶺南村村規民約規定違反者給每戶發一斤豬肉、違反者每人每戶伍佰元罰款明顯的與國家制定法相抵觸。
2.民事行為 在民事方面,農村習慣法有關財產所有權、債權債務、婚姻家庭繼承等方面的規范,與國家制定法的原則、規則有許多不一致之處。
農村習慣法基本以家庭、家族乃至村寨為財產所有權的主體,個人很少能成為財產所有權的主體而獨立擁有財產、自由支配財產。而國家現行的《憲法》、《民法通則》、《繼承法》等規定財產所有權的主體既有國家、集體,更主要的則是個人,國家現行法律保障個人的主體地位和個人權利。值得注意的是,農村習慣法對出嫁女及其子女土地承包權、集體經濟分配權、宅基地分配權等財產權益往往進行剝奪和侵害,成為農村習慣法與國家法沖突的突出方面。[注:
如2006年7月26日,重慶市綦江縣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綦江縣趕水鎮馬龍村第二村民小組在判決生效后五日內向該組村民翁某父女兩人、余某母子三人各支付2004、2005年分紅補償款2233.84元、3350.76元。法院經庭審查明,該組在2004年12月10日討論制定了“村規民約”,規定凡當年死去的人可以分紅,次年農稅由集體負責,但其不能再享受分紅;嫁出去的姑娘,2004年按承包地份額分紅,次年的社會負擔由集體負責不再分紅;本組學生升學后國家分配工作的,不能再享受分紅,在校或從事打工性質的工作享受本組分紅。法院審理認為,村、社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依法受法律保護。綦江縣趕水鎮馬龍村第二村民小組在煤礦擁有的股權系該集體經濟組織的集體資產,其股份的分紅同樣屬于集體收入,為該組全體成員所有。該組根據集體組織自治作出的分紅決定,其成員都應當享有。原告翁某父女兩人、余某母子三人能夠證明其戶口在分紅期間一直在被告所在的馬龍二組,且原告的戶口能夠保留在該組系基于婚姻關系,雖現原告常住地非被告所在組,并不能因此否認原告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原告作為集體組織成員享有與當地村民同等的權利。《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0條規定,村民會議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并報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備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討論決定的事項不得與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相抵觸,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村民小組制定的村規民約,同樣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內容,不能違反法律和政策禁止性規定。該組制定的村規民約中以原告必須居住在本村民小組,否則難以履行相應義務為由,剝奪部分成員分紅資格的行為,損害了作為村民小組成員的合法利益(參見:郝紹彬.綦江對不合法的“村規民約”說不——一審判決集體組織成員的合法權益受保護[N].人民法院報,2006-07-30.)。]農村習慣法與《婦女權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不一致,違反男女平等原則、侵害婦女合法權益的內容較為明顯。
在債權債務方面,對欠債不還的,不少農村的習慣法規定可以任意拉債務人牲畜、財物乃至以土地、房屋清償。國家制定法對欠債不還的處理卻絕對不涉及到人身權利方面,財產問題純以財產手段解決。同時,國家法規定債務的清償以本人的財產為限,而農村習慣法卻往往規定“父債子還”、“債務不死”,強調責任的無限性。
在婚姻家庭繼承方面,農村習慣法一般都規定訂婚的效力;農村習慣法大多剝奪婦女的繼承權,這與國家法律在繼承權男女平等的規定也是相矛盾的;習慣法還維護家長權、尊親屬權,賦以家長廣泛的權利,這在國家現行制定法上是找不到類似內容的。如有一起返還彩禮糾紛。
3.違法犯罪 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在刑事方面的沖突更為突出,農村習慣法視為正當的行為,國家制定法卻規定其有社會危害性而為違法犯罪行為。這些沖突包括人身方面的,也包括財產方面的,還涉及社會管理方面。
在人身方面,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沖突主要表現在拘禁、強奸、通奸等行為。如1999年元月,安徽鳳陽縣一對農村男女青年李某、吉某按照當地習慣法(尚未領取結婚證)舉行了婚禮,誰料一周之后新娘吉某就出逃并控告新郎李某強奸了她。李某以吉某借婚姻騙取彩禮為由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吉某返還彩禮,當地法院判決解除雙方的同居關系并責令吉某返還了部分彩禮;后來,在吉某不懈的控告下,當地公安機關以李某涉嫌強奸正式立案并將其逮捕,2000年6月6日當地法院認定李某犯強奸罪并判處有期徒刑3年。這一新娘控告新郎犯強奸罪的事件在當地引起了較大的反響,不少村民包括吉某的親戚對吉某的行為感到難以理解,并對法院的判決感到困惑,因為在鄉親們看來這樁婚事是經明媒正娶的,按習慣法辦完喜事吉某就是李家的人了,強奸之說實屬荒唐。自稱有叛逆個性且在南京打工時見過世面,懂得“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吉某面對鄉親們的說三道四處境頗為尷尬。當地村民普遍認為喝喜酒這種農村習慣法儀式和明媒正娶這種民間風俗就是約定俗成的結婚形成要件,至于領不領結婚證并不重要,而《婚姻法》則將領取結婚證視為婚姻成立的法定形式要件。正是代表村民這種“地方性知識”的農村習慣法與代表主流法律意識形態的國家制定法的沖突,使得當地多數村民對李某的遭遇和法院的判決感到困惑[9]。
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習慣法規定的早婚、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搶婚制、“公房”制,可能觸犯國家制定法規定的強奸罪、奸淫幼女罪、重婚罪等。父母包辦婚姻、姑舅表優先婚權這些習慣法的規定則可能觸犯國家制定法的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非法拘禁罪。少數民族習慣法規定的家長權、男女不平等的內容也可能出現虐待家庭成員的行為而觸犯國家法。如拉祜族的鄧某自1984年起以找對象談戀愛為名,多次和未婚婦女發生兩性關系。1986年5月的一天,他去舅舅家作客,夜間無事,便閑逛到該村附近的公房,與青年男女談笑嬉戲。夜深,鄧某向一婦女提出同居要求,遭到拒絕后仍糾纏不休,后見其他人各自散去或在公房中睡覺,便采取暴力手段,將該婦女強奸,被國家司法機關判處10年有期徒刑[10]。
許多國家制定法不禁止、允許的行為,農村習慣法則視為違法犯罪。如廣西金秀六拉村的村規民約規定,“不許破壞他人家庭和睦。嚴禁調戲婦女,通奸者男女雙方各罰款伍拾元。”這一規定明顯與國家制定法相異。
值得注意的是,農村習慣法在人身傷害、剝奪生命方面有其自身的標準和規范。如2002年7月6日,湖南省會同縣堡子村村民因懷疑同縣東門街人張順成到本村偷油,將其抓獲后按照懲治小偷的習慣法做法將其綁到電線桿上,在全村居民的毒打下,張順成竟被活活的打死。案發后,主犯吳喜建等人被依法逮捕并被判刑,但他們一直認為自己是冤枉的,他們認為自己做了他們所應該做的,按照習慣法懲罰小偷是每個村民義不容辭的責任。而村民們也認為他們是村里的英雄,他們實際上是在為全村人受過,他們的行為是值得原諒的。[注:
參見:張慶國.習慣法與國家法的博弈——鄉村糾紛解決機制初析[EB/OL].[2006-10-8].http://www.modernlaw.com.cn/4/3/02-20/1280.ht.作者認為,習慣法與國家法在實施成本、實施效力、以及公平性、穩定性與易操作性方面存在不同。]這種行為嚴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觸犯了殺人罪而為國家制定法所嚴格禁止。
(二)在法的實施方面,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沖突和矛盾還表現在執行與處理審理程序、處罰方式方面的不同
農村習慣法的效力較為特殊,只能在有限地域范圍內適用,一般也無專門的執行及調解處理審理機構,其程序也遠沒有國家制定法所規定的復雜、嚴格。不少農村地區發生糾紛乃至刑事案件后,往往不向國家司法機構提起訴訟請求裁決,卻按習慣法規定解決。更有許多民眾在人民法院判決以后置判決書于不顧又按農村習慣法重新處理一次,損害了國家制定法的權威和尊嚴。
在實施主體方面,農村習慣法往往擴大農村社團的權限,規定于國家制定法無據的權力。如云南滄源勐董帕良村規民約規定,禁止包辦買賣婚姻、近親結婚,如出現,罰款30-50元;廢除婚約,情節嚴重的罰款50元,并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這一條文中混淆了法定的婚姻登記機關與村公所的職責,村公所越俎代庖,不可思議的是居然設置了追究刑事責任的條規[11]。
在處罰方式方面,農村習慣法以罰款、罰物、開除村寨籍、肉刑、處死等為基本形式,表現出損害名譽、給予人身傷痛的特點,這與國家制定法的文明處罰方式有一定距離。像貴州的一些農村地區對搶走耕牛、馬匹、豬、現金的行為,今天仍按習慣法進行“四個一百二處罰”,即要違法者交出120元錢和肉、酒、米各120斤,請村寨全體成員喝酒,賠禮道歉即可了結。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沖突較為直接和明顯。
同時,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在具體的責任承擔方面也有差別。如1990年間,四川茂縣黑虎鄉與汶川縣龍溪鄉發生了草場糾紛。龍溪鄉村民曾在黑虎地界放牧幾頭菜牛,“起先黑虎鄉村民打招呼讓其牽回,后來過了好幾天(龍溪鄉人)還不牽回去。”于是,“黑虎鄉三村的八個年輕人用火藥槍射殺了這幾頭牛。龍溪鄉人上告到縣里,公安局后來查到了是這八青年干的,沒收了火藥槍六支,并分別進行了7~15天不等的行政拘留。各家還罰了幾十元的款”。事后當地村民群眾意見較大。據調查,糾紛起因是老規矩(習慣法)“山分梁子水分涇”,龍溪鄉人放牧行為違反了“規矩”;其次村民們認為,該糾紛應該通過調解和協商解決處理,以避免增加矛盾;再次,對違法行為習慣法上是或打或罰,只取一種,但對這種行為(公安局的處理)又打(拘留)又罰(罰款)是不“合理”的。由此可知,民眾對該案的處理有意見不在于處理結果,而是處理程序上撇開了習慣法上當事人之間的調解協商處理糾紛的“必要”程序[12]。
在責任追究方面,農村習慣法比較強調集體責任、連帶責任,與國家制定法的責任自負原則差距較大。如廣西金秀六拉村村規民約規定:“一人犯法全家負責,各家長要嚴格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十六周歲以下的兒童)。凡因犯法的經濟賠償誤工補助等一切經濟費用犯者一律不得抵賴。”習慣法具有傳統的株連性、牽連性特點。而在法的執行方面,農村習慣法往往由農村社區的成員共同執行,表現出群體性。
(三)在法的精神、法的價值方面,農村習慣法以血緣、親緣、地緣為基礎,成為熟人社會的關系規則
在農村社會,奉行著“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的精神,村民們也奉行著“樹之藝,種之谷,桑之麻,萬事不求人”的基本生活原則,社會關系較為穩定。而當代中國對農村社會具有重要作用的國家法律主要是根據現代化發展的情況、考慮國際標準和全球化的要求而制定的,以人、財、物的流動以及勞動、資本和原材料在流動中結合的市場經濟為基礎。因此,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基礎存在差別。
具體而言,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在集體與個體、特殊與普遍、具體與抽象、權利與義務、控制與保障、秩序與自由等方面存在沖突。
集體與個體方面,鄉規民約等農村習慣法都比國家法律更多地介入農村民間的日常生活,它以協調鄉間公共秩序為己任,以團體為本位,堅持處事中集體利益優先、團體利益優先的原則,個體作為家庭、家族、村落中的一分子而存在。而國家法奉行個人本位,從維護個人的自由、平等、人權不受政府權力侵犯出發,法律必須以保護公民權利為核心,尊重和關懷人權。
特殊與普遍方面,農村習慣法基本奉行特殊主義,往往個別案件個別處理;法的內容和實施具有比較明顯的主觀色彩;習慣法表現出內外有別特點,只有其內部成員有資格分享利益,對外部成員具有排他性或采用另一類標準;農村習慣法規范一個相對獨立的鄉村生活共同體,超出這個邊界,它的作用就減弱或根本不為他人所承認。國家法律則不是為特別保護個別人的利益而制定,也不是為特別約束個別人的行為而設立,“法對于特殊性始終是漠不關心的”[13]。
具體與抽象方面,農村習慣法通過列舉具體的行為規范表達法的價值、法的精神,根據具體情況,因人而異地進行調整,習慣法的實施是面對面的、生動的、形象的,村民從熟悉里得來的認識是個別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則。國家法突出規范的普遍意義,力圖為所有人們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模式、標準、方向;國家法律具有概括性,法律規定的內容抽象,它的對象是一般的人,而不是特定的人;它是反復適用的而不是僅僅一次適用的。
權利與義務方面,法對人們行為的調整主要是通過權利和義務的設定和運行來實現的,權利表征利益,義務表征負擔。通過法律的規定,影響人們的動機和行為。農村習慣法更突出規定村民的義務和責任,而國家法更注重保障公民的權利,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非依正當的法律程序不受剝奪。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為權利保障。在法律權利與法律義務關系上,法律權利是主要的、本位的,權利是目的,義務是手段。法律、法治的出發點、基本精神、價值取向都是為了維護民眾的利益,保障民眾的權利。
控制與保障方面,農村習慣法比較強調社會控制,權益保障則放在次要位置,約束村民的行為,比較強調制裁、處罰,規范以命令性規范、禁止性規范為主體。對一切足以引起破壞鄉村秩序的要素、個性都被習慣法遏制著。而國家法注重利益保障和社會管理,既有義務性規范,更有授權性規范。
秩序與自由方面,農村習慣法重秩序,以維持農村社會秩序為核心,主要滿足個人和鄉村社會的穩定、安全的需要,維護社會生活各組成部分的某種一致性和不矛盾性,個人的行為自由有其特點,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在一個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自由。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從俗即是從心。” [13]國家制定法則與之不同,充分保障個人自由,這種自由既包括積極自由,也包括消極自由。[注:英國學者伯林在《兩種自由概念》一文中將自由分為兩種,一種他稱之為消極自由,另一種稱之為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指主體不受別人的干涉,是“免于……的自由”。積極自由是一種以做自己主人為要旨的自由,是“去做……的自由”(柏林.兩種自由概念.陳曉林,譯.[G]//劉軍寧,等.市場邏輯與國家觀念.陳曉林,譯.北京:三聯書店,1995:200-206.)。]國家制定法為個人提供選擇的機會,為普遍自由的實現提供前提。
三、農村習慣法對國家制定法的補充
由于國家制定法的局限和資源供給的不足,農村習慣法就以其內生秩序特性自然填補空白,滿足鄉村社會的規則需要。農村習慣法在調整范圍、功能等方面補充國家制定法。
(一)調整范圍補充
農村習慣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有不少是國家制定法所沒有調整的,像社會交往、紅白喜事這些方面的規定是農村習慣法獨有的。
在國家制定法和農村習慣法都調整的那些社會關系上,農村習慣法的規定比國家制定法更為具體、更為明確、更貼近村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能彌補國家制定法比較原則、抽象、一般的缺陷。農村習慣法基本都規定了熱愛勞動、助人為樂、扶助孤寡、熱心公益事業的內容。廣東澄海許多村(居)老年人協會都制訂了喪事簡辦的鄉規民約,通過鄉規民約推動殯葬改革、移風易俗,樹立愛老敬老、厚養薄葬的文明新風[14]。
在護林防火、生態保護、環境保護等方面,農村習慣法規定詳細、實施有力,社會效果比國家法更好。如廣州市蘿崗區九龍鎮楓下村于2006年6月制定了“環保公約”,對本村出現的有損村容和環境保護的不文明行為作出限制性規定,如養雞戶拉出的糞便,只許拉往田間地頭,不準在村中街邊、河邊堆放,確需在村中堆放的應一律建起糞池,并要在上面加蓋。農戶產生的垃圾,只許送入垃圾池或垃圾桶。定期組織檢查評比,對優秀的進行現金獎勵[15]。
(二)功能補充
國家制定法具有規范、禁止、懲罰等功能,而農村習慣法更強調鄉村社會的和諧,通過個人角色的培養、社會秩序的維持以實現“和諧”之道。
農村習慣法能夠解釋國家制定法的規范,細化國家制定法的規定,使國家制定法的內容更明確;農村習慣法適應不同農村社區的需要,具有針對性,有助于國家制定法的具體實施;農村習慣法具有補充國家制定法的功能。
農村互助習慣法在實現鄉村社會和諧方面有重要作用。農民在用水灌溉、日常耕作、房屋修建、生活娛樂等方面,都需要合作和互助,互助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大量的生產性的基礎設施,從一般的流通領域到生產領域,再到農村金融。習慣法對于源于血緣、地緣關系的社會交往、互惠行為進行調整,有助于保障農民的生活,促進農村生產。
農村習慣法強調農村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在農村地區,關系更多的是一種資本,是一種社會資本,是一種知識性力量,是一種結構性力量,也是一種潛在的社會能量,是一種鑲嵌于主觀和客觀結構中的潛在的力量,既能實現社會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也能復制社會關系本身[16]。
當然,鄉規民約、村規民約等農村習慣法的具體實施效果有所差異,對國家制定法實施的作用不可高估。正如云南河口瑤山鄉水槽行政村村長李國榮所說:“村規民約對我開展工作很有幫助,許多過去的老大難問題,都是靠村規民約才得以解決。當然,在執行過程中,也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如有的村民拒絕配合干部的調解工作,甚至無視村規民約的存在,因而村規民約的作用發揮有限。”[16]100
因此,農村習慣法可以補充國家制定法的不足,有助于國家制定法的實施,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是可以協調和良性互動的,是可以整合的。
四、結語
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這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敏感的現實問題。在新農村建設中,我們應從有利于國家法制統一,有利于農村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維護農村社會秩序,有利于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和法制建設出發,認真、慎重地對待和處理農村習慣法與國家制定法的關系。
作為文化傳統的一部分,農村習慣法不但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這些已溶入農村村民血脈之中的行為規范,即使在今天仍然是維護鄉村社會秩序、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規范。作為重要的內在制度,習慣法“在構建社會交往、溝通自我中心的個人和實現社會整合上的重要性早已被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們所認識”[17]。在堅持國家法制統一的前提下,允許農民的習慣法觀念、習慣法情感和某些習慣法規范的效力的一定存在,對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合拍于社會發展的內在運行規律,促進農村地區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和諧,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以法治的理念,以客觀、歷史、發展的眼光正視農村習慣法、認識農村習慣法。
同時,國家在法律制定過程中,應當考慮農村地區發展的實際情況,汲取農村習慣法的合理內容,吸納農村習慣法的積極因素,使國家法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否則形式的法律與農村實際的生活滋生距離,國家立法的目的終亦無法實現。同時應注重調解。在審理婚姻家庭、相鄰關系、小額民間借貸、人身財產損害賠償等民事糾紛案件中,常常遇到國家法律規定與農村習慣法的沖突,法院硬性判決往往很難案結事了。當國家法律與農村習慣法不一致時,法官宜通過調解把當地的習慣法揉進國家正式的規則里,進行調適性適用,以便求得“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和“情、理、法”的統一。
おお
參考文獻:
[1] 龍勝各族自治縣民族局《龍勝紅瑤》編委會.龍勝紅瑤[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2:49.
[2] 民政部基層政權司.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有關法規、文件及規章制度選編[G].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435.
[3] 王賢.恩平不少地方把“保護古樹名木”寫進鄉規民約 300多棵古樹名木“安享太平”[N].江門日報,2005-03-14.
[4] 陸廣毓.評理會還真管用――雁塔首場鄉規民約評理會小記[N].西安日報,2005-06-06.
[5]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三聯書店,1985:5.
[6] 張靜.基層政權——鄉村制度諸問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92.
[7] 趙佩麗,尹德坤.關于云南少數民族婚姻家庭問題的調查與思考[J].人民司法,2005(12):43.
[8] 春楊.徽州田野調查的個案分析——從“殺豬封山”看習慣的存留與效力[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2):18-21.
[9] 《法律的故事》撰寫組.在鄉村習俗與現代法律之間[N].檢察日報,2000-06-11.
[10] 云南少數民族罪犯研究編寫組.云南少數民族罪犯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92.[11] 張曉輝,等.云南少數民族民間法在現代社會中的變遷與作用[G]//張躍.跨世紀的思考——民族調查專題研究.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189.
[12] 俞榮根.羌族習慣法[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222.
[13]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范揚,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58.
[14] 李凱.澄海3萬多老年人簽名骨灰撒海[N].汕頭日報,2006-05-04.
[15] 文遠竹,穗先宣,張文濤.鄉規民約規范村民 蘿崗打造整潔新農村[N].廣州日報,2006-06-07.
[16] 匡自明.云南民族村寨調查——瑤族(河口瑤山鄉水槽村)[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100.
[17] 柯武剛,等.制度經濟學[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