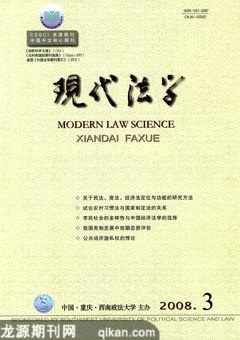析我國刑法的基本立場
陳家林
摘 要:我國兩部刑法典都是客觀主義性質的刑法典,1997年對1979年《刑法》的修正只是立法技術的提升,并不意味著刑法基本立場有重大的轉變。刑法首先是行為規范,其次才是裁判規范。純粹的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都無法說明我國刑法的基本性質,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考慮才符合我國刑法的基本立場。法益侵害說存在缺陷,應同時考慮規范違反說才能正確解釋刑法規范的性質。
關鍵詞:刑法;立場;主觀主義;客觀主義
中圖分類號:DF61
文獻標識碼:Aオ
我國刑法理論一直對主觀主義刑法思想與客觀主義刑法思想持批判的態度,認為它們都有失片面,而主張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1]。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于刑法的基本立場問題,我國并無爭論。上世紀90年代以后,不斷有學者對這種主客觀相統一的思想提出批評。有學者認為,它在方法論上是對規范科學的基本背離,“對于刑法秩序最大的危害在于,他為刑法脫離自身的規范性和做任意出入人罪的需要性解釋提供了廣泛的理論基礎。”[2]也有學者認為,“我國需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但這種主客觀相統一是應以客觀因素為基礎,還是以主觀因素為基礎,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3]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不少學者將我國兩部刑法典作了對比,認為兩部刑法典立場有了明顯轉變,從而明確提出應按照客觀主義的立場重新解釋刑法。其中,有的學者主張法益侵害說,有的提倡規范違反說,有的主張結果無價值論,有的則主張行為無價值論,從而使我國有關刑法基本立場的爭論復雜化和白熱化。筆者不揣淺陋,擬就此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對立的實像
西方國家的主觀主義刑法思想與客觀主義刑法思想都不是單純地主觀歸罪或客觀歸罪,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國學界過去對他們的批判存在簡單化和片面化的傾向。因此,我國刑法中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應以客觀主義為基礎,還是以主觀主義為基礎,的確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問題。那么如何區分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呢?我國有學者認為,“客觀主義總是堅持罪刑法定原則,而主觀主義總是緩和罪刑法定原則。結局,是客觀主義還是主觀主義,是堅持還是緩和罪刑法定主義,取決于是否重視刑法乃至國家在社會統制中的作用。重視刑法與國家作用的觀點,可以說是權威主義或干涉主義的態度;不重視刑法及國家作用的觀點,可以說是自由主義或不干涉主義的態度。”[4]還有的學者更明確地指出,“深層地看,一種刑法觀是否有利于限制刑罰權,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才是區分刑法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試金石。”[5]基于以上認識,這些學者認為,我國1979年《刑法》偏重于主觀主義,而1997年《刑法》則回歸到客觀主義,他們對1997年《刑法》的這種轉變大加贊賞。
筆者認為,上述學者對于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認識有相當的主觀任意性,并不符合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真實內涵。
(一)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特定含義與本質區別
在刑法理論中應當重視主觀還是客觀,這種爭論由來已久。奴隸制、封建制下的各國刑法幾乎都處罰思想犯,顯然是憑主觀定罪的。然而,在嚴謹的學術討論中,我們可以將這些時代的思想稱之為主觀擅斷的刑法思想,但并不稱之為主觀主義的刑法思想。這是因為刑法理論中所使用的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有其固有的含義,即分別與刑法中的新派、舊派相對應,是各學派思想在犯罪論中的體現。而學派的對立在刑法中又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概念,在歐洲,它是特指以賓丁以及畢克邁耶為代表的古典學派與以李斯特為代表的近代學派,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經過整個魏瑪共和國時代所展開的激烈論爭。在日本,則是特指1907年新刑法頒布后至二戰前以小野清一郎、瀧川幸辰為代表的舊派與以牧野英一、宮本英脩為代表的新派之間的學術爭論。
在學派之爭的時代,舊派與新派的對立盡管不局限在犯罪論領域,但有時也被稱為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對立[6]。這種對立影響到刑法理論的方方面面,而對其中一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主觀主義的觀點似乎與我國1979年《刑法》時代理論通說的立場相同或相似,正因如此,我國學者才認為1979年《刑法》是主觀主義的刑法。
但是,這些學者卻忽視了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即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既然產生于學派之爭,那么就必然有其完整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相互對立的理論基礎之上的,有著思想的內在統一性。如果剔除了其最基本的理論支點,僅就各個具體問題個別考察,那么就失去了這種理論的本來意義,我們不能斷章取義地理解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
事實上,客觀主義(舊派)與主觀主義(新派)的對立不在于具體問題上的分歧,而在于整個刑法觀的差異。客觀主義(舊派)主張意志自由、行為主義、道義責任、報應刑、一般預防;主觀主義(新派)主張意志決定論、行為人主義、社會責任、改善刑、特殊預防。更具體地講,客觀主義主張行為刑法,認為應受懲罰的是行為,行為概念在刑法理論中具有中心的地位。而主觀主義主張行為人刑法,主張應受懲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概念在刑法理論中具有中心地位,行為只是認定這種危險性的手段,即主張犯罪征表說。
由此可見,國內有的學者所主張的應當從是否有利于限制刑罰權,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角度來區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觀點,忽視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特定歷史背景,并不妥當。而且,即使是大家所公認的持客觀主義立場的學者也未必都主張限制國家刑罰權,例如,賓丁就主張類推制度,容忍類推適用,肯定刑法的溯及力[7],可見這一分類的不合理性。況且,上述標準也過于絕對,難以適用。眾所周知,在現代客觀主義內部還存在不同觀點的爭議,有的重視行為本身的惡性,有的重視對法益的實際危害,可以說后者更有利于限制刑罰權,按照上述觀點可能只有后者才屬于客觀主義,但事實上大多數學者都不否認二者的客觀主義屬性,可見區分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的標準并不在此。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歸納出如下結論:
第一,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概念產生自特定的時代,即與刑法中的學派之爭相對應,因而必須從各自學派的理論原點來理解這兩種不同的刑法立場,不能簡單地根據刑法是重視主觀因素還是客觀因素而將其稱之為主觀主義刑法或客觀主義刑法。
第二,區分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行為在該刑法或刑法理論中的地位。無論一部刑法或一種理論在認定犯罪時如何看重主觀因素,但只要它承認行為的基礎性地位,就是客觀主義的刑法或刑法理論。反之,一部刑法或一種理論無論它如何強調客觀因素的不可缺少,但只要它是以行為人為中心,就屬于主觀主義的刑法或刑法理論。
第三,與前兩點相聯系,應當區分主觀主義、客觀主義與刑法中分析具體問題時的各種“主觀說”與“客觀說”。現代刑法理論充斥著各種主觀說與客觀說,“刑法理論不過是一連串的‘主觀與客觀的迷思”[8]。這些主觀說、客觀說只是在解決具體刑法問題時的觀點分歧,與刑法中的主觀主義、客觀主義的對立并無絕對的對應關系。
(二)1979年《刑法》與1997年《刑法》基本立場的再考察
1.1979年《刑法》——客觀主義立場的刑法
根據以上的觀點,筆者不同意那種認為我國1979年《刑法》以及當時刑法理論的通說屬于主觀主義立場的見解。
(1)我國1979年《刑法》第10條規定,構成犯罪的是“危害社會的行為”,這就鮮明地表明了行為刑法的基本立場。而第14條至第16條又詳細規定了自然人犯罪主體的刑事責任能力條件,否定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能夠成為犯罪的主體,從而又明確地否定了主觀主義的社會責任理論。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我國1979年《刑法》并沒有將理論基石建構在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之上,其基本的出發點是犯罪行為,這充分反映出1979年《刑法》的客觀主義屬性。此外,1979年《刑法》明文規定意外事件不構成犯罪,分則條文具體規定了各種犯罪的客觀行為特征,這都是客觀主義刑法的表現。
(2)1979年《刑法》對構成要件的規定比較簡單,非常頻繁地使用“情節嚴重”、“情節惡劣”等表述,這些現象并不能說明1979年《刑法》的主觀主義屬性。認為1979年《刑法》屬于主觀主義刑法的學者多以該刑法規定粗疏為理由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但是,如果具體考察1979年《刑法》的立法背景,就可以看出上述推論并不成立。因為刑法條文規定的細密與否,固然在一定條件下與刑法的基本立場相對應,但是這種對應的前提是立法者在有足夠的立法經驗和能力的前提下對具體法律作出自己價值上的選擇,如果不存在這一前提,也就不能得出后一結論,因而不能將這種對應絕對化。我國1979年《刑法》是新中國的第一部刑法典,無前規可循。而十年“文革”造成法制空白、法律人才短缺,改革開放又剛剛起步,一切都有待探索,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種立法人才、立法能力上的現實與社會迫切渴望結束動亂、實行法制的實際需要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既要順應民心、順應時代,又要防止矯枉過正、弄巧成拙,因此,立法上不得不確立“宜粗不宜細”的基本原則。這是時代的局限性,而非立法者的主觀愿望,“現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夠,因此法律條文開始可以粗一點,逐步完善。有的法規可以先試搞,然后經過總結提高,制定全國通行的法律。修改補充法律,成熟一條就修改補充一條,不要等待‘成套設備。總之,有比沒有好,快搞比慢搞好。”[9]從“逐步完善”這一用詞就可以看出,當時的指導思想并不是就滿足于這種粗疏的狀態,而是寄希望于日后的改善。這充分證明了立法者追求完備刑法的客觀主義傾向。
(3)1979年《刑法》對犯罪預備與犯罪未遂設立了一般處罰規定,這也不說明刑法的主觀主義立場。刑法主觀主義以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為中心,因而只要行為人的行為表現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就可以作為犯罪加以處罰,而且由于這種主觀惡性并不隨行為人的客觀行為屬于預備還是未遂而有所改變,因而主觀主義對預備犯和未遂犯處以同既遂犯一樣的刑罰,即實行“同等主義”。與此相對,我國1979年《刑法》規定:“對于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對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理論上對此的解釋是,“犯罪預備對一定的社會關系還沒有開始侵害,它距社會危害結果的發生,還有相當的距離,與犯罪過程中的其他犯罪形態相比,其社會危害性較小,所以對預備犯一般應當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對未遂犯一般應當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這是因為,犯罪未遂所造成的實際危害一般較之犯罪既遂要輕,也即未遂犯的社會危害性一般輕于既遂犯。”[10]這種解釋重視的不是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而是行為的客觀危害,顯然是客觀主義立場的解釋。
(4)從犯罪主觀因素方面限制犯罪成立的做法也與刑法的基本立場無關。有學者認為,“在限定犯罪成立方面,舊刑法的許多條文也只是從目的(或動機)著手。……重視主觀因素的思想從這里也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來。”[4]60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仍屬牽強附會。犯罪的成立需要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這是現代世界各國都承認的“公理”。既然如此,根據犯罪的主觀因素來限制某些犯罪的成立就是一種非常合理的做法。即使以論者所推崇的日本刑法而論,日本現代的刑法理論屬于客觀主義刑法理論是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日本刑法同樣也根據主觀因素對某些犯罪進行限制。例如,成立偽造罪必須“以行使為目的”,否則就不成立犯罪。可見論者的主張并不成立。
(5)1979年《刑法》規定了類推制度,這也是部分學者認為1979年《刑法》主觀主義屬性的最重要的論據之一。但筆者認為,1979年《刑法》規定類推制度是時代背景使然,是不得已而為之。況且,立法者也沒有對這種制度表現出太多的贊賞與肯定。1979年《刑法》規定類推必須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就顯示出立法者對類推制度本身所蘊含的危險性的充分覺悟。從司法實踐看,自1980年到1997年的17年間,全國按照類推定罪的案件總共只有92件[11],從案件類型看也大多是一些性質輕微的破壞婚姻案件、侵占財產案件,而事實上1997年《刑法》卻增加了大量的新罪名。這一反差也旁證了立法者(以及受立法制約下的司法機關)對類推的慎重乃至從本質上反對的態度,否則我國1979年《刑法》施行階段的類推判決應當遠遠超過現實中的數字。
綜上,筆者認為我國1979年《刑法》并不象有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實行的是主觀主義。相反,1979年《刑法》是一部以客觀主義行為刑法為基調的刑法,它的不足反映的是時代的局限性,與主觀主義無關。
2.1997年《刑法》——客觀主義刑法的再確認
1997年,按照“要制定一部統一的、比較完備的刑法典”的修法原則,我國對1979年《刑法》進行了重大修改。這次修改力度很大,刑法條文從原來的193條增加到452條,被認為是我國刑事法制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我國大多數刑法學者對這次修改持積極肯定的態度,更有不少學者認為這次修改實現了刑法基本立場的成功轉換,即由1979年偏重主觀主義的立場轉換到現在的偏向客觀主義的立場。“既然新刑法以保持連續性、穩定性為指導思想,何以從舊刑法的主觀主義向客觀主義傾斜呢?”[4]69
如前所述,筆者認為我國1979年《刑法》即為一部客觀主義的行為刑法,因而筆者不認為1997年《刑法》在刑法的基本立場上有任何的重大轉變。相反,筆者認為1997年《刑法》貫徹了保持連續性、穩定性的指導思想,在1979年《刑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貫徹了重視主觀的價值取向。
具體而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理論積累以及司法實踐經驗不斷增多,原來想做卻無法做到的立法精致化的目標到了1997年終于有了實現的可能。1997年《刑法》在立法技術上較之1979年《刑法》有了諸多的改進。例如,根據實踐中所積累的經驗,大量擴充了刑法中的罪名,同時相應地廢除了類推制度,而正式確立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將原來的含混的口袋罪分解為許多具體的犯罪;對法定刑的升格條件作了具體規定,進一步縮小了法定刑的幅度;對假釋、減刑的條件規定得更加具體等。這些改動顯示出我國刑法對客觀主義立場的一貫堅守,反映出立法者“修改補充法律,成熟一條就修改補充一條”的一貫立場。
毫無疑問的是,1997年《刑法》的確更大程度地限制了司法機關的權力,更加追求對公民權利的保障。但是,如前所述,這本就是1979年《刑法》制定時立法者的指導思想,更深層次地講,這本就是1979年《刑法》客觀主義屬性所決定的刑法追求的終極目標。由于時代的變化,條件的成熟,1997年《刑法》完成了1979年《刑法》所欲做而不能做的工作,這充分體現了時代的進步,也體現了新舊刑法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而與刑法基本立場的轉換毫無關系。
另外,還必須注意的一個事實是,1997年《刑法》在繼承了1979年《刑法》的基本立場,堅持了行為刑法的基本屬性的同時,也繼續堅持了在客觀主義立場基礎上更加重視主觀因素的法律傳統,總則條文的極少改動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立法者在客觀主義的內部分歧中,選擇了更加重視行為本身惡性的立場。
二、客觀主義內部的價值選擇
(一)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
我國兩部刑法典都是行為刑法,都堅持客觀主義的基本價值取向。但是,客觀主義內部也存在諸多爭議,這首先涉及的就是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區分問題。
刑法規范是行為規范還是裁判規范,這一爭議由來已久。費爾巴哈很早就論述了這一問題,他認為,“刑法,第一,與行使國家司法權的官吏相聯系。刑法要求官吏對犯罪應當根據刑法處罰這一完全的拘束”,“第二,刑法與作為就違法行為應予威嚇的可能的犯罪者在刑罰權之下的所有的人相關聯。”[12]可見,他認為刑法既是指導司法官吏裁量適用、限制司法權力的裁判規范,又是規范一般人行為的行為規范。但費爾巴哈并未將這兩種規范對立起來,相反他把兩者統一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之下。而對于裁判規范與行為規范的先后次序,費爾巴哈并未論及。
但是,從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本質來看,二者卻存在對立的可能。因為如果把刑法理解為行為規范,那么針對的對象就是一般人,在判斷行為的性質時就應當立足于行為時社會一般人的觀念加以衡量。相反,如果將刑法理解為裁判規范,那么針對的對象就是法官或者說科學的一般人,在判斷行為的性質時就應當立足于行為后科學的因果法則加以衡量。由于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本身蘊含著這一對立,費爾巴哈以后的學者逐漸采取了不同的觀點。
有的學者認為,刑法是行為規范,或者說主要是行為規范。例如,川端博指出,“刑法在構成要件、違法性之層面,對行為發揮評價規范的機能,其結果是對一般人具有作為行為規范的性格……作為刑法規范對象的一般人要避免刑法所禁止的行為,實施刑法所命令的行為。正是在這一點上,刑法發揮作為行為規范的機能……所以,刑法不只是單純以裁判官為對象的裁判規范。”[13]
有的學者則認為,刑法是裁判規范,至少主要是裁判規范。如木村光江指出,認為刑法是行為規范的觀點雖然易于為國民所理解,但它們所理解的違法一詞卻偏離了日常用語本身的含義。“問題在于,為何國民的行動以及與之相連的一般預防的效果能夠決定‘違法論。事實是,只有進行責任非難并加以處罰時,國民才會以法院的判決來確定自己的行為準則。如果確立了‘某種行為雖然違法但絕對不處罰的判例,那么對于國民的行為就不能起到制止的作用。”[14]
筆者認為,單純地將刑法規范視為行為規范或者裁判規范都有不合理之處,刑法規范同時具有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的性質,但以行為規范性為主。
首先,刑法規范是行為規范。毫無疑問,刑法規范能夠規范國民的行為。奴隸制、封建制時代的刑法強調“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從而便于統治者任意出入人罪。但是,近代刑法確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則,要求法律必須是明確和公開的。“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因為,對刑罰的無知和刑罰的捉摸不定,無疑會幫助欲望強詞奪理。”[15]公開的刑事法典能夠告知人們什么是犯罪,犯罪應當處以何種刑罰,從而使人們了解法律允許人們做什么,禁止人們做什么。刑法的這種功能又被稱為規制功能,它是刑法與生俱來的功能,是刑法內在的屬性,“對于一般國民來說,刑法就是行為法”[16]。一部刑法一經公布,即使尚未有任何根據該刑法作出的判決,仍然會具有指導人們行動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講,刑法規范首先是行為規范而不是裁判規范。
其次,刑法規范同時又是裁判規范。制定公布的刑法并不會自動地加以適用,相反,如果一部刑法長時間得不到應有的適用,那么這部刑法也就形同虛設,刑法本身所蘊含的行為規范的功能也會喪失殆盡。因此,刑法要從紙面法律走向現實法律,必須依靠司法機關的適用。“刑法規范是行為規范(第一次法)和裁判規范(第二次法)的復合體。所謂行為規范或第一次法是指不為一定的有害行為或為一定的有益行為的法。如果人們沒有遵守第一次法的命令或禁止規范,被判定為違法,則給予其一定的制裁,這便是裁判規范或第二次法。”[17]
單純地將刑法規范理解為行為規范或者裁判規范都會存在不合理之處。例如,如果僅將刑法規范視為行為規范,那么“徒法不能自行”,刑法將會失去其威懾力,最終也會失去作為行為規范的功能。也正因為如此,貝卡里亞才主張刑罰要具有及時性,“只有使犯罪和刑罰銜接緊湊,才能指望相聯的刑罰概念使那些粗俗的頭腦從誘惑他們的、有利可圖的犯罪圖景中立即猛醒過來。推遲刑罰只會產生使這兩個概念分離開來的結果。”[15]14
同樣,如果單純地將刑法規范理解為裁判規范,這就意味著刑法針對的只是司法人員,這就容易導致無視一般國民即規范接受者的理解情況,從而導致與法律規定不符的錯誤結論。例如,現代各國刑法都規定一定年齡以下的年幼者以及精神病患者不承擔刑事責任,顯然這考慮的是刑法的行為規范功能,由于這些人無法理解規范的內容,因而無法對他們適用刑法規范。又如,雖然各國刑法理論對于成立故意是否需要具備違法性認識存在爭議,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如果“某種行為一向不為刑法所禁止,后在某個特殊時期或某種特定情況下為刑法所禁止,如果行為人確實不知法律已禁止而仍實施該行為的,就不能講他是故意違反刑法”[18]。再者,刑法的一般預防功能也不是從判決中推導出來的,裁判規范約束的僅僅是法官,判例之所以具有指導人們行動的功能,歸根到底還在于判例中所蘊含的行為規范,因此,判例的一般預防功能仍然只是行為規范所具有的功能。
那么在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之間,是否有先后或主從之分呢?筆者認為,刑法規范之所以能夠分解為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是因為它們所針對的對象不同。行為規范所針對的是普通的一般人,而裁判規范針對的是司法官員。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無先后主從之分。然而,如果我們作進一步的分析,就會意識到,作為裁判對象的行為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首先是根據自己對刑法規范的自覺或不自覺的理解來實施犯罪行為的,因而在對他們進行定罪量刑時,也應當首先考慮刑法規范對行為人所發揮的作用,即刑法的行為規范功能,因此,刑法規范既是行為規范也是裁判規范,但首先是行為規范。“刑法可以認為是制裁規范,然而毫無疑問,其中同時含有規范國民行動的機能,并且這還莫如說是刑法的本質性目的。只不過是在屬于實定法的刑法中,其制裁性機能表現于前,命令性機能隱藏于后罷了。制裁可以說是刑法的第二位的性質。”[19]
由于刑法首先是行為規范,所以,在對行為性質進行分析時,應當立足于行為時,根據一般人的立場進行判斷。同時,由于刑法又是裁判規范,所以,在對行為性質進行第二次考察時,應當以科學的一般人的觀點進行事后的考察。
(二)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
所謂行為無價值,是著眼于行為的反倫理性而予以否定的價值判斷。反之,所謂結果無價值,是著眼于行為惹起對法益的侵害或危害的結果而予以否定的價值判斷[20]。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概念肇始于威爾澤爾,自從他將二者作為對立的概念提出后,造成了自學派之爭后的刑法理論的又一次大分化。“近年來與學派之爭相類比的,則是關于違法實質的從60年代后期開始的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論爭。”[21]
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在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尖銳的對立:第一,在違法性的判斷上,結果無價值論認為不需要考慮行為人的主觀因素,不承認主觀的違法要素,而行為無價值論則普遍承認主觀的違法要素。第二,在違法性的判斷標準上,結果無價值論認為應以科學的一般人為標準,而行為無價值論則主張以社會一般人為標準。第三,在違法性的判斷時間上,結果無價值論一般主張對違法性的有無進行事后判斷,而行為無價值論主張以行為時為基點進行判斷。第四,在如何理解刑法目的的問題上,結果無價值論將刑法的目的首先理解為保護法益,所以違法性的本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脅。行為無價值論則認為刑法的目的是保護社會倫理秩序,因此違法性就是對作為秩序基礎的社會倫理秩序的違反[22]。
在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對立過程中,持行為無價值論的學者認識到這種學說忽視法益侵害的缺陷,因而對自己的學說作了相應的修正,從而產生了兼采結果無價值與行為無價值的二元的行為無價值論。
二元的行為無價值論認為結果無價值與行為無價值都為不法奠定根據。它認為,通過引起事態無價值而違反評價規范是結果無價值,而違反以平均人為對象的作為命令的決定規范則是行為無價值,原則上必須綜合兩者才能認定不法。據此,這里的行為無價值論具有三個特征:第一,承認主觀的要素是不法的根據;第二,單純違反行為規范也可以是不法;第三,這種意義上的違反行為規范,是指平均人都可以遵守規范,而該行為人卻不遵守規范,因而具有“規范違反性”[23]。
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對立是關于違法性本質的對立,由于我國不采用大陸法系國家的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的三階段的犯罪成立體系,因此,我國通說中并不存在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這種理論。但是,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所爭論的問題在我國同樣存在,因而這一問題也同樣值得研究。從法學淵源來看,我國目前的犯罪論體系來源于前蘇聯,而前蘇聯的犯罪論體系則改造自德國的犯罪論體系。“前蘇聯學者對大陸法系的上述犯罪論體系進行了改造,將上述成立犯罪的三個條件轉變為犯罪構成:構成要件被改造為犯罪客觀要件;實質的違法性被改造為犯罪客體;有責性被分解為犯罪主體與犯罪主觀要件。”[24]從這個意義上說,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問題在我國刑法理論中應當屬于刑事違法性的實質面,即社會危害性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也有學者主張結果無價值論,并認為客觀主義犯罪論理所當然主張結果無價值論。筆者不同意這一觀點,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都是客觀主義內部的爭議,因而所謂客觀主義犯罪論理所當然主張結果無價值論的觀點是不成立的。而且,單純主張結果無價值,不符合我國《刑法》的規定。
第一,我國《刑法》在規定罪與非罪的區別時,相當重視行為人的主觀惡意。結果無價值論者認為,行為是否具有實質的違法性,只是取決于行為是否侵害或者威脅了法益,而與行為人的主觀能力及故意、過失無關,但我國《刑法》的規定與此正好相反。例如,在經濟活動中,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并無犯罪故意,即使造成了對方巨大的經濟損失,那也只是民事問題;相反,如果行為人以犯罪的故意通過經濟活動騙取對方的錢財,即使這一數額遠遠小于前述的損失數額,仍然可能構成犯罪。對這種規定,僅從客觀損害上來解釋顯然是行不通的,可見刑法對行為人主觀因素的重視。
第二,對于同一類型的犯罪,刑法往往根據行為的不同方式規定為不同的犯罪,這顯然考慮的是行為無價值。結果無價值重視的僅僅是對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險,可是對于侵害同一法益的犯罪,如侵犯財產罪,刑法根據行為人實施行為的不同方式,將之劃分為盜竊、詐騙、搶劫等不同的罪名,這表明刑法對行為無價值的重視。
第三,同樣的犯罪行為,因為主體的不同,刑法規定了不同的罪名,這考慮的也是行為無價值。我國《刑法》對于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挪用公款罪與挪用資金罪規定了不同的罪名與法定刑,顯示出對行為主體性質的重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脫離行為無價值而主張純粹的結果無價值的觀點不符合我國《刑法》的規定。
同樣,在認定犯罪時,如果脫離結果無價值而單純地主張行為無價值也是不妥當的。因為一元的行為無價值論僅將刑法規范理解為行為規范,但是如前所述,刑法規范不僅是行為規范,而且還是裁判規范。一元的行為無價值論無法說明刑法為何要設立行為規范,因而它忽略了法益保護這一刑法任務,屬于過度的“行為規范論”。而且,從具體法律規定來看,我國刑法規定過失犯發生結果才處罰,結果犯以結果的發生為既遂的要件等,都顯示出對結果無價值的重視。
筆者認為,在認定犯罪的成立時,既不能忽視行為無價值,也不能無視結果無價值,行為無價值以結果無價值為前提,同時使作為結果無價值的事態在刑法上的意義更加明確。因此,只有把行為無價值和結果無價值并合起來加以考慮才符合我國刑法的基本立場。
(三)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
與刑法規范的性質以及行為無價值與結果無價值的爭論相關聯,關于違法性的實質還存在著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的爭論。法益侵害說認為,犯罪是對法所保護的生活利益的侵害或者引起危險(威脅),因而違法性的實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或威脅。規范違反說則認為,違法性的實質是違反法規范或者違反法秩序。規范違反說認為,刑法規范的實質是社會倫理規范,從根本上看,法是國民生活的道德與倫理。所以,違反刑法的實質是違反刑法規范背后的社會倫理規范。
我國刑法理論中本無法益侵害說與規范違反說之類的爭論,但近年來,主張引進法益概念的學者呈增多趨勢,主張法益侵害說的學術觀點影響力逐步擴大,但也有少數學者提倡規范違反說。筆者認為,法益侵害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完全排除倫理道德的因素,單純主張法益侵害說則未必能夠全面地解釋刑法中的問題。
1.法益概念具有模糊性
法益是德日刑法理論的核心概念。然而對于什么是法益,德日學者則存在爭議。李斯特認為,由刑法所保護的對象就是法益,他將法益表述為“人的生活利益”。麥茲格則認為,“法益是由客觀的法所認可的利益存在的狀態,即法所承認的、刑法所保護的客觀價值。因此,法律中所特別列舉的手段的不使用及法律中所規定的實行樣態與方法的回避,也要納入法益思想與概念之下;不僅如此,‘人的關系也不能被排除在法益概念之外;置于刑罰之下的‘心情刑法本身也包含在法益概念中。”[25]二戰后,耶賽克主張社會行為論,并明確地將法益作為純粹的非物質的價值來加以把握。他認為,法益是以共同社會的原來存在的安全、幸福及尊嚴為基礎的社會秩序的理念的諸價值,是社會秩序的精神價值[24]104。羅克辛也認為刑法的任務在于保護法益,“法益是在以個人及其自由發展為目標進行建設的社會整體制度范圍內,有益于個人及其自由發展的,或者有益于這個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種現實或者目標設定”[26]。羅克辛認為純粹的思想性目標設定所保護的不是法益,純粹違反道德行為所侵害的也不是法益,他同樣將法益理解為價值。
由上可見,法益概念本身并不清晰,具有多義性。有的學者將法益解釋為一種利益,有的學者則解釋為一種狀態,還有的學者解釋為價值,其分歧主要在于是否承認法益概念精神化的問題。
2.法益侵害說難以適應現代的“危險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