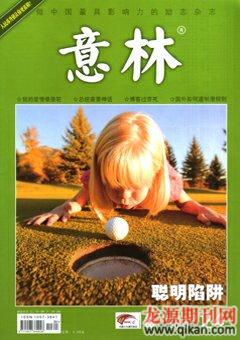咖啡流行是趁酒之危
余澤民
歐洲人喝咖啡成癮,但咖啡并不是歐洲人的發現。早在16世紀末咖啡從阿拉伯半島傳到歐洲大陸之前,就被阿拉伯人奉為“代酒的神品”。穆斯林禁酒是被明明白白地寫進《古蘭經》的。
有一個通俗易懂的阿拉伯傳說:一天,一個惡官將一位穆斯林青年招進官府,狡詐地問他:“聽說你信奉真主。那我今天就考考你。”隨后,他列出四件事讓年輕人選擇:一是強暴民女,二是劫財害命,三是縱火燒村,四是飲一壺酒。小伙子暗想:頭三件罪惡自不能干,喝一壺酒又有何妨?
這時,魔鬼也悄悄走來,附在耳邊柔聲勸他:“這酒既能健身強體,又可消愁解憂,你就喝了吧!”于是,小伙子提起酒壺一飲而盡。一壺酒下肚,年輕人頭暈眼花,不能自控。于是在魔鬼的誘惑下,一口氣把另外三件事都做了。
英國人則不然,他們不僅早在16世紀就從阿拉伯半島引入了咖啡,而且在17和19世紀,先后掀起過兩次號稱“咖啡館運動”的禁酒熱潮,不僅將這種曾被英國人譏諷為“混合了煤灰和臭鞋味道的黑湯”的舶來品傳播到各個家庭,而且還以喝咖啡為形式組成了許多小型沙龍。其中最有名的該算牛津咖啡俱樂部,一些志同道合的科學家和學者聚在一起交流觀點,講演辯論,成為英國皇家學會的前身。
17世紀的英國,剛經過一場并不徹底的社會變革,社會動蕩,經濟低迷,倫敦更是“躁亂無序”的代名詞。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和到新世界尋夢的外鄉人擁進倫敦,卻沒有工作,無路可走的人們聚集在酒館里醉生夢死,逃避現實。
正是在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酒館盛行、酗酒嚴重成了17世紀末英國最令人頭痛的一大社會問題。人在絕望的境地只有兩種選擇:或者用什么東西麻醉自己,讓自己幻覺地獄里的生活并不那么痛苦;或者用什么警醒自己,用真實的疼痛逼迫自己在絕路逢生。酒館庇護了前者,咖啡館聚集了后者。
從當時倫敦咖啡館的內部裝修來看,也與酒館存在天壤之別,“清醒”,似乎是咖啡誓與酒精決一雌雄的廣告語。傳統的倫敦酒館氣氛懨懨,光線陰暗,骯臟破舊,烏煙瘴氣;咖啡館卻截然不同,店堂里大多立著書架,掛著圖片或照片,桌椅舒適,衛生整潔,墻上柱上掛著鏡子,家具大多古樸考究,到處透出人文情調。酒館的門通常關著,而咖啡館的門一般敞開。泡酒館的以下層市民為主,而去咖啡館的多屬知識階層,而平民喝咖啡大多在家。酒館里經常打架滋事,一般只有叫來警察才能解決,而在咖啡館卻有自己的解決習慣———假如有誰引發了爭吵,他必須買一杯咖啡向對方道歉。總之,與酒館相比,咖啡館相對平靜、清醒、有序、文明。酒館是發泄之地,咖啡館是談話的場所,咖啡喝再多,頂多讓人興奮話多,但不會使人情緒失控。
政府意識到酗酒造成的社會問題,于是到處張貼告示:“禁止酗酒,禁止穢語。”不過所謂“穢語”并非指吵架罵人,而是禁止持不同政見者的煽動性言論。由此可見,咖啡在英國的流行,得力于當時的大氣候。許多酒館也知趣地紛紛“從良”,就連莎士比亞生前愛泡的小酒館也改頭換面,變成了著名的“威爾咖啡館”。
有趣的是,咖啡于19世紀末在英國的再度流行,同樣要感謝“禁酒運動”。這次“禁酒運動”的目的是為實現一個十分美好而幼稚的社會目的:幫助大批因酗酒而減低或喪失勞動能力的產業工人戒除酒癮,試圖通過這種天使般的手段拯救他們,同時緩解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于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在社會活動家們的鼓動下,英國許多大城市出現了明亮寬敞、布局簡單的新型咖啡廳,并且打出“代替啤酒的溫馨飲料”的廣告詞。咖啡運動的倡導者們不僅在工廠散發傳單動員工人們來這里喝茶或喝咖啡,還為客人免費加工食品,建議他們到咖啡館用餐。同時舉辦一些知識講座,發放一些免費報紙雜志,有的地方為客人準備了桌球、象棋、紙牌等娛樂設施,試圖通過咖啡館打造一個健康開朗、與社會為友的“新工人階層”,咖啡館一度人頭攢動,煙霧騰騰。除了工人、平民和流浪者外,不少窮困潦倒的藝術家也聚到這里大談烏托邦的夢想和無產者藝術的理念……但是好景不長,社會問題依然尖銳,加上世界大戰的打擊,轟轟烈烈30年的“咖啡館運動”連同“禁酒運動”一起偃旗息鼓,倫敦街頭又剩下了酒館。咖啡第三次興起,則是“二戰”之后的事了。
所以從歷史上看,咖啡館在英國乃至歐洲的流行,都屬于落井下石,趁酒之危了。
(晉華云摘自《歐洲的另一種色彩》百花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