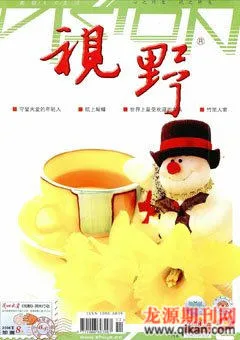畫布上的淚滴
徐 魯
據說,米勒小時候,村子里的一位神父對他說過:“我的孩子,你有一顆會帶給你許多苦惱的心,你不知道你將來會受多大的苦呀!”米勒后來的人生經歷,果然被神父言中了。他成了一位擁有《扶鋤的農夫》、《拾穗者》、《播種者》、《晚禱》和《牧羊女》等不朽作品的桂冠畫家,同時也是巴比松那片寒冷的土地上人人皆知的農夫的兒子和終生與苦難為伴的藝術家。
那是一個冬日的黃昏,來自外省的窮困潦倒的青年畫家米勒,孤獨地走在巴黎街頭。他走過一個明亮的櫥窗時,忽然聽到兩個青年人的對話。他們一邊看著陳列在櫥窗里的少女裸體畫像,一邊談論著:“這畫糟透了,簡直令人厭惡。”“是啊,米勒的畫嘛!他是個除了裸體女子,其他什么也畫不出來的人!”米勒聽到這些,臉頰不由得紅了起來,感到頭暈目眩。當時的巴黎,有一種怪現象,只有女人裸體畫像才可以換幾個錢去買面包。
米勒親耳聽到了觀眾對他的評論,心里再也平靜不下來了。一回到家里,他就對妻子說:“我決定今后不再畫裸體畫了,即使生活將會變得更為困苦。”他心情激動,臉色蒼白。過了一會兒,他平靜地說出了自己的打算:“我已經厭倦巴黎了,我想回到農村。”就在這一瞬間。米勒的眼前悶過了他在巴黎的全部日子。他23歲時從偏僻的農村來到了日夜向往的大都會。他經受了城里人無數的白眼、嘲弄和輕蔑。畫女人裸體畫像雖不值得,但總還可以換幾個面包充饑,而自以為認真創作出來的畫作,卻一幅也賣不出去。
如今,為了真正嚴肅的藝術,也為了心靈的歡愉和生命的價值,米勒終于作出了決定:選擇也許比在巴黎更加艱難、更加饑寒交迫的道路,回到巴比松鄉村去!
在巴比松,米勒像那些真正的農人一樣,一邊從事繁重的勞動補助生活,一邊從事著艱苦的藝術創作。令人意外的是,在巴比松的厚土上,米勒的身體和精神漸漸健康和旺盛起來。他用飽蘸深情的畫筆,畫他所接觸和熟悉的農民,歌頌他們的勞動、愛情和淳樸善良的性格,同時也毫不保留地揭露剝削制度的殘酷,暴露農村的種種不幸,在沉郁凝重的藝術追求中透出自己強烈的愛與恨。他說:“我生來就是一個農夫,我愿意到死也是一個農夫。我要盡力描繪我所感受到的東西。”他的《拾穗者》、《牧羊女》、《晚禱》、《死神與樵夫》等作品都誕生在巴比松赭色的原野上。
“你坐在樹下,感覺到可能享受到的全部安樂和平靜。”他像一個真正的農民一樣,在家鄉的村莊里生活著、觀察著、感受著。他的目光又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的目光。他寫道:“突然,你看到幾個窮人背著柴,從一條小徑中費力地走出來……”他感到,這些沉重的柴火仿佛是人世的苦難,背在那些微賤的農人背上,同時也壓在他這個農民的兒子的心靈上。他無力拯救他們,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和他們一起去承受這生活的苦難與艱辛。
“藝術不是消遣,”他說,“那是一種抗爭!車輪錯亂地滾動,人在其中被碾得粉碎。”為了神圣和莊嚴的藝術,米勒在鄉間辛勤地勞作著。用他的朋友盧梭的話說,他像一棵開花結果太多的樹一樣消耗著自己。他在他的畫布上無限深情地歌頌著那些樸實的勞動者:種土豆的人、紡織女工、采石工、牧羊女、扶鋤的農夫、伐木者、剪羊毛的人、耙地的女人……他認定。所有這些人的勞動,都顯示了人類真正的尊嚴和最真實的詩情,這些勞動者的崇高和偉大是無與倫比的。
只有真正的藝術,才經得起歲月長河的淘洗。米勒活著的時候,他的畫并未得到太多的贊美,相反,巴黎的藝術界給予他更多的是挖苦和嘲弄。但隨著歲月的流逝,米勒的作品卻越來越顯示出強烈的現實力量和強大的藝術生命力。他的畫幅里展示出來的,不僅僅是一種寧靜淳樸的鄉土之美,還有更深沉更廣闊的、整個人類的戀歌與鄉愁。巴比松蒼涼而厚實的大地以及大地上的勞動者,牽動著一代代人的鄉土情思和還鄉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