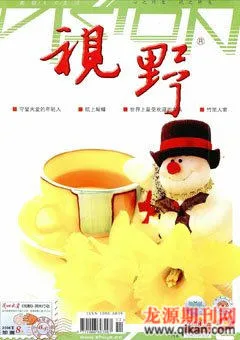竹里人家
莫景春
深藏在西南的人家都喜歡竹子,它高風亮節,青潔滑亮,耐看;竹葉青青,遮天蔽日,能調節氣候。要是房前屋后有個巴掌大的一塊空地,便見縫插針地隨手插下個竹竿。沒幾天,枝節上竟透出幾點嫩芽,慢慢長高。冬去春來,居然蔓延一大片,最后黑壓壓的全把房子罩住,綿綿數里,蒼蒼莽莽的一片竹海。黃昏時分,縷縷青煙從綠海中裊裊升起,盤旋在竹葉之上。雞鳴犬吠相聞,竹海深處紅墻黑瓦;這便是竹里人家。
竹里常是悠閑地逛著老母雞,老母雞“咯咯”叫,后面拖著一大群“吱吱”叫的小雞。竹下的土壤是濕潤松軟的,蟲兒特別多:有鉆來鉆去的長條蚯蚓,有爬上爬下的甲蟲,有竹葉上飛前飛后的蠅兒。竹里人家的雞是極少用飼料喂養的,只需老母雞用大爪一撓,蟲兒便紛紛散出,小雞們便前前后后地撲著啄著。忙個不停,跟著母親的爪子,忽左忽右,不一會兒囊兒脹鼓鼓的,又快樂地追逐嬉戲去了。夕陽西下,雞兒回棲,順手抓一把谷子,一撒,補補能量。竹里人家的雞兒肥瘦適中,肉兒帶些野味,鮮美甜嫩,有個什么客人遠道而來,隨手抓來一只,就是一桌極好的山珍海味,再添上一兩碗醇香的竹青酒,更使客人“不辭長作竹里人”了。
三四月是竹里人家最朗潤的日子。綿綿的春雨,打濕了空氣,使竹林濕潤潤的。春光融融,滿地竹筍破土而出,透著新鮮泥土的氣息,齊刷刷的一大片。拔出一兩根,剝下青硬皮兒,露出嫩白的身子,壓碎,洗凈,放進清水鍋里一煮,沒幾分鐘,竹青味自鍋里逸出,讓人清爽;不必加什么佐料,只需往鍋里撒一把鹽,加點油,那白渾的湯兒,一口吞下,清新爽口;再撈起一根筍兒,咬上一口,清脆可口,拌著飯兒,甜得你大口大口地嚼著飯;若再混炒個竹里人家的酸菜,黃白相問,酸甜適宜,又別有一番滋味。這是老天爺的賜物,自生自長,無需施肥管理。城里人挺喜歡這綠色食品,有事沒事地往鄉下找這東西。
竹子是引水的,水是招竹子的。凡是長竹子的地方,都有一條細流涓涓而過,凡是水漫過的地方,也常常伴著青翠的竹子。常是一條整天唱著歡樂的歌的小溪穿林而過,翠竹把白亮亮的水染成青青的,連溪里的小魚也給染綠了。小溪匯成小河,竹里人家又把竹子砍下來,串成竹筏,又可以在清幽幽的河面上漂流,網些小魚或蝦什么的,解解葷渴。河岸或溪邊也常常見著用竹子搭成的支架,擺上幾塊稍平的石頭,那兒便傳來“撲撲”的捶衣聲,姑娘甜美的笑聲和著清亮的流水聲,飄蕩在竹林里,格外悠揚。要是碰上個月白風清的夜晚,竹林“呼呼啦啦”的響,聲音細膩而微妙,擦過耳邊,感覺是那么的縹緲。月亮透過密密的竹林,漏下幾縷,更顯得幽遠。再有個多情的小伙子砍下竹管,隨意一吹,那笛聲悠揚簡直把人的魂兒都勾走了,難怪竹里人家說他們時時在享受天籟音樂。
竹里人家是沒有季節感覺的。竹葉青青,一年四季都是如此,沒有外面世界那種大把大把葉子摔落下來,樹兒光禿禿,沒一點生氣的傷感,也沒有外面世界那種大片大片山花爛漫,萬物蓬勃的熱烈。狂風吹不進竹里,竹里人家像是舒適地躺在溫暖的搖籃里,由竹子精心地呵護著。炎熱的夏天,密密層層的竹葉又把毒辣的陽光溫婉地拒絕,竹里是清風送爽,因竹子又是招風的,輕風微微拂過,甚是愜意。入冬,偶有雪花飄落,卻沒讓人感覺寒意。于是一年四季,滿眼青乎乎,滿身清攀攀。只在房前屋后的地上突出滿地尖筍時,竹里人家才恍然大悟:原來春天已經長得很高很高了,該弄點春天的活了。
竹里人家的日子是用竹子編的。閑著沒事,在竹林里晃悠,摸摸這支,看看皮兒老青了沒有;敲敲這根,聽聽聲音脆了沒有。選幾支老的砍下,削出薄薄的青皮兒,細長的竹條兒在手里不停地跳舞,不需多時,一只結實美觀的籃子便活脫脫地出現。竹里人家的東西大都是竹子做的:手里拎的籃兒,背上背的簍子,肩上挑的籮筐,甚至圍著菜園、雞柵、豬欄的都是竹子的。竹子質地堅實柔韌,經久耐用,使用多年,仍是橙青依舊,而且泛光,比以前更為青亮;又輕便好用,上山采摘什么物,一股腦兒地往筐里塞,那筐肚大嘴闊,裝得多,又光滑,可在草叢間穿梭自如,不擔心藤兒蔓兒會勾著,省事;下河撈蝦打魚,那竹筒一網,水滲走了,魚留下了,令人興味無盡。竹具也不招誰惹誰,質地堅實,令蟲兒們望而生畏,少有所犯,因而竹里人家的竹具常常是數代祖傳的。更有竹編的涼席,精選晝夜溫差大而生長在幽谷深澗中的慈竹,削成數萬根篾,精心編制,柔軟舒適。炎炎夏日,往席上一躺,陣陣竹青味沁人心脾,涼意透人暑氣全消了。竹里人家別出心裁地在這些竹具上編上個“福”或別的什么美麗圖案,精致漂亮,傳到城里,竟成寵物。生意人紛紛往竹里趕,與村里合作辦起了竹品加工廠,竹子紛紛倒下,竹品源源不斷地往竹外送。竹里人家的口袋也漸漸地脹起來,如一節一節的竹子漸漸拔高。
如今,竹林深處,雞犬相聞之間,更多了些汽車和摩托車的喇叭聲,電視、音響的歌舞聲。它飄蕩在竹林間,悠悠地散去。
竹里人家的日子如清風拂動的竹子一般悠悠地晃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