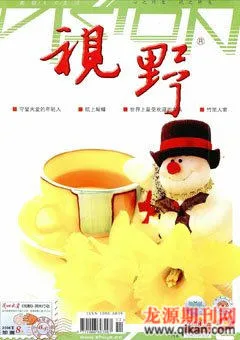獨居瑣記
李臻穎
中國古代多“隱士”,“隱士”一詞出現在中國是頗有特色的。
一方面來說,“隱士”在成為隱士之前,是抱著“仕”之理想的,一旦理想不行于天下,“邦無道則隱”的時候,“仕”字只好“隱‘士”了——隱去右邊的“士”,于是終于成了“人”了。
但中國的知識分子似乎總是不安于做一個單純的人的,所以從另一方面來理解,所謂“隱士”也不過是隱著的士,是潛在的士,一旦給了他做罰“士”的機會,他立刻也就不隱了。
一個人踱步在未名湖畔,看著一對對小情人老情人親親熱熱的樣子,不禁頗為感嘆。戀愛中的人似乎特別留戀兩個地方——山坡與水畔。記得讀高中時,學校的那個小山坡被譽為“情人坡”,因為隨便走走都能踩到幾對。后來我們嫌“情人坡”的名字過于直白,于是改名為“谷欠坡”,外人常常不知所以,其實只要將“谷”“欠”二字一合,便知其中妙處。現在到了大學里,湖水越來越不滿的未名湖倒每天能人滿為患——而且是“情人滿為患”,所以說,獨身者去胡邊很容易受刺激,幸好湖水淺,尚構不成投水沉湖的條件。記得上次去中國人民大學時,他們那深不過踝的“一勺池”竟然也滿滿地圍著竊竊私語的戀人,仿佛一群人圍著一個大腳盆談戀愛,其場面實在讓人哭笑不得。
孔老頭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人一旦處在戀愛中,就真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了,于是情人們一個個都“求仁得仁,求智得智”了。
現在作學術論文也好,作學術刊物也好,都要講究學術規范。而學術規范的一個很大的體現便是要做好注釋。所謂“注釋”有時是件很好笑的事情。很多時候,一篇論文注釋的多少在于作者知識的廣博與否。知識貧瘠者,稍得一感想訴諸紙筆,便以為是發前人所未發了,實則不過盡拾前人之牙慧。而知識廣博者一旦作完一篇論文,又只發現處處皆可從前人所言中尋根究底,只覺得滿紙都應該寫上注釋。更多時候,做注釋比做文章還傷腦筋。因為做文章很多時候不過是回憶、組織些別人說過的話并提出些自以為的創見,而做注釋卻要求你說完了還得指出是誰在什么時候在哪里說的。前者是犯罪,后者則是交代犯罪經過,故前者有發泄破壞的快樂,而后者有被審問及回憶的苦痛。
注釋是引進西方學術體制以后的事,中國古代是不講究注釋的。但若要藉此說中國古代沒有注釋的學問,則非知言也。在我看來,中國古代注釋的功夫大多體現在所謂的“小學”上,這里是廣義來說,跟校讎學、考證學、目錄學、版本學乃至傳記學、檢字學都脫不了干系,是章學誠在《校讎通義》里所謂的“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的功夫。所以說,中國古人的注釋是不跟在論文的屁股后面的,是一門獨立出來的專門的學問。因此,專門做文章的古人很幸福,他們無須去做注釋,文章寫得好了以后自然有后人挖空心思去做注釋,十三經注疏之類的東西不就是這么來的么?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國古書的神秘感,因為作者本身常常就寫得不明不白的,具有很大的解釋空間,再經后人出于各種目的的注釋,以及一些“莫名”但的確大感“其妙”的附會,中國古書的東西就莫衷一是,玄乎其玄了。
讀了兆明寫的《圍城之后》,90年代初“錢學熱”的時候,出現了一大批盜版的圍城,以及托錢鐘書之名寫的新圍城,還有就是像《圍城之后》這類續集型的作品。據說那時候,為了這事,以侵犯著作權、名譽權的名目,錢鐘書打了不少官司,兆明也是被告之一。最后的結果自然是《圍城之后》禁版了。所以現在要買這書殊不容易,上學期在舊書攤上無意間淘到一本,到現在才有閑暇來讀。
公允地說,作為普通的小說來看,這本書寫得應該也算不錯了,而且在行文上不像錢鐘書的風格,倒有幾分接近楊絳在《洗澡》里面的味道。但若是作為錢鐘書《圍城》之續編,則無疑是狗尾續貂了。我倒覺得這書更適合叫《圍城之前》,因為里頭的人物總還覺得尚未經過《圍城》中一番磨練,在感情與學識上均顯尚未成熟。
寫些跟名人有關的東西,最好是能跟名人“叫板”,似乎一直是很modern的事情。但兆明之類的不夠聰明的作者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對于真正的高手,遠遠地叫罵幾句是可以的,近些年來的“聰明”的作者們干的就是這類事情;而若要真的挑戰高手或與之過招,恐怕還需要勤加修煉一番。所以說,“叫板”也是要講究策略的。所幸的是,現在的人已經比90年代初的那些人狡猾多了,都很懂得策略,更何況,現在“高手如云”的情況下,“高手”們的質量卻大大下降了,于是,“叫板”的目標多了,難度也減小了。
漢語從單音節字發展到雙音節字,我們的學科似乎也隨之很識相地從形單影只走向了雙棲雙飛。如什么散文詩、文藝心理學、管理哲學之類的名目,讓人充分領會到漢語的靈活性以及漢語語法體系的flexible。
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研究》中,他以西方心理學的方法切入,得出一切嗜好皆出自人的權欲,故嗜好有雅俗但無高下的觀點。但在文末,靜安先生又提到,教育的目的即在使人的嗜好脫俗趨雅。
心理學因為其立足于人類共同之心理模式,而使人都趨于平等,而教育學相反,它往往可以通過后天的塑造把人推入不同的階級。所以,心理學是把人的衣服脫光,揭示每個人在裸體的時候都是沒有區別的;而教育學則是教人如何穿上各種衣服以遮羞與掩飾的。因此,教育心理學是一種尷尬的存在,它總要先把人的衣服脫光。再教人怎樣把衣服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