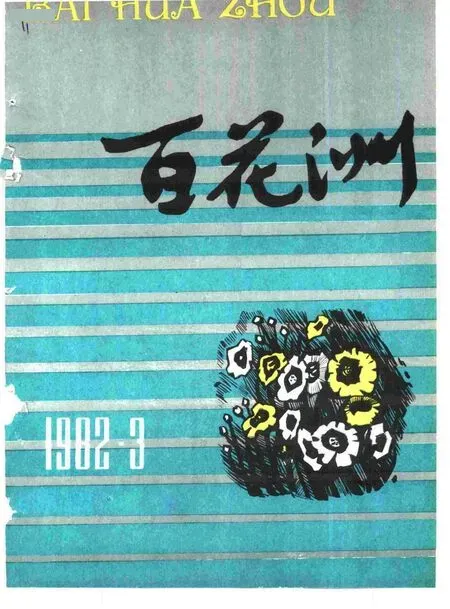親親我的桃(外二篇)
許冬林
初夏的時令,各色的水果仙子還沒有魚貫而入、齊整地列于水果攤前,桃暫且唱了回主角。
其實,櫻桃也是這個時候上市的。小小的,晶瑩剔透,宛如著紅裝的小家碧玉,沒有殷實的家底,故而嫁得早些,從濃密的枝上走下來,開始堂前庭外地待客理家。但這種水果只在山區丘陵里見得多,山泉里濯洗,綠篾籮里攤開來,盈盈的水光晃動。倘能一夕瞥見,回家隔了一夜,心底里還惦記著。只是在我生活的這塊江北平原,難得見的。
街頭巷尾也能見到荔枝,謠傳說是福爾馬林溶液泡過,遠遠地從火熱的南方過來的。于是翹著蘭花指,嘬著雙唇象征性地嘗兩顆,不敢貪多。像對異族的人,伸長脖子拿臉頰和人家的耳朵碰一回,作友好狀,其實心底里總要習慣地設上幾道防。
去年的蘋果在水果攤或裝潢考究的水果店里都能見到,但是,是再不肯買了。費了半天的勁削皮,一口下去,是酥松,又粉又面的那種感覺,可以當餅干了。那口感,是一位老太太在兒孫前兜露了千百回的往事,已經嚼不出零星半點的新鮮勁。于是故事聽不到一半,各自撒歡去了——垃圾桶里總有吃不掉的大半個好端端的蘋果。
這樣一琢磨,就挑桃了。
桃和櫻桃一樣,都屬于平民家的水果,沒聽說有吃不起桃的窮人。住在平原上的人家,宅前屋后多半有一棵或幾棵桃樹。春天里路過,遠遠看見一大團燃燒著的粉紅的火,近了,人從花下過,百轉千回,還是掐了一枝走。主人家走出來,脆生生甜蜜蜜地叮嚀一句:夏天來吃桃啊!于是當真惦記著,當真在夢里千百次回眸。夏天也當真來了,自己伸手摘,拿到水邊搓一搓軟軟的桃毛,再坐到樹底下吃,偶爾和主人家話話桑麻之事。桃讓你和一些最平凡樸素的人走近,親著。
也有玲瓏的小媳婦,或者面善喜笑的阿婆,扁擔上歪斜地勾著兩支竹籃,里面是新摘的桃,肥嘟嘟,新嶄嶄,像剛被關進教室的一群小學生,憋著一肚子的嘰嘰喳喳,里里外外都是新下枝的鮮嫩。這樣的桃,只管放心地買——自家的桃挑出來,無非是,阿婆為著農閑牌桌上的手頭活絡,小媳婦大約惦記著街角某個鋪子上的一塊花布料。蕓蕓小民掐指過日子,在屬于平民階層的桃上可見。
鄉間的桃,離人近,抬眼可看,伸手可摘。鄉間的桃,握在手里就想起春風,想起那一枝桃花綻放在哪一場春雨里,想起哪一天花瓣零落,哪一天果實成形。你是這樣熟悉它生長中經歷過的一花一葉,一枝一節,像一對青梅竹馬深諳對方的歲月在自己的心底覆了多少層。像胳膊上枕了三十年的那個人,沒什么心下轟然的初見,沒多少觸目時的新奇,可是里里外外都是親。與它相對,心安,實在。不像面對超市商場的保鮮柜里的名貴水果,看它擺在精巧的小盤里,蒙上保鮮膜,貼上標注著品名產地重量價格的標簽,在幾百瓦的節能燈照耀下泛著誘人的光。柜臺前流連,像迎接遠道的貴賓,場面奢華,心里戰戰兢兢。這樣的水果,至多偶爾買買,滿足好奇,或是給家里的水果盤子裝一回門面。能愛得久的、放心去愛的,還是手邊竹籃里的桃。體己,隨心,坦然,沒有拼命攀一個階層所遭受的疏離之苦。
初夏去小鎮上買桃,沒有陳貨,新鮮就放心好了。圍著圓圓的大竹筐蹲下來,一個個青的紅的半青半紅的桃像小腦袋在手心底下翻跟頭,濃眉樣的綠葉子還嵌在里面助陣。咬一口,山歌似的脆,泉水似的純。鄉人賣桃都是當天的桃當天賣光,完了再回去摘。來來去去的路上沒有冷庫,沒有精明饒舌的水果批發商。那桃的身世清清白白,干干凈凈,沒有隱瞞的婚史前科,沒有一身抖不清的舊帳。它是平民家的子弟,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沒有占據幾張紙的豪門陳規。它不招人,不惹眼,不像陳年的蘋果,能面不改色地熬過一冬,依然沒落貴族似的鮮紅著。它就那樣真真實實地新鮮著,脆嫩著。
桃似你身邊平凡的親人,是你命里來得早或走得遲的人,他沒有財力,沒有頭銜,可是幾十年你蹭著他的胡碴,聽著他的呼嚕,與他安靜相守在鍋碗瓢盆里。
桃更似你不示顯赫,不事張揚的平民生活姿態,不仰視權勢,不附和權威。摒棄了臺上浮華的光與影,藏身于萬人如海的寂寞謙卑里,懂得去禮贊陽光,空氣,水,還有泥土……
人在黃梅天
人在鏡子前,聞到綠豆湯的香。也不全是綠豆,還摻了些百合,細碎的苦,隱約在齒舌之間,走走停停的樣子。中醫里,百合是治咳的一味妙藥,也可久久地食用。身有一小疾,時聚時散地糾纏了多年,也不甚礙事,但也記得時時煮那白月牙樣的一瓣瓣小百合。像棄了貧賤的舊相好,嫁進豪門的婦人,縱然一朝安逸,心里終是不安,年年月月還記得把那錢物迢迢地寄去,安撫著。
也只繞了個簡單的蓮蓬髻,放下梳子,不修眉,不上妝。
端起白碗,嘬著小口,吹開一片浪,湯匙來來去去地撈著,權當是仲夏采蓮的船。一碗綠豆百合粥見底,天就熱起來。玫瑰紅的旗袍已經有點纏人,像熱情的初戀男女,膩得叫人的心底生出幾分厭來,只是尚還能受得住,那分惱人還未到唇邊。
窗外才九點鐘的香樟樹上早擠滿了單調的蟬鳴,鋪路石子樣的粗糙,祥林嫂似的一遍又一遍,沒個了時,叫人厭煩。上午的天氣和人較上了勁,卻又不動聲色,窗子開著關著都是悶。也知道不關窗子的事,這是黃梅天了。墻角潮潮的,擦不干,而陽光,明明在曬著窗臺。這天氣,像分頭而睡的一對老夫妻,各自絮叨著,多年的不呼應。撥弄窗子的人也潮潮的,只覺得有千萬只手臂勒抱著,掙脫不去,力氣都用在了喘氣上。想到浴缸里泡個涼水澡,打開衣櫥,滿眼的姹紫嫣紅,可是兩根手指捏不出一件來,新的嫌新,舊的嫌舊。
一塊牛奶糖,在桌角,也軟了,白白的一攤,沒保住自己的矜持。像旋風中的女子,剛蹲下身捂住了裙擺,結果低胸的領子又泄了上面的春光。所以,這樣的時候,是拒絕和朋友見面的。黃梅天,燥熱像無處不在的泥,刷得人面目模糊。涂了粉底和胭脂,一張小臉梨花白桃花紅地艷著,怕一路上,出了汗,像個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的末路英雄。然后躊躇著在門外,再也不敢推開門,抬頭迎接圍了一桌子的面孔。所以,我的淡漠,我的孤僻,愿它像畫著殘荷夕照的屏風,曲曲折折地立在陰暗的深宅里,遮住了后面一張俊俏含著煙愁的面孔,一根裊裊的辮梢,一雙繡花的鞋子。
午后的時光是慵懶的。當有一爐香,一壺茶。竹搖椅的枕上,發有三五分的亂,亂發的底下是泛黃的紙,泛黃的紙上是平平仄仄的句子。眼閉著,夢做著,人是醒的。涼了的茶喝了一半,水沒續上。
料定會有一場雨,果然。蓮蓬髻歪在右耳邊,不及梳,俯在窗臺邊,由著風從指間過。想著,天上也一定住著一對夫妻,打雷的是老公,下雨的是老婆。男人嘛,火氣大;女人么,淚水多。雷聲和雨聲糾纏到黃昏,做丈夫的漸漸沒了聲音,只剩下連綿的雨在窗外,像掩了房門,俯在梳妝臺上的嚶嚶啜泣,間以點點滴滴的數落。
午后三寸雨,浮生一日涼。難得。倚著窗兒,是拂面的晚風,像美人的裙裾在半空里翻飛,看得見的清涼。轉身,謀劃晚餐。
想起一個淺淺交往的女友,人長得漂亮,卻受不得朝九晚五上班的辛苦,更不屑牛奶尿
布拖把菜刀的瑣碎,她的過日子,就是走馬燈似的換男朋友。三十多歲了,還能花開幾度草綠幾茬呢?她離美麗也許很近,離生活,卻很遠。回頭看自己在切得薄薄的白藕上撒糖,忽然想起,自己這一天的庸碌和瑣碎,后面,還是甜的。
蟬聲歇,蛙聲起。總算是涼了,好人眠的。
后半夜的月,從西邊的墻頭上,斜斜地出得港來。像妙齡的寡婦那張清白瘦削的臉,從房舍到樹林,到草地,到小河,一路寂寂地走著,目不斜視的樣子,是圣潔又孤獨的靜。
前半夜雨,后半夜月。一日的浮躁,煩悶,糾纏,辛苦和瑣碎,都化作了這一刻的澄明恬靜。而我,在這樣的夜,成了被內在的清明和外在的安靜養著的女人。像青灰色的磚墻后面那個舊陶罐里,盈盈的一捧清水養著的盈盈的一彎皓月。
是是非非的吐絲
江南養蠶人是要把蠶稱為蠶寶寶的,可見其愛。聽說,蠶的壽命通常也就是一個月多一點,心里悄悄疼了一下。也聽說,江南人在蠶吐絲的那段時間里,家家戶戶都閉門謝客,惟恐有一點點的喧嘩,驚了這寶寶,它就不吐絲了,它太膽小。于是聽人描述的時候,也不敢出一點大氣,感覺吐絲是那樣一個羞怯,神秘,玻璃般玲瓏易碎的過程。像在月光下的樹林里看天上的仙女在人間沐浴,只能向往,只能朝圣般俯首閉目地安靜,是不能走近的。近了,神話就碎了,碎成一地冰冷的月光。
讀李義山的句子: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知道“絲”是諧音“思”的,知道這是千古流傳的愛情盟誓。便以為,春蠶吐絲,只是一場從生到死一點不打彎的癡情。蠶是生而為吐絲的,日日夜夜的吐絲在一寸一寸耗盡蠶的生命——自從和某個冤家相識,從此一生便耗在了對那人的無盡的思念中,不問值與不值。如此,蠶的吐絲是深情的。
后來,這深情有了更廣泛的外延。所有在平凡崗位上默默奉獻自己熱血青春乃至生命的人,都成了一只吐著絲的春蠶。教師,醫生……那些吐絲人的名和姓,年年月月總要占據幾回頭版頭條的位置。春蠶吐絲,這一次從廂房里牽出來,穩穩端坐高堂上,享盡饒舌的謳歌。
看到“作繭自縛”四個字,心頭忽然就一陣麻。揚名了幾千年的吐絲,忽然之間,吐絲就成了罪孽。還要遭人恥笑一一迂腐,頑固,不識時務,不明事理。文字里的蠶的命運,竟也這樣顛沛流離。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知識分子,還是那樣的名和姓,還是低頭在做著學問,忽然名字就寫在墻上,上面還打著叉。王孫公子,貴婦宮妃身上的綾羅綢緞,怎就忘了呢?順著常人的目光看那“作繭自縛”四個字,想那吐絲竟是用情極深,可惜用錯了地方,便成了無謂的糾纏。吐絲一事,當初的神秘,崇高,威嚴都沒了,像王子落難民間,賤了賤了,還躲不過萬人的恥笑。
在蘇州第一絲廠看見一個女工剝開了一個繭,里面躺著相對而抱的兩只蠶,心底溢出四個字:低調的愛。內行人解釋說:不是所有的繭都可以理出絲來,大的繭里是兩只蠶同時吐絲,絲頭就亂了,只能用來做蠶絲被。于是動情地想:這兩只蠶淡泊名利,無意于身后的絲是否走進華堂,披在貴人身上。只要兩個生命能終生抱在一起,我的絲纏著你的絲,一輩子在這座巢里不出去就好。至于做衣還是做被,那是身后的事情;貴還是賤,成還是敗,也由外人說去吧。抱定了一生不棄的,像《胭脂扣》里的梅艷芳和張國榮,約定了為愛一起去死,縱然一個暫且留下,另一個化作一縷冤魂,也要折回來尋他。
如此,回頭看那功成名就的一只蠶吐的絲,就覺得它太寂寞了。成就了綾羅綢緞,人前有了奢華,背地里,少了多少歡愛。
唉!這個季節,江南的蠶寶寶正在低頭咀嚼自己的桑葉吧。年年月月,它依然在忙著吐自己的絲,做一只蠶能做的事。是非曲直,只是他人口里的無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