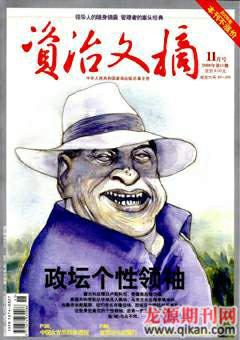土地制度改革提速
程 默
進入2008年,關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探索驟然提速。
4月9日,來自安徽省建設廳的消息稱,安徽省將建立并實施農民住房產權登記制度,農戶獲得建設部門發放的房屋所有權證后,有望以農村住房作抵押獲銀行貸款。4月15日,在抵押擔保問題上,浙江省表示計劃根據農民住房特點和銀行抵押貸款的條件,在城鄉結合部的農村地區試點農房抵押貸款。5月19日,山東省政府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促進就業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農村金融服務機構要拓寬農戶小額信貸和聯保貸款覆蓋面,放寬貸款條件,降低貸款抵(質)押標準,創業人員的房屋產權、土地使用權等均可作為抵(質)押品”。
地方政府的改革,從某種程度上也促使中央的態度變得更為積極。6月,國土資源部有關負責人在談到新一輪《土地管理法》修改時指出,最核心的改革可能是在農村集體土地財產權實現的形式和制度上的改革。7月,國土資源部要求,各地應“力爭在2009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國宅基地使用權登記發證”。
但是,按照目前頒布的《物權法》和相關法律,農村宅基地只能在村集體內部流轉,尚不允許城市居民或外村人購買,也就是說,農民的宅基地和土地不能進入市場交易,也沒有獲得抵押貸款的資質。同時,相應的房屋權屬登記系統也極為滯后,缺乏進入市場的技術支撐。

在中央的法律環境還沒有提供保障的背景下,如何解釋地方政府如此密集的土地制度“創新”行為?如果我們把視野拉寬,放在中國整體的經濟和分稅制背景中,就不難理解地方政府的良苦用心了。
土地、房市與政府
當前,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性很大。隨著房地產市場泡沫開始暴露、土地流拍的事件頻頻發生,在土地收入預期不明朗的背景下,高度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開始試圖激活壓抑多年的農村土地“死產”這個“價值洼地”,就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過去房地產行業屯地現象嚴重,今年年初頒布的《國務院關于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明確,土地閑置滿2年的,依法應當無償收回的要堅決予以執行;而土地閑置滿1年不滿2年的,按出讓或劃撥土地價款的20%征收土地閑置費,尤其是對閑置土地特別是閑置房地產用地要征繳增值地價。
8月6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經濟述評稱,目前無論從宏觀經濟形勢、政策層面還是需求層面,都不支持房價持續高漲,“房地產的暴利時代已經終結,在長達10年的房價上漲之后,中國房地產市場開始向理性回歸”。國家統計局還認為,國內樓市上漲至遠離其基本價值,遠超國民的消費能力,其價格最終回落將成為必然。
8月26日,央行和銀監會聯合下發《關于金融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下稱《通知》),《通知》規定,嚴格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金融機構禁止向房地產開發企業發放專門用于繳交土地出讓價款的貸款。對國土資源部門認定的建設用地閑置2年以上的房地產項目,禁止發放房地產開發貸款或以此類項目建設用地作為抵押物的各類貸款(包括資產保全業務)。央行與銀監會聯合下發的《通知》,正是對《國務院關于促進節約集約用地的通知》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具體化。
但是嚴重依賴土地財政來滿足本級政府開支運營的地方政府,盡管沒有旗幟鮮明地跟中央唱反調,不少地方卻已經默默開啟了“救市”之旅。
5月6日,河北省建設廳宣布,河北省將建立住房公積金中心與房地產開發企業合作的貸款合作機制;將住房公積金貸款上限從30萬元提高到40萬元;開拓住房公積金個人貸款異地買房業務。此舉不但會刺激當地購房需求,在信貸收緊的情況下,開發商還可以轉向住房公積金處獲得一定的資金支持。
7月中旬,江蘇國土廳網站刊登了一則由南京市國土局提供的“新聞播報”:市國土局“采取有效措施促進土地市場平穩發展”,將出讓的土地規模從原先的200畝左右降低到100畝以下,有土地的土地出讓金付款期限被延長到一年。
同月,長沙市人民政府近期就出臺了《關于促進我市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意見》細化到將交易稅調整為1.1%;多項房地產稅費減免或延遲收取;以及公積金貸款首付降為20%。這些從土地、金融、稅收以及開發報建等各方面提出的優惠政策,被長沙業界看為旨在增強樓市消費信心。
7月下旬,在聽取了《上半年蕪湖房地產市場運行報告》,以及多家房地產商的“感言”之后,蕪湖市副市長洪建平明確表態,“政府將積極聽取各家開發企業的意見和建議,并采取相應措施進行調整”。近期被列入蕪湖市政府調整范圍內的,就有“調整一手房和二手房交易中的相關政策”,“調整住房公積金貸款政策,激活銀行現有資金,同時鼓勵二手房上市交易”等等。
這種曖昧的調整說明,土地政策已經出現了實質上的松動。而支撐地方政府這么做的最大動力,則是地方財政高度依賴土地財政這一事實。
土地財政綁架地方政府
與2007年“地王”頻出的喧囂相比,2008年的土地交易市場多多少少顯得冷清。來自國土資源部的全國城市地價動態監測系統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土地有接近50%都是以底價成交收場,更有10%左右的土地遭遇流拍流標。以北京市為例,6月份北京住宅用地僅成交了1宗地,整個二季度共成交土地11宗,即使和一季度的35宗相比也下降了300%。
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2008年一季度,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上漲11%,土地交易價格上漲16.5%。二季度房價同比上漲9.2%,漲幅比一季度下降近兩個百分點,土地價格漲幅回調則更加明顯,雖然土地交易價格同比上漲10.8%,但相比第一季度漲幅下降了5.7個百分點。
這種局面不得不讓地方政府大幅下調2008年的土地出讓收入預期。深圳市政府將今年的國土資金收入預期大幅降低到154.33億元,比去年215.6億元的實際收入下降超過60億元。而土地出讓金,基本上已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一塊財政收入。
有資料顯示,2007年房地產商交給政府的土地出讓金超過1萬億元,而當年地方財政總收入不過2.3萬億元。再加上房企的營業稅、土地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地方財政已“退化”成名副其實的土地財政,地方政府已經退化為“房地產商的附庸”。而地方政府是怎樣走到今天這個困局,則必須要從分稅制說起,因為分稅制正是土地財政的根源。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至今,一方面,中央把財權高度集中,在稅收分享上降低了地方政府所能取得的比重。收入來源穩定、稅源集中、增收潛力較大的稅種,幾乎都被列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如地方工業增值稅的75%上交中央政府,另外的25%留給地方。但另一方面,中央在收繳財權的同時,卻把更多的事權層層下放給地方,把財政支出責任推給地方。在地方財政收入比例沒有明顯變化的前提下,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卻逐步走高。
也就是說,在分稅制改革中,中央政府一方面把財權上收,另一方面又把公共品供給的大部分責任作為政治任務“承包”給地方。當地方政府的本級財政收入不足以平衡財政支出的時候,為了滿足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維持龐大的行政機構的正常運轉,地方政府就只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尋求中央的轉移支付,即我們經常看到的“跑部錢進”,另一個則是謀求非稅收入,把增加GDP、稅源、土地出讓金作為頭等大事。
由于并沒有承擔與財權相對應的事權責任,中央也默認了地方的一些自收自支行為、甚至不規范的收入追求行為,由此導致了中國預算外收入迅速增加。這其中,土地出讓收入變得越來越重要,有不少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這就是為什么許多地方政府都在打著土地的主意,并變出花樣抬高地價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最新取向也讓地方財政收入雪上加霜。
根據有關媒體披露,財政部財科所的方案認為,為了加大中央平衡地區間貧富差距的能力,所得稅最好改為中央稅。現在所得稅實行中央地方按6∶4比例分成。2007年,中國企業所得稅收入7723.7億元,個人所得稅收入3185億元,合計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26.2%。同時,適當考慮加大增值稅地方分享比例。很多地方政府提出從目前的75∶25,調整為50∶50、60∶40等分配比例。
發改委宏觀院的方案則更為大膽—它建議把增值稅全部改為中央稅!增值稅現為中國第一大稅種,2007年全國國內增值稅收入高達15609.9億元。增值稅也是地方稅收收入僅剩的最主要的來源,通常占地方稅收收入一半以上。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的最新財稅體制改革不僅沒有朝著“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的方向演進,反而在“強干弱枝”的路途上越走越遠,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的缺口將進一步擴大。
發現農村“價值洼地”的意義
面臨如此大的收入壓力和資金缺口,對于地方經濟,釋放“凍結”的農村土地就成為一個值得嘗試的辦法。而從基本經濟原理上看,隨著城市化的發展,農村土地進行流轉和交易有迫切的現實需要。
2007年,中國人口約13億,城市化率約45%,根據政府相關規劃,到2020年,中國總人口約14.6億,城市化率將達到55%。按照上述數據測算,2007~2020年,大約有1.7億的城市新增人口,按照通用的每個城市人口占用100平方米的土地計算,約需要170億平方米的土地,即2550萬畝土地。如此澎湃的城市化進程和龐大的新增用地需求,自然需要農村土地作支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在農村調研中發現,農村普遍存在一些傾向,如把整個農村納入城市建設規劃區,把農村集體土地全部轉為國有土地;或者隨意改變土地產權關系,“拿土地換身份”、“拿土地換社保”。類似的情況,在近年高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中大量存在,其結果是房地產商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而農民則成為最大的輸家。
從農民角度看,目前農民發展農業生產有大量的融資需求,卻因為沒有抵押物得不到信貸支持。
《IT經理世界》對陜西佳縣的一份調研資料顯示,截至2008年5月末,佳縣金融機構存款總額是6.08億元,其中農村信用社2.8億元,農業銀行是2.3億元,郵政儲蓄8828萬元。分別占比47.84%、38%和14.52%。可是在3.7億元的貸款總額中,信用社2.8億元,占75.96%,農業銀行是8433萬元,占22.67%,郵政儲蓄510萬元,占1.37%。
也就是說,信用社用47%的存款放出了75%的貸款,占整個貸款市場的3/4。另外的1/4中有絕大部分已經像抽血一樣被農行抽走,資金嚴重外流。
這是一個農業縣的金融服務全貌:機構3家,信用社作用是正面的,但根本無法全面覆蓋;農行現在基本上只存不貸,作用基本上為負面;郵儲銀行剛剛起步,還在探索階段。而且郵儲目前能提供的貸款也都是質押貸款,意義根本不大。
佳縣樣本典型地反映了當代中國農村金融困局:一面是可以再放大數倍的資金需求,一面是供給渠道的單一;一面是需求的多層次性,一面是金融機構政策的一刀切;一面是農民對于小額資金的需求,一面是正規金融機構的“嫌貧愛富”……
因此,激活壓抑多年的農村土地“死產”這個“價值洼地”,無疑將釋放出巨大能量,并隨之帶來信貸擴張、投資和就業增加、GDP增加等等一系列地方政府所樂見的現象。
而事實上,激活農村土地價值更大的意義在于,地方性的這種制度探索或許為全國性的農地改革提供了范本。目前中國農民最值錢的資產有兩個:一是農地承包權,一是宅基地使用權。依照《物權法》,這兩個都被定義為“用益物權”,也就是說,事實上就是農民的財產。但是目前現行法律卻規定兩者都不能抵押,事實上等同于限制了農民的財產權利。
從這個層面上講,地方政府的積極實驗,很可能成為難得的創新之舉。
例如,為了解決房產拍賣后的“執行難”和土地使用權的“變更難”,溫州市法院和國土部門聯合發出《協助人民法院辦理集體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暫行規定》。該文規定:抵押的“農民房”經法院作為被執行物處置(拍賣)后,可直接辦理農民集體土地使用權的變更登記。這就從“終端”上解決了“農房抵押貸款”的法律障礙,使之頭尾打通,在實際上認可了“農房抵押貸款”。
安徽省的做法是,一旦銀行實行了抵押權,可能會把該農村住房出售以收回貸款。按照受讓對象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情況:如果是本村農戶受讓住房,按照現行土地管理的相關法律,該住房及宅基地產權隨之轉移;如果是城市居民受讓該農村住房,房屋所有權變更后,相應的宅基地應依法由集體所有變為國家所有,由受讓人享有土地使用權。
這樣看來,釋放農村土地“價值洼地”,即便不是地方政府不遺余力推動農地抵押貸款制度的最大動力,但它更大的意義則在于其衍生的一個“副產品”—為全國性的農地改革提供范本,從而在客觀上推動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根本性變革。
(摘自《南風窗》200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