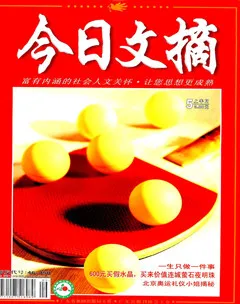雪寒心暖
那個時候,我和她都在當兵。因為彼此的部隊相隔將近一百公里,見一次面十分不易,所以,我們都很珍惜每一次見面的機會。哪怕我出差路過,她也要千方百計趕到火車站,在車窗前說幾句話。
有一年下大雪,整個冬天,東北的大地都是白的,積雪慢慢被壓成冰,厚厚的,要到第二年5月才化。那時正值12月,雪下得很大,對面幾十米看不清人。這時候,她打來電話,電話機是手搖的那種。外面刮著大風,電話里面好像也刮著大風,噪音嘶嘶地響。她說的大概意思我聽懂了:有一輛送黃豆的汽車到我們這兒來,她正好休息,想搭車過來看我,卸了黃豆就回去。這么大的風雪,如果路上有意外怎么辦?冬天路滑可是常出事啊。我不讓她來。卸車頂多一個小時,然后馬上回去,就為見這一個小時的面,來回要坐六個小時的車,值得嗎?我對著電話筒大喊,要不她聽不見,她也大聲喊,要不我也聽不清,就這樣,話筒里的聲音仍然像蚊子叫似的。喊著喊著,電話斷了。
對著漫天大雪,我心急如焚,從她那兒到這兒差不多要三個小時,我苦苦守候著。眼看快到點了,我站在院子里等她。我想好了,見面后非訓她一頓不可。車過了好半天才到,滿滿的一車黃豆蓋滿了雪,駕駛室里沒有她。我以為她沒來,于是松了口氣,駕駛員卻說:“她來了,在車廂里面呢,剛出來沒十分鐘就說暈車,只好讓她去車廂,這么遠,活受那個罪干什么。”我飛快地爬上車,撥開蓋在上面的積雪,見她蜷縮在裝黃豆的大麻袋堆里,快凍僵了,臉色白得像張紙,只是眼睛還在轉。我心疼地喊著說:“你呀你。”我伸手去拉她,她連張開手臂的力氣都沒有了。我把她緊緊地抱在懷里,她喃喃地說:“你等急了吧……”那時候,我的淚水不知不覺地涌出來。
結婚快二十年了,不論我們之間為瑣事爭吵過多少次,只要想起當年的那一幕,心頭便刮過那漫天的風雪,風雪中的小人兒清清楚楚。我的心便柔軟起來,好像觸到了一生中最溫暖的時光。■
(沈雋薦自《東方煙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