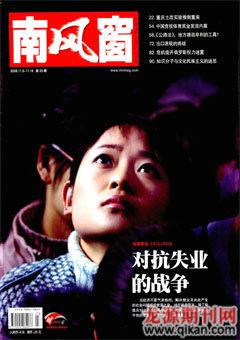管制文化亟待改造
趙 杰
在監管者與監管對象共同面對一個不斷擴張的市場時,必須在公開、透明、公眾參與、法治嚴明的環境中加強監管。否則,我們就會出現“事故頻發—加強監管—監管制度苛嚴—監管環境更加封閉—事故隱患更加難以暴露—出現更加嚴重的事故”的惡性循環。
9月,各地因安全事故、食品衛生事件,共免去19名瀆職高官職務,其中最高職務為正部級。有因承擔領導責任而引咎辭職、有因“負有領導責任,對事件未及時上報、處置不力負有直接責任”而免職。到了10月份,又曝光了幾起事故瞞報事件。
在上半年結束的多個部委參與的“安全生產百日督查行動”結束不久,卻通過事故頻發與官員去職來展現“行動”成效,不得不讓人對“百日督查行動”的實際效力打個大問號,對“百日督查行動”這類政府監管行為的內部封閉運行的弊端察之一二。
近些年來,政府管理者的思路是,哪個部門出問題出事故多,就加強哪個部門的力量。這種思路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實際運行中,這種“加強”往往只是一些人力、硬件、權力上的加強,而沒有對其法治化程度、監督機制、責任追查機制進行很好的梳理,缺乏對管制權力的法治化、公眾化約束方面的加強,缺乏對“管制者——管制對象——社會公眾參與”這個管制系統的機理、機制的研究和突破。
越“狠抓落實”,越難落實
檢索一下國務院辦公廳今年4月開始的“安全生產百日督查行動”的相關新聞,不難發現,各級政府部門都對這一文件進行了一字不漏的“轉發”,文件的宣傳可謂及時到位。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一級政府或者監管部門,在新聞媒體上披露過任何一次督查的結果。也就是說,督查是在老百姓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老百姓根本沒有機會也缺乏動力和激勵,向有關部門舉報身邊的安全隱患。而事后安全百日督查情況的體制內循環,也無法讓老百姓的“火眼金睛”發揮監督作用。

而另一面,我們的政府管理似乎總是面臨“落實”難題。整個中國行政體制規模浩大、機構林立、文件會議眾多,無奈的是,絕大多數這類行政資源卻都是圍繞著“落實”、“抓落實”、“狠抓落實”、“建立長效機制”在運行。當前政府管理的確具有缺乏章法、有令不行、回應性不夠的一面。但是,像安全生產、價格監督、城市管理這類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要么缺乏公眾參與政府管理的渠道,要么公眾參與流于形式,要么公眾參與成本過高。個中原委,令官場內部人士也感到汗顏。聯想到,10月8日,山西省公布山西省16個廳局安全生產舉報電話。同日發布的《關于集中開展煤焦領域反腐敗專項斗爭的意見》也提出:“深入查處煤焦領域及非煤礦山領域的腐敗案件,望廣大干部群眾對掌握的問題積極舉報。”筆者不禁擔憂,舉報電話對遏制安全生產和煤焦領域腐敗現象的效力。
簡而言之,仍然用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來處理新的經濟活動帶來的外部性,必然出現管理理念不科學、管理流程不匹配、管理獨立于社會公眾之外封閉運作、管理績效差的問題。經濟學上有一個“管理者被俘獲理論”,說的是被管理者天然有收買管理者的利益沖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應該是貓和老鼠的關系,如果不對這種關系進行強化,那么管理者隨時可能被“俘獲”。
事實也證明,來自政府的物質、物力、級別、硬件的“加強”,遠遠比不上來自“煤老板”、“舞廳老板”等的市場力量“公關”的力量大。三鹿奶粉事件早在3月份就已經露出苗頭,為何能一再被瞞報?深圳“舞王”出事前,有關部門剛對該地區進行過兩次安全排查,而“舞王”居然不在名單上。如果不能從公眾參與政府管制的角度,對這個將細節放過(而恰恰細節之中就有“魔鬼”),最終釀成大禍的管制環境(包括責任人、管理體制),進行系統性的改造,貓和老鼠的管制難題,就仍然深深扎根在我們的政府體系內部。隨時,都會有安全事故光臨。兩種政府管制類型的扭曲運行
全國安全事件高發的態勢不僅沒有被控制,反而更加惡化,說明單純寄望一個問責制常態化、而不改造我們的管制理念、管制流程、管制環境,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各種安全事故規律性的爆發,說明我們的社會性管制存在體制性漏洞,不適應市場發育后的管制環境的新變化。管理不科學是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而絕非特定的領導者失職瀆職、基層小吏被腐蝕被拉攏那么簡單。這是個政府管制的新課題,單靠問責制局部的“點”,無法解決全局性的管制績效問題。
按照現代政府管制理論,政府部門主要承擔兩種管制:一個是經濟性管制,即對水電氣、火車票地鐵票、部分藥品等的價格管制;一個是社會性管制,主要管理經濟活動帶來的各種外部性,尤其是負的外部性。像礦難、火災、食品衛生事件等都屬于經濟活動帶來的負的外部性。
官員責任追究方面的不留情面,主要發生在社會性管制領域。通過高官行政免職,雖可看作對過去安全生產管理體制在領導責任追究機制建設方面的一次痛心疾首后的“亡羊補牢”,但是混淆高官個人、領導責任與監管機構的體制性責任,用局部官員個人行為失范來遮蔽、矮化監管體系的系統性責任,用大批量的官員行政懲戒來替代監管流程再造,不觸及和動搖事故頻發的體制基礎,仍難絕斷管制漏洞對公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威脅。
電話舉報等公眾參與方式,雖說是一種低成本的安全監管形式,但要發揮其作用,仍需政府管理部門轉變管制理念、創新管理方式、追問管理績效。一句話,公眾參與政府管理,需要政府部門改造管制文化,提供公眾參與的“制度接口”,使得公眾參與管理成為政府日常管理的“千里眼”、“順風耳”。事故頻發的當月,不少人用常態化、長效機制建設來冀望健全未來的安全管理機制和問責機制;在事故處理高峰過去一個多月之后,筆者更愿意用改造我們的管制文化來認識當前這場問責風暴,更希望高層在強化企業是安全生產的責任主體不動搖的前提下,同時探索一條強化管制者監管責任的新路,來走出管制困境。
其實,經濟性管制領域的失范,更是導致社會民生問題突出的一個重要原因。經濟性管制的理由在于自然壟斷行業(供電、供氣、供水、供暖等公用事業)長期平均成本遞減,由一個壟斷者經營更加有效率。但是這種自然壟斷特點是由其網絡經濟屬性而非經濟競爭過程決定的。所以,政府授予特定企業、組織經營自然壟斷行業的特權,同時為了社會公共利益,對其服務價格進行管制。我國《價格法》第3條第1款規定:“國家實行并逐步完善宏觀經濟調控下主要由市場形成價格的機制。價格的制定應當符合價值規律,大多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極少數商品和服務價格實行政府指導價或者政府定價。”
根據《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的規定,列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的藥品,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以外具有壟斷性生產、經營的藥品這兩類藥品實行政府定價或者政府
指導價,其他藥品的價格一律由市場調節。我國新藥層出不窮,一年曾有10009種新藥,就反映了藥廠影響價格部門獲得新藥資格認定,從而可以將普通仿制藥包裝成新藥高價出售的“行規”。正是通過新藥審批,“新藥”的利潤空間、流通費用和回扣空間變得巨大無比,以藥補醫的體制才能大行其道。
政府管制與市場力量的博弈
市場發育與政府管制是兩種交叉影響、相互牽制的力量。強化管制、放松管制、簡化管制,都是針對市場發育的不同狀況,改善管制效率的不同方式。面對市場發育初期、市場競爭不充分、競爭者數目較少的市場,制定一定的門檻和經營標準,是該階段政府管制的主要特征。面對市場發育不斷深化,產業的技術、資金約束壁壘不斷降低的市場,通過簡化或放松管制,能夠鼓勵更多潛在的市場競爭者進入市場,從而增進市場效率,降低產品和服務價格。
不同行業、不同產業的不同階段,都對應著不同的競爭狀態。站在政府管制者角度,針對競爭狀態,調整管制強度,有利于提高管制效率;站在市場力量角度,競爭者誘導、影響、“俘獲”(甚至是威脅、“綁架”)政府,通過形成有利于己的管制政策,排斥打擊市場競爭對手和潛在競爭者,最大限度獲取“消費者剩余”,也是市場競爭的一種變異方式。
不斷擴張的市場規模,一方面對市場管制政策的調整提供激勵,另一方面也對傳統競爭格局及其慣性運作提供激勵。兩種激勵是“針尖對麥芒”的反向力量。迅猛發展的市場需求,充沛的產業投資密度和豐厚的產業利潤,足以支撐日益龐大的政府監管部門的運轉。市場發育的廣度拓展和深度挖掘,又會孕育龐大的中介、灰色的“潛規則”、“服務”鏈條換得市場發展的良機。但這種由市場發育及其附著的經濟利益推動形成的監管,注定是“貓鼠共存”的監管模式。

在這種政府管制與市場力量勢均力敵、不相上下的領域,若是簡單憑借出于“公益心”來加強政府管理,局限于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增加執法檢查的頻率,加大懲罰金額額度,卻忽視政府管理的公開化、透明化,公眾參與的法治化、便捷性的話,往往會適得其反:加強監管,只不過抬高了市場力量拉攏腐蝕政府監管部門的成本,加強監管甚至成為利用社會心理和法律法規手段擴張部門利益的義正詞嚴、冠冕堂皇的借口。在監管者與監管對象共同面對一個不斷擴張的市場時,必須在公開、透明、公眾參與、法治嚴明的環境中加強監管。否則,我們就會出現“事故頻發—加強監管—監管制度苛嚴—監管環境更加封閉—事故隱患更加難以暴露—出現更加嚴重的事故”的惡性循環。加強監管,就會淪為加強監管者權力,就會流于拉長監管鏈條,就會停步于監管者內部的監管文件、會議、匯報和檢查。監管的結果就局限于為監管體系內部掌握,少數人掌握。監管的真實性、完整性、公正性會受到質疑。否則,怎么會出現,兩次安全生產大檢查,深圳舞王歌舞廳都榜上無名?因為,監管者排除了對無照經營企業的查處。而無照經營方式成為發達地區非法生產企業幫助監管機構回避和逃脫監管職責的一種制度安排,也就不足為奇。
企業和社會管制部門是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如果只強調企業的安全生產責任,而忽視政府的監管責任,這對矛盾還是無法解決。從南丹礦難、松花江污染事件以來,社會各界對“企業是安全生產事故的第一責任人”這一理念可謂充分理解了。2006年,發改委等三部委印發了《關于強化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嚴格安全生產業績考核的指導意見》。對企業的安全生產責任進行了規范。但是對政府的監管責任,尤其是日常監管責任,還缺乏法規規范。通過一些部委網站,我們發現,中央加強監管能力建設的資金,更多地是被拿去添置計算機系統、人員培訓,而相應的法治化建設和群眾參與機制、行業協會參與機制卻只字未提。貓抓不到老鼠,并不是因為硬件裝備跟不上,最重要的是要明確、強化管制者與違法違規者之間的“天敵”關系,強化對這種對立關系的社會性監督。
問責風暴對公眾參與政府治理的啟示
目前的問責制有很大缺陷。首先是管理手段超越了管理目的,罰款、檢查超越了查疑、補漏,寓管理于牌照發放之中,寓管理于資格審查之中,寓管理于管制者內部“一手遮天”之中。問責文化停留在事故發生后,沒有在整個政府活動全過程扎根。
但是,9月份的問責風暴,突出的意義是,一方面強調了《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對官員的剛性約束,另一方面說明中央正在從傳統的重視企業這一安全生產主體,轉移到重視政府部門這一監管主體上來。若能以此為突破口和契機,理順對監管主體的責任、義務、權力對應關系,將監管者放置于公眾參與的“汪洋大海”之中,我們就能超越單純的就事論事的官員問責,逐步走出管制困境。當然,連續19名高官的落馬,必然也會帶來很強的官場沖擊波,會讓官員心中形成一種問責預期,那就是,出多大的事就會有相應多大的官被免職。有權必有責、有權必擔責的行政意識,必然會在官員頭腦中打下印跡。
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上提出:“創造條件讓人民監督政府。”一方面,這指出了人民監督、公眾參與對保障政府工作健康有序運行的必要性、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對當前人民參與政府監督條件的擔憂。就政府管制活動而言,管制的體制變革,影響百姓生活生產條件的改善,直接影響民生狀況;管制文化的創新,直接影響民間創業和財富積累的積極性,間接影響民生狀況;管制理念的現代化直接影響公民管理國家事務的廣度與深度,影響服務型政府建設外部力量的聚集。總之,管制理念的變革也是為人民服務宗旨創新的新挑戰。改變不合時宜的政府管制,為市場發育提供公平規范的法律環境,也正成為民營企業當前極其重要的利益訴求。
加強監管,需要的不僅僅是政府權力對市場秩序的干預力度和范圍的加深和擴張,而是需要一個監管成本與監管效果的適當權衡。政務公開與群眾監督舉報、公眾參與相結合,應該成為創新政府管制文化,提高政府管制效率的重要突破口。現代政府行政管理的兩大支柱是行政程序的公開原則和公眾參與原則。在行政內容公開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2008年5月1日開始生效;在行政過程公開方面,2008年10月1日通過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這些法律都為創新政府管制文化提供了良好條件。在“對政府而言,法不授權皆禁止,對公民而言,法不禁止則自由”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的今天,在資訊發達的信息社會,走出管制困境的低成本方式,就是政務公開、監管公開、公眾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