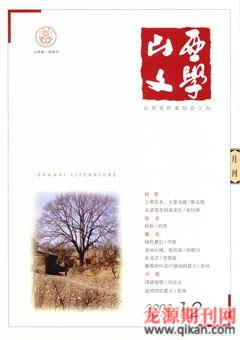被我的叫賣聲感動的夏天
黃 風
1988年的炎熱異乎尋常,從頭籠罩到腳,盡管所有的窗戶都洞開了,讓風暢通無阻,但我借居的老屋依然熱得像一條老狗,趴在地下茍延殘喘。自然,我也一樣在劫難逃。
炎熱使我變得十分懼怕運動,就像一個肥胖癥患者,除了吃喝拉撒,終日躺在一張鋼絲折疊床上。那折疊床放在屋外的一棵杏樹下。在躺之前,我總要拿桶接上自來水,先把折疊床澆得水淋淋的,然后再把桶反扣到頭上,把自己澆得水淋淋的。但是仍然不能抵擋炎熱,躺在折疊床上的我很快就被蒸得熱氣騰騰,黝黑的皮膚變得發紅。
每至黃昏,鎮上的大喇叭就像忠于職守的公雞,先打一聲啼鳴,然后哇啦哇啦大叫起來:
“據縣氣象站最新預報,明天依然是晴天,白天最高氣溫38℃,晚上最低氣溫22℃。”
一聽到大喇叭這樣的叫喚,我的耳朵就沮喪地耷拉下來,因為那哇啦哇啦的聲音,無疑等于宣判了次日死刑。就在我的期待被焦灼得形容枯槁的時候,一場大雨終于電閃雷鳴地到來,將鋪天蓋地的炎熱沖刷得一干二凈。
雨后的小鎮,盡管殘余的炎熱還藕斷絲連,但是追逐濃云遠去的大雨,已給了小鎮足夠的涼爽與清新。每一片樹葉都在閃閃發亮,每一個屋檐都在滴滴答答。被炎熱圍困已久的人們和我一樣瘋了,光著膀子聚集在街上,像一群哇哇亂叫的鴨子。一個叫老紅頭的老頭,竟站在一家店鋪的門前,一手咚咚地搗著拐杖,一手捋著胡須上的雨水,大罵老天爺:
“你他媽旱呀,往死里旱呀!”
他的大罵持續了很久,最后又像小兒一樣痛哭流涕起來:
“再不下,我這把老骨頭就當柴燒了。”
那天下午,我穿著條紋短褲在街上游來蕩去。我響亮地踏著積水,無論碰到誰都點頭哈腰:
“好雨,好雨!”
在長不足兩里的大街上,我不知往返了幾個來回,將多日的溽悶與無聊拋售出去,然后鉆進臨街的一家小酒館。酒館里還不到熱鬧的時候,三五張桌子就陪著我一個人。我選擇一張挨窗的桌子坐下后,要了一碟花生米和一瓶啤酒。我一邊往嘴里拋著花生米,一邊喝著泡沫擁擠的啤酒。喝罷一瓶還不盡興,我就又要了兩瓶,并且叫來老板一塊兒喝。老板叫牛三。
我欣賞著街上的景致,對牛三說:“好雨。”
牛三很會附和,也說:“好雨。”
為了進一步證明他的回答,牛三指著屋外的樹說,你瞧街上的那些樹多鮮活,被風嘩啦啦地一吹,就像風流的寡婦。牛三的話令我耳目一新,那些被大雨梳洗過的樹,的確像風流的寡婦。就在我為牛三的話贊嘆不已的時候,大街上悠揚起幾聲冰棍的叫賣聲。牛三便放下手里的啤酒,看著隨后從窗前經過的賣冰棍的女人,對我說:
“這個女人就是寡婦,你瞧那頭發一飄一飄,那腰一顫一顫的,不像是街上的一棵樹嗎?,
牛三的目光充滿了一廂情愿的迷戀,一直目送那女人在窗外遠去,然后收回來說:
“這女人可掙錢了,每天至少要賣三兩箱冰棍,可比你們當教師的強。你們咬文嚼字行,賣冰棍行嗎?”
說女人就說女人,沒想到牛三會扯上我們當教師的,心里不禁恨道,你以為當教師的就會咬文嚼字,別的什么也干不了?于是,看著牛三那張做飯館小老板做久了,完完全全老于世故的臉,我把啤酒瓶往桌子上一放,說:
“牛老板,我要是能賣了呢?”
牛三晃蕩著的頭停了下來,滿臉臭烘烘的不屑迅速轉化成嘻嘻一笑,糾集了臉上所有的皮肉說:
“好好好,你要是敢放下教師架子去賣冰棍,這頓酒錢我做東!而且,等你暑假開學了我再請你一頓。”
“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
經過一場大雨的沐浴,第二天陽光更加鋒芒畢露。那大雨帶來的涼爽很快就退避三舍,只在墻頭上和院子里留下一層浮淺的濕潤。在這樣的天氣去賣冰棍,等待我的無疑是狼狽,我后悔不該同牛三打賭,可是既然已經開賭,我就絕不能食言。
那天我一早起來就騎著車子進城了。因為我棲居的小鎮并不生產冰棍,要賣冰棍就必須到城里去販。城里的冰棍作坊有好幾家,我去的這家是牛三舅舅開的。昨天喝罷酒,牛三給我開了一張二指寬的紙條:
“老舅,這是我的一個朋友,請照顧。”
牛三這樣做我很清楚,表面上是熱心幫忙,實際上是想監督我。牛三的老舅非常熱情,不僅冰棍箱子讓我白用,而且冰棍販多販少都不用掏現錢,每天賣完了再回來結算。然后他把我帶進作坊,打開幾個冰柜說:
“這是冰棍,你三分錢一根販上,出去可以賣七分錢。這是雪糕,你七分錢一根販上,出去可以賣一毛二,或者一毛五。”
那些五顏六色的冰棍和雪糕,我后來才知道并無多大區別,所謂冰棍純粹是由冷水、糖精和色素凍的,而雪糕只不過是冷水換成了開水,又多加了點牛奶而已。那雪糕吃起來多少還有點酥脆,而冰棍簡直就像是玻璃,嚓嚓的一咬滿嘴冰碴。
從那天起,我每天一早進城販上冰棍,然后從離城最近的村子開始,一個村挨一個村地叫賣。好的時候一天賣三箱兩箱,差的時候一天賣一箱半箱。
我的叫賣聲起初無比僵硬,尤其在烈日當空的時候,還帶有一種氣勢洶洶的沙啞:
“買冰棍來!”
盡管我叫得十分賣力,出來買冰棍的人卻寥寥無幾。一次我騎著車子進村后,遠遠看到一個小男孩站在巷口,從那瞭望我的樣子,我斷定他是想買的。可是,等我把車子在離巷口不遠的一棵樹旁停下,喊了一聲,那小男孩竟嚇得把頭一縮從巷口消失了,過了一會兒才由一個老太太牽著又出來。老太太出來的時候,我還在喊叫,老太太于是瞇起眼打量著我,說:
“小伙子,你這不是賣冰棍,你這是嚎嗓子。你干么要那么叫呢?瞧你脖子里的青筋都繃出來了。”
老太太又說她也賣過冰棍,只因上了年紀才不賣了。她說賣冰棍得把嗓子放柔和了,就像跟人熱情打招呼似的。說著,老太太就給我做起了示范:
“哎,買冰棍來!”
為了說明聲音的柔和性,她又把一只胳膊伸展了,一柔一柔地展示給我看。老太太盡管上了年紀,喊出的聲音未免嘶啞,但是聽了仍叫人感覺舒服,有一種溫柔的親近,讓我想起了小鎮上那個賣冰棍的女人。
老太太見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就把手一揚謙虛起來:
“老了老了,跟你這么說叫人笑話呢,不過也就得那么喊,做生意嘛!而且,你們男人喊出來的聲音,還應該有一點磁性。”
老太太的話讓我十分驚異,我沒想到老太太還會說出“磁性”這個很時尚的詞來。為了表示對她的謝意,我取出一根雪糕給那小男孩:
“別買了,這根雪糕送你。”
老太太立刻激動得嘴里漏水,要那小男孩謝了又謝,然后一邊拉著孩子往回走,一邊告訴我她就住在那條巷里,以后再來遇到什么不方便,可以找她。
說著,老太太又哈哈笑了:
“大兄弟別見外,我這是人老了,王婆賣瓜自賣自夸。”
自從接受了老太太的指教,我就改變了叫賣方式,努力使自己的聲音婉轉悠揚起來,像溫柔的紗巾飄過鄉村的大街小巷。并且按照老太太說的,充滿一種磁性的誘惑。后來又見過一次老太太,她對我改善了的叫賣聲非常滿意,隨即又進
行了熱情的指教。她說賣冰棍也是在做生意,像識字一樣一定要有悟性,她看出我有這方面的悟性,所以我的冰棍會越賣越好。
老太太接著告訴我,她祖父就是從沿街叫賣起的家,直到后來做掌柜坐過京城。
盡管老太太并沒有告訴我,她祖父的生意做得有多大,但是從她自豪的語氣中,我聽出了她祖父當年的富有。老太太說曾聽她祖父講,在老北京沿街叫賣不叫“喊”叫“唱”,春天賣風箏叫唱風箏,夏天賣西瓜叫唱西瓜,秋天賣菱角叫唱菱角,冬天賣糖葫蘆叫唱糖葫蘆。在她祖父的那個遙遠年代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每天都能聽到唱的聲音,而且胡同越深唱得越動聽。
比如賣琉璃咯嘣的。老太太鼓起缺牙漏氣的嘴,先撲撲地給我模仿兩聲琉璃咯嘣聲,然后把一只手遮到嘴邊,唱道:
“買琉璃咯嘣哎——買琉璃咯嘣哎!”
在老太太的兩次指教之下,我的叫賣聲大有長進,每天早晨只要我帶著冰棍一進村,迎著朝陽吆喝一聲:
“買冰棍哎!”
就會有孩子奔跑出來,咚咚咚地穿越巷子,有時屁股后頭還跟著一條小狗。其中有一個叫貴貴的小男孩最使我難忘。他穿著一件破舊的背心,從巷子里跑出來的時候,眼角常常糊滿眼屎,一副剛從被窩爬出來的樣子。然后站在巷口的大街上,兩手交替著揉搓眼窩,證實我的吆喝并不虛假后,又迎著我咚咚咚地跑來。
我問他:
“要冰棍,還是要雪糕?”
望著我手里五顏六色的冰棍雪糕,貴貴一開始并不說話,而是拿眼睛不停地選擇著,那眼睛已變得葡萄一樣明亮。經過一番選擇之后,貴貴的目光落在了一根粉紅色的冰棍上,他說:
“我就要那根。”
可是,當我把那根冰棍遞給他的時候,貴貴又猶豫不決起來,改變了主意,指著我手里的一根黃顏色的雪糕,說:
“我不想吃冰棍了,想吃雪糕。”
貴貴遞上的錢又黑又臟,好像在手里攥了很久,帶著一種汗的潮濕。他像剝香蕉一樣剝去雪糕上的紙,第一口先是小心翼翼地品嘗,接著大口大口地抿了起來。我看到他的喉嚨近乎夸張地蠕動,看到他的鼻涕進進出出,每一次無聲無息鉆出來,每一次又被響亮地吸了回去。
早晨的鄉村十分平靜,一抹輕描淡寫的炊煙,春困似的盤繞在上空。因為大人們趁著涼爽下地去了,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盡管我的叫賣聲穿越空曠的大街,給鄉村帶來了嘹亮的氣息,但是出來買冰棍的人并沒有幾個。直到將近中午的時候,大人們陸陸續續從地里回來,街上變得熱鬧起來,買冰棍的人才漸漸多了起來。
他們買上冰棍以后,吃的表情豐富而生動。如果是個大男人,他咔嚓咬上一口,還沒來得及吃出個味道,就開始表示不滿:
“這他媽還解渴?冰疙瘩一個。”
如果是婦人就先抿上一口,把兩片嘴唇咂得啪啪的,隨即又抿上兩口,然后舉起胳膊來吆喝孩子:
“毛毛你快點出來,這人賣的冰棍挺甜呀。”
而姑娘和小媳婦吃的時候,總是把臉背過去,怕冰棍汁滴到衣服上,又把身體前傾了,先伸出舌尖切上一點,接著咬下一塊兒來。她們吃著,就一手捂住腮幫子,驚訝地叫道:
“這冰棍咋這么浸牙,還不如不買呢!”
最有意思的是老太太,摸摸索索地從兜里掏出錢來,經過一番挑挑揀揀之后,便拿上冰棍反復看,然后把臉的兩側凹進去,意味深長地吸溜上一口。也許是冰棍太涼了,老太太馬上就聚集起滿臉皺紋,把牙齒殘缺的嘴大張開,發出一聲嘆息:
“啊喲喲,這貴巴巴的,快拿回去給娃們吃吧!”
說著,老太太就搖搖擺擺地離開了,兩只小腳擰得非常急促。如果迎面碰上有誰來買,老太太就趕忙阻止:
“快別買,快別買,那東西還有個吃頭!”
在一個村子賣得差不多了,我就又去另一個村子。烈日下的田野熱氣騰騰,寂靜得沒有一點喧嘩聲。這正是賣冰棍的好時候,我必須趕往另一個村子。我騎車行走在鄉間的黃土路上,有時從路旁的地里會突然冒出一聲:
“賣冰棍的,等一等!”
那吆喝聲望眼欲穿,好像等待了好久。我停下車子,開始并看不見一個人影,慢慢才發現莊稼沉靜的波濤之上,漂浮著幾頂閃爍的草帽,游移的脊背像水牛一樣。有一頂草帽挺立起來,一只手臂在向我揮舞。草帽過來,齊腰深的莊稼發出水似的聲響。陽光下,赤裸的肩膀油亮油亮,像涂了一層古銅色的油彩。
從地里出來之后,那草帽下的一張臉已揮汗如雨,但是依然掩蓋不住興致勃勃,他把買的十幾根冰棍放到草帽里端著,然后吆喝地里的人:
“別鋤了,吃冰棍來!”
那還在勞作的幾個人,就把鋤頭栽在地里,把草帽戴在鋤桿上,齊聚到路邊來。他們拿起冰棍放進嘴里,就像吃黃瓜蘿卜。那吃的聲音,像他們的肌肉一樣緊張有力,嚓嚓地吃完一根又吃一根,直到把草帽里的冰棍吃完為止。每當他們歇息的時候,如果我還繼續待在一旁,就會遭遇一種尷尬——
“嗨呀,這后生哪像個賣冰棍的,衣服穿得筆挺筆挺!”
在他們印象中,事實上在我的印象中也是,那些賣冰棍的人大多形容不整,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吱吱咯咯地奔走在鄉村,一副為生計所迫的模樣。而我,不僅衣著齊整,還戴著白色的太陽帽,他們自然就十分奇怪了。于是圍繞著我,他們開始了嘻嘻哈哈的盤問,最后一致得出的結論是:
“這后生是個懶蟲,不想在地里受苦,才出來賣冰棍了。”
1988年,在他們標本式的農民眼里,賣冰棍一向是游手好閑的事情,不務正業的事情。遭遇幾次尷尬以后,我再一聽到地里有人吆喝就心跳,要么連車子也不敢停,要么把冰棍賣給他們就走,但是仍免不了背后的笑聲。
我的信心因此倍受打擊,有幾天幾乎賣不下去了。
但漸漸地,賣冰棍也給我帶來了樂趣,帶來了未曾預料的回報。1988年的教師還滿臉菜色,當教授的不如賣茶蛋的,遠不敢像現在形容的,加入到“粉筆頭大蓋帽”的行列。那時我和妻子兩個人教書,每月工資加起來不足300塊錢,而每天賣冰棍至少能賺十幾元錢,讓我羞澀的錢囊倍感驕傲。當時十幾元錢,割豬肉能割5斤,買豆腐能買70斤,拉煤能拉800斤。
每當下午,我風塵仆仆地回來,把滿兜零零碎碎的錢掏到桌子上,妻子的欣喜就溢于言表,把一枚枚硬幣集中到罐頭瓶里,把一張張毛票用手撫展了,然后拿系辮子的皮筋扎好,認真的程度讓我不勝其煩。妻子激動地告訴我:
“今天又掙了十四塊八毛六分錢。”
或者發出一聲驚訝:
“哎呀,今天掙了二十多塊錢呢!”
妻子的驚訝十分可愛,像孩子意外獲得糖塊一樣。當初我賣冰棍的時候妻子十分贊成,但也僅僅是贊成而已,根本沒想到會掙錢。我后來想,她當初之所以贊成,大概是見我每天無所事事。但是不管怎樣,當時妻子的態度非常出乎我的意料,她說想賣就去賣吧,怕什么?
“不過,賣冰棍的時候,還是別說你是老師。”
妻子總還是有所顧忌的。這顧忌一聽就多余,真要碰上相識的人,還用我自作多情地遮掩嗎?可是妻子的顧忌也不無體諒,我一旦碰上熟人,他們就像那地里的農民一樣,視我如異類,目
光中包含了許多復雜的東西。開始的時候我還回避,然而發現這個世界太小了,愈是回避反倒愈容易碰上,到后來隨著賣冰棍時間的增長,我的臉皮也愈來愈厚了。
每天十幾二十幾塊錢的收入,使我賣冰棍的初衷脆不可擊,漸漸發生了改變,不再是跟牛三打賭,或者體驗一種生活的樂趣,而是實實在在地為了掙錢。可以說,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小販。
那些屬于小販的東西便像老人斑一樣,開始在我身上潛滋暗長出來,為賣好每一根冰棍而挖空心思。因為買冰棍的大多是孩子,我就想辦法在他們身上做文章。比如,他們最喜歡什么顏色的冰棍,最喜歡在什么時候來買,還有家里不給錢的時候,如何蠱惑他們去要。許多家長最害怕孩子哭鬧,我就教他們,一哭鬧家長就得出來,把買下的冰棍狠狠地塞給孩子:
“吃吃吃,吃死你就算了!”
有時,看著家長生氣之極的樣子,我覺得自己有點缺德,就像一個教唆犯。可是稍后,看著孩子香甜的樣子,甚至朝我做個小鬼臉,表示我們配合成功,我就又釋然起來。不就是一根冰棍嗎?我掙了幾分錢,孩子得到了小小的享受,何樂而不為呢!
暑假期間,不少學校依然在補課,鄉村少了許多熱鬧,也使我的冰棍生意清淡了許多。所以每到一村,我就打問學校補不補課,要是補課,我就趕在天氣炎熱的時候,把車子停在校門口的不遠處,或者學校圍墻的一個豁口處。但決不能吆喝,當教師的我深知老師們最討厭小商小販,如果我吆喝被聽到了,會借訓斥學生把我罵個狗血噴頭。
像守株待兔一樣,我必須耐心等待。下課的鈴聲一響,我就把一根鮮艷的冰棍插到冰棍箱子或車把上。從教室里蜂擁而出的學生,目光很快就被那鮮艷的冰棍捕獲了,他們先是一個站在那里看,然后就幾個擠作一堆看,像走進糖果店一樣。
在冰棍鮮艷的誘惑下,他們很快有了行動,先只一個孩子走過來,他小心翼翼,就像一只偷油吃的耗子。他的目光仍不忘背后的同學,還有教室里的老師,直到臨近校門或豁口處,才一下子奔跑起來,把早已準備好的錢迅速地掏給我,拿上冰棍再迅速奔跑回去。這時,我童年的一幕便在那孩子身上再現。他跑回去卻不再扎堆兒,而是待在一個遠離教室視線的角落。
還在原地站著的那些同學,目光一直追隨著他,一個個既羨慕又擔心,隨后你推我攘地湊過去。在虎視眈眈之下,那孩子吃冰棍的樣子顯得無比優越,同時也不無緊張,害怕有人搶奪他的冰棍,也害怕他們去告老師。于是,像我曾經歷的童年一樣,他無奈地舉著冰棍,讓周圍的同學每人輪流抿上一口。見有的同學抿了還想抿,他就尖叫起來:
“你不能自己買去,盡抿我的。”
他的不滿和那一口冰棍的香甜,顯然刺激了圍著他的同學,立刻就有人離開他,像他一樣行動迅速地向我跑來。見一個同學跑過去,其他的同學也便跟著跑,像成群結隊的蜜蜂,一下子把我鬧哄哄地圍住。有的看有的買,十幾根冰棍轉眼就賣出去了。
那鬧哄哄的情形,無疑會驚動教室里的老師,我必須適可而止,于是大喊一聲:
“快走,你們老師出來了!”
在我的一聲斷喝之下,他們一哄而散。買了的把冰棍藏到身后,沒買的就趕緊準備好了話,如果真碰上老師出來,他就慌忙上前表白自己,同時出賣同學:
“老師我沒買,他買來。”
如果發現老師并未出來,他們就重新變得像麻雀一樣嘰嘰喳喳。
在幾十天的暑假中,我跑了許多村子,但大體上是固定的,所以一到那些村子,有眼尖的孩子老遠看到了,就會吆喝:
“快看,那個戴白帽子賣冰棍的又來了!”
漸漸地,我同那些村里的孩子建立起了一種信任,其他賣冰棍的人雖然也去,可是他們總等著我去了才買,要是哪一天我沒有按時出現,他們就會問:
“你怎么才來?”
我的生意因此始終保持不錯。盡管,我為賣好每一根冰棍挖空心思,有時也會為每一分錢計較,但也不乏慷慨的時候。尤其是碰上半路下雨,或者天氣熱得實在無法忍受,我就會把冰棍三八折二地賣出去,甚至白送人。一遇到這個時候,孩子們就蜂擁而至,原本跟前只有一兩個孩子,也沒有誰去叫,一下子竟冒出許多來。
爭搶下的樂不可支,沒爭搶下的就垂頭喪氣。看著人家吃得香甜,免不了就有孩子去搶奪,于是要么打了起來,要么被搶奪的孩子一蹦跳遠了,把冰棍像鴨子食魚一樣,三口兩口吞到肚子里。他笑嘻嘻地揩抹著嘴,挑逗那失意的孩子:
“有本事搶來呀?”
臨近暑假開學的前兩天,我結束了幾十天賣冰棍的奔走。那天下午我收工后,像平時一樣到牛三舅舅家結算了當天的賬,又把冰棍箱子退掉,然后騎著車子直奔回家。
我的臉因飽受太陽之吻,變得黝黑發亮,而我的牙齒卻潔白如初,仿佛一個非洲哥兒們行進在馬路上。我的內心充滿了踏實、輕松和愉快,就像剛參加完一場艱苦卓絕的考試,或者一場曠日持久的戀愛談判。在陽光與樹蔭交替的馬路上,我時而把身子伏到車把上飆車,時而挺起身子來如蛇游走,驚得來往車輛喇叭亂叫。
家里出來后,我帶著專門留下的幾根冰棍去見牛三。牛三一見我就驚慌起來,光是蹺起大拇指說先生你行了,卻閉口不談打賭的事情。我知道牛三想耍賴,就打斷他說,別光是行了行了的,你輸下的那頓酒呢?
牛三立刻變得笑比哭還難看:
“喝、喝,說好了的喝,怎能不喝呢?”
說著就爛了臉,把脖子長了問我:
“我倒不在乎一頓酒,可先生你還真喝呀?”
此后我再沒賣過冰棍,本來還想去賣,然而終究沒有賣成。在我已經歷的人生里,和即將經歷的人生里,那一段賣冰棍的日子,可以說短得只能用分秒計算,但它卻留給了我漫長的記憶。有一望無際的田野和島嶼一般的鄉村,也有我烈日下奔走的身影和叫賣聲,還有那些可愛的孩子和樸實的村民,直到現在依舊美好如初。那美好是粉紅色的,是一種冰棍的顏色,也是那個夏天的顏色。
它是高樓林立,被人與車擁擠不堪的城市無法想象的。
責任編輯/白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