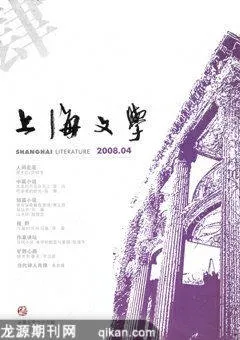“真正屬于詩的不是復雜,而是單純”
張清華:可否談談對詩歌觀念化的看法?
多多:我們現在都快把觀念變成口頭禪了。我不反對觀念,但不應該把它固定。它應該是流動的,是生命的流動,是“氣”,氣先是均勻而長,以后是長而弱。有沒有一以貫之的詩歌觀念呢?那是不存在的,也不可能的。如果太相信自己,這個人就完了。詩歌要傾聽,要虔誠地等待詩神的到來。這很古老,但屢試不爽。詩歌是“結晶”,不能用理性和邏輯推導。但是現在的詩歌有很大的改變,智性的成分增多,詩歌的個性、風格和差異性越來越小。文化的危機源自大量的抽象,導致個性的消失。這不是我說的,這是榮格說的——他說抽象來自原型,原型是一樣的,所以藝術家要警惕抽象導致個性的消失。模式化對于藝術是最可怕的,你建構的所有理論框架最后都不攻自破。強大的個性一旦建立以后,非心靈的密碼不能打開。以語言結構做“硬件”,以靈魂和東方文化做“軟件”,這兩樣結合起來會產生巨大的生命能量。
張清華:你目前也在高校做教授,詩歌方面的個性化思想在學院環境里是否感到受束縛?
多多:上課還好。
張清華:那可能是從一點出發,無極限漫游,在漫游的過程中做出一系列驚險而漂亮的動作。
多多:你看西方詩人,每個人都能談自己的詩歌理論,這與他們的語言文字、受過的教育等密切相關。中國現在許多年輕詩人也在大談理論,但由于作品低下,理論全是別人的。我決不忽略理論,而是覺得目前理論是有問題的。中國學術承擔的問題很大,國學深不可測,西學路子能描述清晰就不錯了,魚目混珠。其實真正屬于詩的理解不是復雜,而是單純。“單純不是簡單,而是更為復雜的緊縮和綜合。”
張清華:另一個問題,目前你在各種版本上登出來的早期作品,年代能確認嗎?
多多:南開大學的李瑞霞找到我確認年代問題,說早期作品是后期補的,我大吃一驚。我的作品在十年以后才能發表,我修改是可能的。做研究的人應該直接做文本閱讀。看來作品不要直接發表,一發表就有時間問題了。
張清華:這是個“文學史問題”,要將其“歷史化”,需要求證。一首詩在不同年代問世,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芒克的“太陽落了,黑夜gzH3xCxVOsrZYHSmBtEOTw==爬上來……”北島也寫過類似的詩句,時間誰先誰后?意義完全不同。
多多:那樣類似的太多了。一個詩人要靠自己的作品建立真正的王國,創造需要的是沖動、盲目、不定性,批判性越強,對創造性損傷就越大。尤其是年輕人——我的學生們智商都很高,但一閱讀詩歌,感覺能力就沒有那么強了。現在的寫作偏離了詩歌本性,我更看重讀詩寫詩講詩。說到底,一個人真行的話,幾句詩就行,否則大量的話語掩蓋了詩的本質。我提倡的批評是中國古代的“點評式”批評。現在這樣的傳統怎么就沒有了呢?這也許涉及到現代詩歌的復雜性。
張清華:呵,學院派詩歌評論有它的限制性。要求有長度,有“規范”。我以為只有通過詩歌閱讀和與詩人的交往、通過詩歌精神的吸納,才可以部分地抵制研究本身的異化,葆有基本的感悟,但這也很困難。
多多:你可以看看波伏瓦、克里斯蒂娃、馬拉美等人,他們的語言真是非常棒。中國詩人和理論家還需要不懈努力。文化中國的建設如果還一直像現在這樣追求名利、安于現狀,那不可能完成。學術也一樣。弱者不但無外交,也無文化,無詩歌。我太希望中國詩歌強大了,但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創造在當下,活在當下。沒有當下,歷史也不存在。
張清華:在自己的限度內做好自己的事情。
多多:盡力。新詩在90年代有質的飛躍,沒有每一代人兢兢業業的奮斗,進步是不可能的。
張清華:是啊,之前實際上可以一直看作是新詩的“童年期”。
多多:“童年”也有神童啊。穆旦在40年代就很成熟了,在今天能找到幾個這樣的詩人呢?詩歌的營養來源極其微弱,但詩歌的敵人無所不在。西方的詩歌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也很多年沒有大師出現。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但每個人要盡力。我全都釋放了,盡到自己的力量了,那也足夠了。在這個技術化的時代,作為一個詩人,面對消費文化、犬儒主義,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中國是詩歌之國呀。
張清華: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們現在正繼續焚毀著以往的文化遺產。
多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詩歌就更重要。因為詩歌不僅是給同代人看的,而是給后人看的,有傳承價值。只要寫出優秀的、有真性情的東西,自然就會流傳。
(安靜整理,未經多多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