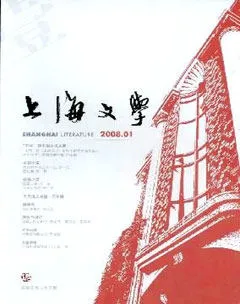談詩片段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詩歌創作的關系……
在中國的新詩寫作實踐中,從一開始產生到現在,一直有一個東西存在,那就是大部分詩人都曾經努力地要使得中國的詩歌“現代化”。可什么叫現代化呢?在某些條件下它實際只是“西方化”而已。這個情況也反映在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說到中國當代文化,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是難免的,因為我們謀求的現代化這個概念是從西方過來的。所以當代的詩人,不論他是多么的本土化,實際上都能在他身上找到現代化的影子。說到底,連本土化的觀念也不是我們老祖宗的觀念——你聽說過李白、杜甫努力尋求本土化嗎?本土化是現代化的反向產物。那么謀求現代化會不會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呢?當然它會不斷地加深,不斷地向前推進,但是呢,百分百的現代化和西方化這種情況不會無止境地進行下去。不光是我,也有其他一些詩人、藝術家,現在慢慢意識到我們不能僅僅是現代化。就是我們的藝術當中不能僅僅包括現代化這個因素,肯定還要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
我最近實際上已經有一段時間一直都在看中國古典文學。最近讀的書全是關于陶淵明的,我也打算寫一個關于陶淵明的文章。對陶淵明的興趣,可能跟我原來讀的一些西方文學有關系。西方文學會提供我一個新的角度來重新看待陶淵明。這比起用舊方法來看陶淵明,能夠看出更多。其實從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能看出不同的陶淵明來。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在創作上的關系,我想主要是一種精神上的關系。傳統寫法當中的有些東西還可以用,有些東西現在可能已用不上了。由于閱讀陶淵明和相關的東西,我發現中國的律詩的形成,有著非常豐富的歷史背景。比如說中國人對于音韻的認識,就是受到印度梵文的影響。伴隨著對佛經的翻譯,中國人才開始對于音韻這個東西有了深入的了解。然后我們慢慢(當然和我們本土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才建立起我們關于律詩的這個概念。所以,我們今天如果強行說中國當代詩歌就要建立起一套什么制度來,這是不可能的;或者我們會建立起一些其他的東西來,而不是老祖宗的那一套五言律、七言律,它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是,詩歌創作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詩歌背后所能夠提供給讀者的那樣一種廣闊的精神,肯定和傳統詩歌是有密切的關系。
怎么讀中國古典詩詞……
雖然很多人聲稱熱愛傳統,但閱讀卻是粗疏的——比如端午節紀念屈原,很多人知道屈原可能就是一句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但他的詩歌到底寫成什么樣?很少有人知道。我自己非常喜歡他的《湘夫人》、《山鬼》這樣的詩歌。但是我相信很多知道屈原的人實際上并不想知道更多。《離騷》到底是一篇什么樣的作品?屈原為什么會寫出《離騷》這樣的作品?他為什么這樣寫?他這樣寫跟他橫向的世界上的詩歌比較時會產生什么樣的意義?它對于后來的中國詩歌的整個寫作是一個什么樣的意義?他的那種寫法到底是一個邊緣化的寫法,還是后來變成了一種主流的寫法?這所有的問題,實際上我們都不是太清楚。在這些問題中如果你有很小的發現,那也會使問題有所進展。否則的話,我們對不起中國古典詩歌。
現代詩的自由與韻律……
中國古典詩歌講究韻律。最早是四言的形式,然后五言、七言,當然還有三言,到了戲劇當中可能還有九言十一言。我剛才講到中國古代詩歌韻律的建立,跟對佛經的翻譯很有關系。因為梵文是拼音文字。由于我們認識到拼音文字,所以我們才知道什么叫做“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聲母和韻母,所以我們建立起了這么一套古代的韻律、格律。那么現代詩人當中也有一些詩人努力的要建立起現代詩歌的格律,像徐志摩寫豆腐塊兒的詩歌,卞芝琳要努力地往中國詩歌里引入“音步”。這個東西在英語里叫foot,有人翻成“音尺”。他們想用這種格律來使得中國現代詩歌也獲得一種表達上的形式。但是這個東西到目前為止是失敗的,包括馮至先生本人的十四行詩,在中文語境里寫得還算不錯。但所謂中文里的音尺,實際上就是幾個詞組放在一塊而已,并沒有什么一定的規范。所以我也對它不感興趣。還有轉行,也是從西方詩歌中來的。西方詩歌講究跨行,因為它是一種邏輯語言。當中有主句有從句,句子很長。雪萊有一首十四行詩叫《奧齊曼德斯》,整個十四行就是一句話。那么我們中文呢,都是短句子,它不是一種邏輯語言,而是一種能夠把我們導向頓悟的語言。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也學西方語言那樣轉行就沒有必要了。在我一開始寫詩的時候,我不明白為什么要轉行的時候,我也轉行,學嘛。后來意識到語言的不同以后,我就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但是,我也可以理解這種轉行。比如說本來可以在上一句出現在末尾的詞,他拿到下一句做第一個詞來出現,這實際上起到了一個強調的作用。也就是說他要強調這個詞,或者他希望這個詞在那句話當中構成一個中斷感,斷下來,等于把一個時間因素引進來。這種情況我理解,但是我自己現在已經完全不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