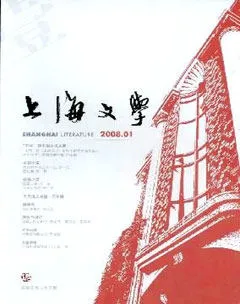正視 斜視 審視 凝視
關于視覺,在《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那邊。郵差并不看我,也不指明他說的那邊是哪邊。他收起他的薄本子就走了,消失在這個連體別墅的青磚圍墻外。我不好意思跟出去看,一方面我知道我自己疑惑的瑣碎,一方面,我感覺到郵差已經看穿了我的問題啊,他憂傷的面孔像是有備而來。此外,手里的郵件也給了我新的疑惑。在我的記憶里,這一輩子我都沒有收到任何掛號郵件。”這里郵差不看,是因為我看;我不好意思看,是因為對方已看穿了我,不看也是一種看,看其實是不看。消失因看而生,不看因疑惑而起。掛號郵件激起新的疑惑,失憶的我開始走上了“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的旅途。疑惑是一個重要的角色,如同幽靈般地在須一瓜小說中徘徊,不招即來,揮之不去,可視與不可視終于難分難解,模糊伴隨著清晰,清晰亦伴隨著模糊。恰如“周巧惠和那個傻瓜終于雙目對視,志同道合地討論起來。‘檔案的真實性’一詞也一再出現。我則視力模糊腦力渙散。”
差不多的說法“可見與不可見”,是法國哲學家梅洛-龐蒂未竟之遺作的標題。遺著出版之際,拉康正在撰寫其重要的論文《論凝視作為小對形》,文中提到《可見與不可見》,并稱其為知音。這里的困惑之處在于,可見與不可見不應有共通之處。但不幸的是它們之間確實是有的。它們的共通之處就在于其互為依存的難以分割。在拉康的言說中,其共通之處還要復雜得多。對一個失憶的人來說,熟悉的過去和事件是不可見的,封存的記憶一旦被打開,銘記鐫刻一件件煤氣爆炸及伴隨著主流文化侵襲的創作也隨之顯現可見了。“我盯著那個電話,像盯著一個真相的路口。我現在才意識到,其實我已經相當不愿意進入了。在這個失去記憶的城市,我恍惚在有罪和無辜之間。不管我是不是殺過人,現在,清白無辜的輕快感覺,正在艱難的恢復和建立中。如果我進入了,我還有退路嗎?”于是懼怕真相的我再次伸出其罪惡之手,不可見的謊言再次露出可見的真相。
“現實一旦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向我們展示,我們就繼續以這種方式來正視它。”
——恩斯特·卡西諾
真相果真在路口那里等著我嗎?不是說這種情況沒有,尤其是涉及到某個事件的某個缺口、懸疑即將臨近尾聲時,但更多的情況遠不是這樣,真相散落在四處,隱匿于彼此斷斷續續的聯絡之中,在真相的表象之上包裹一層又一層的偽裝,偽裝經常吸引我們注視,而唯其真相卻喜歡和忽視、無視打交道,真相也不是一種被動的存在,他或許生來就不喜歡被辨認,假相是其永久穿著的外衣,外衣內可能有真相,也可能什么都沒有。
《西風的話》講述琴聲氤氳、樂浪滔滔的美之島,一樁稀罕的兇殺案,被害人老渡輪,殺人嫌疑人梁祥以及九個間接的目擊證人進入了我們的視線。故事自然使我們聯想起黑澤明根據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筱竹叢中》和《羅生門》改編拍攝的著名電影《羅生門》。所不同的是,《羅生門》描寫的是“不加虛飾就活不下去的人的本性。”(《黑澤明自傳》中國電影出版社1987版)《西風的話》講述的則是追求真相之中如何遭遇假相,而種種假相又呈現出另一番真相。兇殺案的真相不見天日,但那“慢慢地恢復了昔日美好的生活”,葉青芝沒有遺書只有“遺畫”的投海自殺,以及那梁祥“非常流利的口哨”,讓我在不見真相之余似乎又看到了什么。同樣是寫兇殺案件,《西風的話》和《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在視覺感受上是不同的。前者從案件現場出發,破案過程因真相無法顯現而日益模糊,日漸淡忘,視線上是由近走向遠;后者則是事隔二十年后,一個失去記憶的作案人如何恢復記憶,去調查、追尋當年作案的真實現狀,視線上是由遠走向近。
在須一瓜的視覺之中,我們終于會驚異地發現,許多自以為熟悉的東西,結果往往變得陌生而難以辨認,人人都以為自己早已克服了這些弊端,實際還在左右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一次用心籌備的邂逅”竟然是一場空白,語言的親近熟知和身體的陌生抗拒竟然是一回事。“少許是多少”不止是對做可樂雞塊配料的疑問,更是對難以把握正確的審視。笛卡爾因為偏重看的思想而放棄了視覺,所以背棄了可見的事物。這種支配自己思想的支配力量是難以估量的。所謂視而不見的寫作依然活躍在四處便是一例。一部部中國當代文學史只要翻翻那目錄標題,便可知其是一部“偏重看的思想”的文學史。
須一瓜的書寫經歷有點意思。她80年代寫過幾年小說,以后便十幾年不寫,不為別的,“對語言藝術的退潮感,也是個重要的因素”。“語言藝術的退潮感”,意思并不很明確,但大致還是透露出作者的追求,寫是一種追求,不寫也可能是一種追求。十幾年的不寫,須一瓜成了非小說的寫作者,一位專跑公檢法專線的記者。政法記者的生活,須一瓜坦言“事情特別多,白天采訪,晚上寫稿,很忙。很多朋友都擔心我會把筆寫壞,成天的‘殺人、放火、走私、強奸、搶劫’,大家說我是全廈門最無聊的人,我覺得也對。但我知道,這期間,活生生、沉甸甸的生活元素,讓我看見和感悟著一般人不一定看見的東西。”關鍵是看見,政法記者何止千萬,為什么“我”看見了一般人不一定看不見的東西。小說家的眼力總充滿了貪婪的好奇心和感受力,哪怕這視界是意外、厄運、犯罪、暴力、死亡的流放地,充滿著伯格曼稱之為的“負面印跡”;哪怕所有這些元素都沁滲著幽深莫測的色彩,仿佛是寂然無聲的迷宮,須一瓜總能讓優雅的敘事映入我們的眼簾。同樣的經歷,同樣的看,結果卻是不一樣的。為得再現一個已經破譯的真實,是一種看;而瞄準一個總是模糊,尚待破譯的真實,也是一種看。須一瓜的寫作給我的印象是傾向于后者。唯后者這束目光是對一切既定秩序提出挑戰,它化自信為懷疑,“出手捕捉的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人生破綻和被遮蔽、被忽略的人生尷尬。”(姜廣平《與須一瓜對話》)
“那雙漂亮的眼睛一只睜著,另一只眼睛夾著……”
——《尾條記者》
《尾條記者》并不是須一瓜小說的上乘之作,但對審視須一瓜的書寫則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甚至在字里行間都能感受到那傾瀉的快意。“那雙漂亮的眼睛”說的是記者陳啟杰,小說一開始,“啟杰死了”。
“沒有靈堂的啟杰充滿陽光和音樂、在啟杰的笑臉里,張雨生帶有童聲的嗓子,在縱情歌頌生活。
我有一顆
比任何人都要狂熱的心
愿意接受任何一種更不平凡的邀請
這是三十歲陳啟杰生前自己布置的靈堂,大家在這里不知和他父母說什么好,幾個淚眼婆娑的女記者,捧著啟杰照片,叫帶相機的為她們合影一張,好像全是生前知己。一只眼睛睜著,一只眼睛夾著的啟杰的笑臉充滿了輕狂灑脫。”
根據死者的遺囑,敘述者作如此書寫。不知怎么,在閱讀須一瓜小說的日子里,這段文字總在我的記憶中縈回不去。明明白白的話,讀來如吟如唱,殘酷的陰影,充滿疑惑的死亡,灑落的卻是陽光。那充滿輕狂灑脫的笑臉,分明是敘事者不時流露的眼神,或者我們批評的言說許久不提的風格二字。什么是風格?記得杜魯門·卡波特回答說,這個“什么”就像禪宗的心印:“一只手拍出的聲音是什么?”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可遇而不可求。《尾條記者》無疑從文學角度聲援了職業記者對生活的正視,自然更多的情況是正視現實的記錄支撐了文學的偏見與斜視,伸張了文學的想象和意識。這些記錄在須一瓜的小說中俯拾皆是,但我再記住它的時候,已不再是關于記錄的記錄了。那種登上報紙的尾條新聞都是從隱秘復雜的社會故事中產生的,而那種將不尋常、突兀或苦澀的暴力兇殺與流暢的敘述和謎語般的人性奧秘連接在一起的故事,則經常是須一瓜作為小說家處理的題材。前者可以簡短格式加以陳述。后者則麻煩得多,我們須頗費周折,經過耐心思考和諸多闡釋之后或許可能真正理解的東西。
須一瓜是獨特的,我們幾乎很難把她和另外一個作家聯想起來。硬要扯上一個,那遙遠的哈謝克?也不像。須一瓜佩服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欣賞朱文的小說,但加入的絕不是余華或朱文的世界。她骨子里生來就有著對雷同的高度敵意。就題材、素材、地域、類別而言,在歸類問題上須一瓜都難以就范。在闡釋自己的創作時,“顛覆”是其常用詞。在和姜廣平的對話中,須一瓜曾用戲仿的口吻答道,自己的寫作是被生活所干預。這話有點粗暴,在強調差異某一側面時,多少降低了文學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生活與文學并不單純是此岸與彼岸的關系。虛構的活龍活現象真的一樣,說的僅僅是文學?生活無奇不有象小說一樣,說的僅僅是生活?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亦真,這可能更接近文學的居所。差不多的意思,羅蘭·巴特在其《寫作的零度》中這樣說:“小說是一種死亡,它把生命變成一種命運,把記憶變成一種有用的行為,把延續變成一種有方向有意義的時間。”人類生活發展至今,生活早已不是能遺棄文學而獨立的存在。對此,略薩說得更明白:“在心理學家和心理分析學家存在之前,甚至在巫師和魔法師出現之前,虛構就已經幫助人類(他們毫無查覺)共同生活,幫助人類適應那些來自人類內心深處的某些幽靈,以便讓人們生活復雜化,讓生活充滿難以企及具有破壞力的欲望。”(《謊言中的真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版)其實,生活和虛構并不是那么容易區分的。在這種情形中,問題并不在于虛構是不是等同事實,而在于我們的生活和虛構無法分離。這一點,我們只要重溫一下須一瓜小說世界中的生活:比如“尾條記者”的日常生活;“我的索菲婭公主號”一個進城農民工希望不斷演繹失望的故事;“我的蘭花一樣的流水啊”中夢所帶來的麻煩事;“有一種樹春天葉兒紅”中陳陽里那種理想主義的活法與死法;“地瓜一樣的大海”中十二歲的“我”如何幽靈般地進入和告別城市……。令人恐懼的是,從“謊言”世界到“真實”世界就像“從一個公園到另一個公園是那么容易”。當我們對“謊言世界”布滿了我們的評說和詮釋時,自信自然會伴隨著可視的“真實”世界;但文學畢竟始終是一種許諾而非實際,當他在追求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時,懷疑自然也會跟隨著不可視的“謊言世界”。
陳啟杰死后,實習生記者張禾開始其對于真相的追逐,生活也開始展示出一團解不開的亂麻。自以為接近真相的張禾突然發現,真相轉眼間離他遠去。開局和結尾是意味深長的對照。如同張禾去看守所探視那真正的所長時:“兩人互相看著,一點聲音也沒有,這樣的時間竟然持續了三分多鐘……所長的表情已經明白無誤的告訴他,他在承受他應該承受的。張禾覺得心里空蕩蕩的安靜。他事后甚至懷疑是雙方都在珍惜那種無言的相對。”死者的陽光和活著的陰影是一種無聲的對視,或許,這里用無情更為確切。我們已經習慣了帶有面具的事實,可一旦面具被撕破,一種苦澀則會刺痛我們的雙眼,哪怕“另一只眼是夾著的”。
“不是誰都能看到淡綠色的月亮的。”
——《淡綠色的月亮》
相對擁擠不堪、忙忙碌碌、噪音嘈雜的都市生活,須一瓜的文字總讓人感到一種靜謐的力量。纖毫必至的觀察讓奧秘難以置信的深藏著,一種暗藏的目標總能穿越其敘述,從遠處隱秘的浮現出,猶如這“淡綠色的月亮”。存在經常被可見物掩蓋著,“不是誰都能看到”,“不是什么時候都能看到”,原由出自遮掩,還是出自忽視與無視,差之毫厘和失之千里可能是一回事。一件發生在眼前的持刀入室搶劫案,案破之日是一種結果,但那個暗藏著危機的故事卻才剛剛開始。在日常的夫妻生活中,丈夫橋北充滿創意,“比如,做愛。”近期,橋北在玩一種花生粗細的紅緞繩。芥子叫它中國結,橋北不厭其煩地糾正說,叫愛結。“紅緞繩繞過芥子的漂亮脖頸,再分別繞過芥子美麗的乳房底線,能在胸口打上一個絲花一樣的結,然后一長一短地垂向腹深處。橋北給全裸的芥子編繞愛結的過程,也是他們雙方激情燃燒的美妙過程。芥子喜歡這個游戲。”這種游戲近乎于判斷式的介紹,讀來猶如廣告片斷。敘述者刻意推出甜蜜愛意的創意,實則是其蓄意制造的鋪墊。當半夜那次入室搶劫演繹時,創意在劫匪手中便成了一種玩意。這里聚合了歹徒、橋北、芥子,圍繞著紅緞繩的多重視角,歹徒是單向的,而橋北和芥子是多重來回的。當然,或許更重要的是敘述者和閱讀者的視角,不然,“意義”何從潛入和呈現。愛結終于成了死結,幸福的游戲僅僅只是游戲的幸福。無畏和無為可能是一枚硬幣的正面和反面,我們能讓正面和反面相互注視嗎!猴子看到沙漠石頭下的蛇,應該暈倒,抑或應該快樂地跳躍過去。生活在遮蔽之中,與揭示遮蔽的生活,誰離幸福更近?這是須一瓜,或者說是須一瓜小說中那隱含的作者試圖回答的。試圖回答是一回事,能不能回答又是一回事。如同閱讀免不了從中尋求意思和忠告,其危險的結局很可能“是一種心理上的自殺”;如同批評中被米蘭·昆德拉戲稱的那種“媚俗化的闡釋”,總是“向現在時刻扔去老生常談的面紗,使得真實的面貌消失得無影無蹤。”
2003年誕生的小說《淡綠色的月亮》,受到普遍的歡迎和眾多的好評。這自然歸功于講故事的非凡技巧,還有潛藏在故事深處的形而上的轟鳴。抵制明白無誤的理解,抗拒黑白分明的人性界線,或許是須一瓜追求的理解和界線。其結果很容易讓誤解和難分難解經常降臨我們的頭上。對于排他性的信守,須一瓜甚至用了絕對兩字。這里的排他性并非是一種思想和忠告的排他性,更多成份指的是一種可視的角度,一種為感官世界敞開通道而做出的努力,一種尊重欲望的寫作態度。讀《海瓜子,薄殼兒的海瓜子》,我們能感受到人性的磨擦、折騰與逆行的種種姿態,而沉默、孤獨又是如何與溫馨作伴。但解讀與判斷呢,我們只能在徘徊猶豫中難以自拔。讀《在水仙花心起舞》,我們能處處感覺到那言語之中飄落的快樂音符,似童話般的音樂,但心中那沉重的壓抑卻無法抹去。《SS—7號導彈空越12朵紅菇》中,一對難以生育的夫妻尋求偏方的鬧劇,一系列的偏方導致一系列的誤會。鬧劇向荒唐靠攏,所有的誤會都認證了主體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幻想的瘟疫象刀一樣刺向“公共的語言”,而真相則深深陷入虛偽面具的泥淖。《夢想:城市親人》則是對都市化生活的質詢。公共話語的涂抹所渲染的都市神話與燦爛畫面,作者打上的是一個問號。問題不在于我們的城市如何都市化,而是這種生活已漸漸地失去以往生活的意義和特色。“公共生活領域與私人生活的相互關系已被擾亂。這并非由于在城市中人成為失去個性的蕓蕓眾生,而主要是因為城市愈來愈象是人人準備棄之而去的一片弱肉強食的莽莽叢林。”(哈貝馬斯語)
就個人的閱讀而言,我更欣賞須一瓜小說中像《蛇宮》、《夢想:城市親人》、《地瓜一樣的大海》、《求證:我和我奶奶同用一種血》、《乘著歌聲的翅膀》一類作品,此類小說具有更多的不可替代性。從《蛇宮》到《乘著歌聲的翅膀》,敘述都強調一種拼貼的在場,在充斥寓言的蛇宮內外,印秋和那個人都彼此離不開對方,一種對視,一種互為需求的傾訴與傾聽;來自農村的和生活在城里的彼此相遇、摻雜、共同生存;罪犯之心因生命之拯救來到另一個軀體,兩顆心在冥冥之中的奇遇……這也許都是巧合,巧合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但在小說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只能被模仿。當巧合被很好地模仿、被拼貼而呈現出一個問號時,平時所不起眼的、熟視無睹的巧合就會變得意味深長。在《地瓜一樣的大海》中,十二歲的“我”,一個孤兒早早地流浪于這“花樣年華的美麗地方”。混跡于“城市最金迷紙醉,妖人混雜的風花雪月中”這是我們所謂的巧合。但是現在它出現在須一瓜的小說世界中,這巧合就是一個隱喻。農村孩子是沒有童話,吃地瓜的孩子沒有童話,而我們分明見到了一個城市“流浪漢”的童話。這童話不是為人物而設置,它讓我體驗一種有序和無序的存在,或許是城市的特征,或許是命運的特征。再孤獨的人都會尋找合作的伙伴以擺脫孤獨,這是埋藏在意識深處的焦慮,“我有一個秘密的東西,只有我知道。它是我最大的,和愛彌爾都不說的秘密。它是一個真正的神。它是住在我血管里的親人……。”拼貼是一種隱語,是一種反諷,好的拼貼也是一種撕裂,它讓我們帶著審美的愉悅接近我們討厭的東西,它也讓我們的“討厭”去窺視“不是任何人在任何的時候都能看到淡綠色的月亮。”
“看著看著,焦距就透到她眼睛后面什么遙遠的地方去了。”
——《蛇宮》
如果說《淡綠色的月亮》的敘述視角無所不能的作為讓我們多少感到有點遺憾的話,那么《地瓜一樣的大海》的視角則令人為之贊嘆。十二歲的“我”,一個特殊的中介型的視角,幽靈般來回于鄉村和城市、成人與未成人、謊言與真實的世界。這是個謊言世界中的真實故事,又是個真實生活中關于謊言的故事。讀這篇小說,自然使我們想起本雅明提出的關于城市流浪漢的說法,這是關于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且影響深遠的概念。小說中說的更為直接簡單,“城市和農村怎么會靠一盤炒地瓜葉變成一樣的呢?它們永遠也不一樣,農村人永遠破譯不了城市的秘密,除非他變成了城里人。”
“孤兒院的兩周生活,是我這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也許沒人相信。這沒關系,本來這句話就是我和我自己說的。”這樣典型的敘述話語在須一瓜的小說中比比皆是,同樣一句普通的話語,甚至可以說是漫不經心的交待,我們都可以讀出那些隱含在表層故事中的故事,那些沒有說出來的故事。自己和自己敘說的快樂,不止是要和自己說,而是只能和自己說。一種強制性的孤獨、被遺棄的孤獨流于字里行間,對十二歲的“我”來說,竟轉變為一種自我言談的快樂。孤兒院生活中諸多快樂事件中的典型案例竟是這樣的,“一個小傻逼竟然用我藏在柜子中心愛的報紙去包她親戚送的舊皮鞋。”小傻逼最終受到的懲罰是被人把眼睛蒙起來,對“我”作全身的“瞎子按摩”。這里,“瞎子按摩”成了連接詞,一頭牽掛著“我”在城市“內臟”流竄的日子,一頭又連接著眼下不可思議的惡作劇,更搞笑的是,從未進入過按摩院的院長在處理這一惡作劇的過程中,因不解、因好奇,自己被按摩的舒適感所眩暈,“臉上浮上天使一樣的光輝。”我們很少見到如此詭異的敘述,惡作劇、厭惡、謊言、早熟都成了抵御現世的武器。他提醒我們,心理生活中唯一有價值的是情緒。所有的心理力量只是通過其激發情緒的傾向才變得有意義。《地瓜一樣的大海》之類的敘述潛藏著一種快感。很可能,欲望也會帶來相反的走勢,偶爾會做出自我夸飾,記錄下我們感到內疚卻要表現得品行端正時所采取的種種姿態。
《蛇宮》便是這鏡像世界中的另一種姿態。小說的取材,被人總結得很有意思,“江湖女郎,與蛇共舞,吉尼斯記錄,汪洋大盜……還有矗立在滾滾紅塵中的那個既透明又有礙,既封閉又開放,既隔絕又浸透的玻璃房。”一個固定的舞臺,印秋,曉菌與那人,蛇宮內外的審視與話語成了固定難變的視線,每個人都是對象的鏡子,欲望的需求,自我的幻象,都仿佛在遙遠的地方進行著意義微妙的旅行。在這場注視和討論的世界中,不止是我們能經常擁有的焦躁不安,它還多了一份詭詐,每一次談話都微妙地有點偏,影子是歪斜的,目不轉睛的注視失去了其自信,斜視的地位有所抬頭。預期的光源并不如期出現,熟悉的東西依然熟悉,卻無法進入我們記憶,而其產生的多少有點陌生的效果則深深地吸引了我們的視線。
我們可以用不同方式來閱讀《蛇宮》。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當代的寓言故事,在腦海中盡情地享用其隱語的豐富,能指的多種出路。我們也可以把它當作生活中完全可能發生的事件,如同一段錄音的重放,聆聽欣賞其迷人的敘述。一波三折的懸疑之言,如同中國式套盒一樣,我們甚至還可以繼續追尋其故事中的故事,那個神秘的他別處的、未敘述過的、散落在詞語之外的故事,那浪費掉的或至今仍未找到的人生。一個完整的事件或故事,無論是真實或虛構,記憶和詞語的復述總要伴隨遺留,它只能運用其視角的藝術選擇其部分。“少許是多少”,少許是那些,這個曾經被須一瓜用作小說題目的問題總會糾纏我們而不放。游兵的疑惑是一切敘述者開口說話前的疑惑。《蛇宮》既是敘述意義上對當下社會的抽象模擬,又是運用中國套盒手法的那種迷宮式的生動敘事,關于謎團、不解之謎,隱隱約約的可猜測之謎,猶如鬼魂附體般地追隨始終,讓人欲罷不能。謎團的本質是一種過渡,而過渡恰恰是敘事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讓書寫飽受折磨,讓閱讀深陷愉悅的必經之途。
“我所看見的根本不是我希望看見的……”
——雅克·拉康
到此為止,我們對文本的視線使用的只是一種“解釋學”,觀察的視線僅限于物鏡式的層面。被注視的注視有時應翻譯為被書寫的寫作者。我們可以說,須一瓜的小說沒有背負歷史的腳手架,父母親情基本上是空白,我們龐大的農村家族式的資源也是空缺的等等,即便這種判斷是準確的,文本也是作為外界的注視物。
凝視可不這樣。“凝視”被認為是自我和他者之間的某種“鏡像”關系,“凝視”不是字面上所呈現的被他人看到或注視別人的意思,而是指被他人視野所影響。拉康認為,在想象的關系之下,自我如何被置放在他人的視覺領域之中,以及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處境是經由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的。對薩特來說,凝視是一件使主體明白他人也是一個主體的事情。薩特還強調,在凝視中至關重要的東西絕不是他人的眼睛。《海瓜子,薄殼兒的海瓜子》講的是晚娥,老公阿青和公公的故事,故事起因于小說中不斷重復出現的一句話,“沒有那天就好了。”那天的事件就是出現了我、你、他的注視,公公為缺乏維系的難以遏制的欲望所驅使,當他在窺視晚娥洗澡時,被阿青發現,于是窺視的快感立即被一種羞恥感壓倒,窺視的主體在第三者的凝視下被客觀化為了一個對象。其實,即使沒有那天,第三者的注視還是存在的,凝視關注的不在場的注視對主體的影響,主體又是如何被撕裂、被異化、被置換。
我們剛才講過,須一瓜小說不見我們慣常所見的“歷史”劇,“情感劇”,她的小說十有八九離不開案件與死亡,但也絕非是“懸疑”劇。她身在城市,緊緊抓住的是“移民”,她人處中心,牢牢盯住的是“邊緣”,她出入高樓,落筆的總是高樓的陰影。關于真實,她慣于打破的是,把不真實當作真實加以接受的真實。關于謊言,她慣于用“謊言的真實”刺穿真實的謊言。人不是影子,不管他們對生活的把握多么閃爍不定,但你可能得進入真正的影子的世界才能發現這一點。邊緣人是不會習慣把自己看作充分自決的中心,但只有中心的“凝視”之下才能享受這種不習慣。
《乘著歌聲的翅膀》是最近的小說,名字和其他小說名字一樣,怪怪的,初看離題萬里,最終又想用隱語和含意把它抓回來。講的是換心臟的故事,先天性心臟病的少年金河,在社會的幫助下,換上薛淦的心,一個被槍斃的殺人犯薛淦的心。換了心的金河,終日迷戀于鏡像,夢見的是殺人的場景,“異常的目光,眼睛充滿了驚奇,夢見了血,墻上寫字的血嘶嘶響,它噴向雪白的墻。”換了心后金河那奇異的執迷不悟,連行醫四十年,給無數同類病人做過手術的教授被攪亂了心,“打動了教授不輕易被引發的惻隱之心。”因此,我們是處在實現了的幻想的幻覺世界里,通常所謂的“將心比心”這類道德審視的換位思考在這里實現了它的字面意義。金河換上了罪犯薛淦的心,此心不止于生命意義的跳動,他還是一種“良心”,連帶著可思維的大腦。缺席之身和缺席之心都以其缺席證明了他者的在場。“被割裂的思維”、“兩副面孔的幻想”使我們看見了紛至沓來又倏而遠逝的種種情形。于是,換了心的金河成了分裂的主體,原本之心被抹去,成了缺席的在場,被換入的薛淦的心不死,成了在場的缺席。在無形的大他者的凝視之下,金河不可言說,一說就錯。心的置換成“心”的顛覆,那早已根深蒂固的單一主體,同一性主體受到了挑戰,遇上挫折。人們發現原本認可的金河有時會隱去,而被槍斃的薛淦陰影不時顯現,那被注定不能發射的飛去來器神奇般地再次發射。它出現于金河的沉默,出現始終無法抹去的一次又一次的噩夢,夢靨的驚叫。
“前半個月,夢境是零亂的,東一鱗西一爪。柔軟的被子,人體和被子微溫的芳香,一個長頸的女孩的后腦,頭發一直粘手。雪白的墻上突然飆成樹枝的紅色。冰冷的床架,眼淚在手上澀澀地搓不開,開了一半的鞋盒子……散發著紫煙光的半球穹窿。”
換了心的金河從一開始,都是在一個異化的方向進行,各自都以隱去和顯現的兩顆彼此糾纏相互替代之心,在異化的道路上與現世主體有更大的摩擦,更多的誤認,于是驚訝之聲不絕于耳,不解之容四處可見,不止是給金河做手術的教授心被攪亂,那象征“慈善”的心也露出了并不慈善的真相。耐人尋味的裂縫、空隙,和須一瓜小說中諸多結尾一樣,金河最終還是攜帶著身份認同的幻象離開了這座“城市”。直截了當簡練的開頭和不怎么明確而意味深長的結尾,對須一瓜的敘事之境來說,這也許又是一次奇異的“拼貼”,也應驗了金河換心的奇詭的變數,“也許,我們換掉了一顆苦難的舊心,卻變生了一個更受煎熬更絕望的心……”
綜觀須一瓜的小說,給我們留下最深的印象莫過于那雙“眼睛”,其魅力在于犀利的穿越之力,細察散落于四處的真相,不忘卻那作為剩余之物的溫情。作為藝術家,尤其是作為小說家的藝術才能,她不缺正視、斜視,關于審視,她始終保留著對“他者”的權利,而關于自我的審視,似乎是一個弱項。舒婷曾有一篇議論張愛玲的文章,題目為“審己度人”,在須一瓜的小說中,我們難見“審己”,讀到的是“度人”盡多,關于“審己”,至多也只能通過其“度人”猜測一下“審己”而已。還好,對于凝視,對于作為第三者的不是觀看的觀看,對于“大他者”的視覺能力,她又能無師自通。須一瓜的小說經常用“我”作為視角的觀看方式,但其小說確實又很少有“我”的地位,很可能,對于“你”和“他”的觀看之中,也包含著“作為欲望對象的他者對主體的注視,是主體的看和他者的注視的一種相互作用。”(見斯拉沃熱·齊澤克《敏感的主體》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相互作用很重要,比如一個小說家的優勢和弱勢,長處和短處都有相互的作用。有人喜歡指出作家的局限以顯其批評的鋒芒,鋒芒是有了,但與創作并無多大益處。從某種意義上說,藝術都有局限,哪怕后現代那無處不在的“碎片”。局限是藝術賴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個美妙的東西。如同我們一開始講的,可見與不可見的鏡像關系。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日于上海
注:文中所涉須一瓜小說
1 《地瓜一樣的大海》《上海文學》2001年11期
2 《海瓜子,薄殼兒的海瓜子》
《上海文學》2004年3期
3 《夢想:城市親人》 《朔方》2004年10期
4 《有一種樹春天葉兒紅》《收獲》2005年2期
5 《回憶一個陌生的城市》《收獲》2006年3期
6 《在水仙花心起舞》《人民文學》2005年6期
7 《門內的保姆家外的人》
《小說月報·原創版》2006年6期
8 《我的蘭花一樣的流水》《鐘山》2005年2期
9 《提拉半酥》《人民文學》2006年2期
10 《老的人、黑的狗》《作家》2006年1期
11 《SS—7號導彈空越12朵紅菇》
《中國作家》2005年5期
12 《西風的話》 《人民文學》2006年1期
13 《一次用心籌備的邂逅》 《上海文學》2007年1期
14 《少許是多少》 《收獲》2007年4期
15 《乘著歌聲的翅膀》 《山花》2007年8期
《蛇宮》、《我的索菲婭公主號》、《淡綠色的月亮》、《04:22分誰打出了電話》、《求證:我和我奶奶同用一種血》、《尾條記者》均見小說集《蛇宮》華藝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