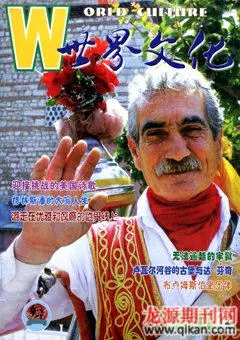布盧姆斯伯里團體
戈登廣場46號
上世紀初葉,英國著名作家、藝術家等許多知名人士聚集在大英博物館附近的布盧姆斯伯里(Bloomsbury)地區,逐漸形成一個團體,被人稱作布盧姆斯伯里團體。早年胡適先生曾譯為:百花里,概其意直取自“花開(Bloom)”,而bury于詞尾在英國通常指地區,所以翻作“里”,又隱喻這里百花齊放的文化繁榮。
布盧姆斯伯里團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劍橋文化精英的沙龍,其核心成員有: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夫婦,藝術批評家克萊夫·貝爾,傳記作家利頓·斯特雷奇,畫家朵拉·卡林頓,文學批評家德斯蒙德·麥卡錫,翻譯家阿瑟·威利,作家維多利亞·薩克威爾-懷斯特,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畫家鄧肯·格蘭特,音樂家西·特納,藝術批評家羅杰·弗萊,作家福斯特等人。除此之外,哲學家羅素、詩人T.S.艾略特、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和奧爾都斯·赫胥黎也與布盧姆斯伯里團體過從甚密。他們有著極為相近的世界觀,但沒有明確的綱領,并不成其為一個流派或運動。然而由于這個團體群星薈萃,因而在文學史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些“歐洲的金腦”多半是劍橋大學的優秀學子,幾乎所有成員都曾在劍橋的三一學院或國王學院就讀過。他們通常每周四晚上相聚,討論文學、藝術和哲學等問題。“他們的共同信仰是藝術上的嚴格原則”。這個小團體懷疑傳統觀念,蔑視邪說,探討真、善、美的確切含義,以其自成體系的審美,在當時的英國獨樹一幟。
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成員特立獨行,尤其是他們之間復雜紛亂的情感關系和性取向,向來引起人們不斷的爭議。他們行為大膽,曾因挑戰現存的社會秩序和國家機器,引起外界關注。有故事說,1910年2月,弗吉尼亞·伍爾夫假扮成阿比西尼亞的門達克斯王子,她弟弟艾德里安假扮她的翻譯,賀拉斯·科爾假扮英國外交部官員,鄧肯·格蘭特等人則假扮成弗吉尼亞的隨從,前往韋默斯訪問英國海軍的“無敵號戰艦”,得到了戰艦上海員們熱情的接待。整個騙局設計得天衣無縫,完全將艦隊司令蒙在鼓里。這個天大的玩笑后來經報紙披露出來,國防力量的虛有其表和官僚體制的漏洞百出引起朝野上下無比震驚,英國軍界和外交界頓時陷入了極為尷尬的境地。這場滑稽的“王子秀”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
“文化皇后”伍爾夫
布盧姆斯伯里團體是由弗吉尼亞和她的姐姐文尼莎、哥哥托比·史蒂芬共同創建并發展的。1904年8月,弗吉尼亞搬離海德公園的舊宅,租住在布盧姆斯伯里的戈登廣場46號。托比經常邀請他的劍橋朋友等許多文人雅士來家中開下午茶會,這里安靜舒適的環境使來客們心曠神怡,他們在這里討論問題、交流思想,后來便逐漸發展為定期的“星期四聚會”。也正是在這個沙龍里,弗吉尼亞和姐姐文尼莎后來結識了她們的丈夫。1907年,文尼莎與視覺藝術評論家克萊夫·貝爾結婚。五年后,弗吉尼亞與劍橋大學學者倫納德·伍爾夫也結為了夫婦。
1906年,托比在出游希臘途中,不幸染上傷寒不治而亡。2248e5118fded4443f1c501e1ec86fee托比病逝后,弗吉尼亞姐妹繼續和發展了這個下午茶會,她們與這些藝術家們的聯系更為緊密,她們的家成為當時“倫敦文學生活的中心”。伍爾夫的文學創作顯然與這樣一個自由的文學環境有著內在的聯系,也正是住在戈登廣場期間,弗吉尼亞開始為英國著名的《衛報》撰文審稿,并開始了她的第一篇小說《遠航》的寫作。
團體的終結
布盧姆斯伯里團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出現松散跡象,直至1920年3月,莫利·麥卡錫成立“記憶俱樂部”,為德斯蒙德和自己撰寫回憶錄,部分成員才重新聚集起來。在后來的三十年中,這些成員不定期地聚會,以絕對的坦誠為原則,回憶各自的人生經歷,撰寫他們共同的回憶錄:他們共同成長的經歷、大學時光以及在布盧姆斯伯里的日子。雖然“記憶俱樂部”成員與布盧姆斯伯里團體成員不盡相同,但布盧姆斯伯里團體是這個俱樂部回憶錄的一個重要主題。二十年代,“記憶俱樂部”的成員優秀作品倍出。三十年代,隨著利頓·斯特雷奇、朵拉·卡林頓、羅杰·弗萊以及弗吉尼亞·伍爾夫相繼故去,這個新的布盧姆斯伯里團體輝煌不再。1964年,克萊夫·貝爾逝世,斷斷續續的俱樂部聚會最終停止,布盧姆斯伯里團體徹底不復存在。布盧姆斯伯里團體從產生至今,一直爭議不斷。作為一個孤立的、唯美主義的文學組織,它對于二十世紀以后的文學藝術,乃至更廣闊的社會生活,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