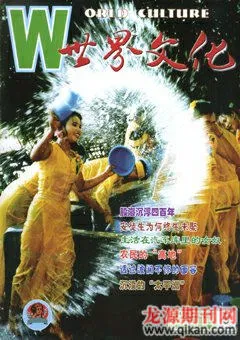愛上之愛
1925年,正值詩人里爾克50歲的生日。里爾克昔日的好友,為托爾斯泰作品插圖的畫家列昂尼德·帕斯捷爾納克向他發(fā)來了賀信。畫家在信中介紹了自己的大兒子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并說他這位已經(jīng)成為俄國知名詩人的兒子是里爾克“最熱烈的崇拜者”。就這樣,兩位詩人開始相識,并互通了書信。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在信中激動地表達了對里爾克的崇拜。用他的話說:“我愛您,猶如詩可能而且應當被愛,猶如活的文化頌揚其頂峰、欣喜其頂峰并依賴其頂峰而存活。”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還在信中介紹了此前已與自己通信多年,也同樣崇拜著里爾克的女詩人茨維塔耶娃。至此,茨維塔耶娃與里爾克、帕斯捷爾納克的書信頻繁來往。而隱藏在書信之中的愛的心曲也越奏越響。
里爾克是三位詩人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他們相互聯(lián)系時,里爾克已經(jīng)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晚年疾病纏身,離群索居,用驚人的毅力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諾哀歌》和組詩《獻給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詩》。這年是1926年,里爾克似乎已經(jīng)“寫完了”他的詩。一生浪跡天涯的詩人,終于隱居在瑞士一個幽靜的古堡中。嚴重的白血病,使他感到死亡的迫近,他甚至哀怨自己是折斷的樹枝。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茨維塔耶娃的信猶如里爾克晚年生活的一束陽光,給詩人帶去了激動,也喚起了里爾克身上尚存的激情。里爾克一生愛過許多女人,也更為許多女人所愛。但對于茨維塔耶娃在信中大膽直露的表白卻始料未及。作為一個行將枯槁的老人,面對突如其來的愛,他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但他最終還是安靜的、有節(jié)制地接受了女詩人熱情的愛。里爾克用書信應和了女詩人的愛:“我接受了你。瑪麗娜,以全部的心靈,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現(xiàn)而震撼的全部意識。”里爾克還向女詩人寄去了詩集和相片,更為她寫了一首長長的《哀歌》。這首后來被女詩人稱為“瑪麗娜哀歌”的佳作,是里爾克寫給茨維塔耶娃的情書。
與里爾克不同的是,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與茨維塔耶娃是幾乎同齡的,他倆同是莫斯科人,同樣出身書香門第,同樣曾留學德國,甚至連他們的母親也都曾是魯賓斯坦的學生。他倆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同時登上俄國詩壇。但一開始他們交往并不深,直到茨維塔耶娃流亡國外之后,帕斯捷爾納克才通過書信向茨維塔耶娃表達了愛情:“這是初戀的初戀,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質(zhì)樸。我如此愛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著愛,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議。你絕對的美。”“如今我再也無法不愛你了,你是我唯一合法的天空,非常非常合法的妻子。”帕斯捷爾納克幾乎每天都會給女詩人寫信,訴說愛意。在他看來,對茨維塔耶娃的愛無所不在,無時不在。
茨維塔耶娃是這段三角戀史的主角,他接受了帕斯捷爾納克的愛,同時也愛上了里爾克,她同時為兩個男人所愛,也同時愛著兩個男人。她與帕斯捷爾納克的交往持續(xù)了很久,而與從未謀面的里爾克的愛則是一個短暫的爆發(fā)。她對里爾克的詩頂禮膜拜:“在您之后,詩人還有什么可做的呢?可以超越一個大師(比如歌德),但要超越您,則意味著(也許意味著)去超越詩”。她同時也愛著自己的丈夫。這種愛絕對不是一種輕浮,這是女詩人豐富內(nèi)心世界的愛的釋放。茨維塔耶娃本人就是一片激情的海洋,她需要多樣的“被愛”,也需要多樣的“去愛”別人。貴族出身的她,面對丈夫是一位“賢妻良母”,在他鄉(xiāng)含辛茹苦地撫養(yǎng)著兒女。她愛帕斯捷爾納克,用她的愛撫慰著一個“半大孩童”。她也愛里爾克,愛得熱烈任性,甚至像個在父親面前撒嬌的女兒。這是一種愛的分裂,但更是一種愛的結合,不同的愛在女詩人的心中融合為一體。
孤獨使三位詩人走到了一起。亂世中,分別面對現(xiàn)實的三位詩人,驀然轉(zhuǎn)身對視,驚喜、激動之后,吐露心曲,交流出一份慰藉。當他們單獨存在時各自像星星一樣熠熠閃光。當他們接觸到一起時,便會爆發(fā)出強烈的電光。那是感情的電光,是愛的電光。他們相互依偎、惺惺相惜,在孤獨中彼此敞開心扉,用詩人敏感的心去感受對方的溫暖,理解人世間僅存的依戀。暮年的里爾克,回想當年,世紀末的情緒、一戰(zhàn)的凄慘、社會的動蕩、新舊觀念的撞擊、文藝思想的格斗、愛情婚姻的挫折,俱往矣。如今里爾克已經(jīng)走近了他生命旅途的終點,他感到“體內(nèi)的生命奇異的沉重了起來”。他一再回避現(xiàn)實,晚年離群索居,終不能排遣心中的抑郁。孤獨中他接受了與他心靈相通的年輕女詩人和對他無限崇拜的帕斯捷爾納克的愛。帕斯捷爾納克在作品遭受冷遇,其“知識分子與革命”的主題不被理解,家人全都出國,自己留守莫斯科,孑然一身的他顯得更孤注一擲,大有一種“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寂寥和落寞。他茫然不知所措,甚至絕望地感到:一切已經(jīng)寫盡。然而,里爾克與茨維塔耶娃的支持與欣賞,成為了他作為一個詩人繼續(xù)存在的理由。帕斯捷爾納克哭了,在他的淚水中有走出孤獨的欣喜。十月革命后苦悶的茨維塔耶娃,流亡國外,僑居巴黎,眷戀祖國,卻有家回不得。在異鄉(xiāng),捷克政府終止了給她的“救濟金”,法國的俄國僑民又因她的大膽的個性而對她展開了“圍攻”。獨自帶著兩個孩子的她時時感到與周圍環(huán)境格格不入。她因孤獨而寫詩,并把這種在孤獨中積蓄的感情以不同方式分給了里爾克和帕斯捷爾納克。在這三角戀情中,茨維塔耶娃表現(xiàn)出了她一貫的坦蕩,也讓我們感受到了她當時的孤苦,她似有太多的話、太多的情要與她所信賴的人分享。
這不是一場爭風吃醋的情場角逐,也不是一種消遣解悶的兩性游戲,這是一種在相互敬慕的基礎上升華出的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或者說,是一陣驟然在愛情上找到噴發(fā)口的澎湃詩情。三人對愛情表現(xiàn)出的超脫是詩人才有的超脫。里爾克聽說帕斯捷爾納克因他與茨維塔耶娃的關系而沉默了,他曾致信女詩人,因自己成了某種“障礙”而不安,并認為茨維塔耶娃對帕斯捷爾納克“過于殘酷”。詩人的愛是廣博的愛,絕不會讓妒火燃燒。
這段三角戀情的另一男主角帕斯捷爾納克則從一開始就體現(xiàn)了愛的超脫。出于對女詩人的愛,他毫無顧忌地把茨維塔耶娃介紹給了里爾克,他想與自己所愛的人分享每一份享受。當他得知茨維塔耶娃瘋狂的愛上了詩人里爾克時,雖然震驚,但隨即表現(xiàn)出了詩人的鎮(zhèn)定。他自稱“如今我愛一切(愛你,愛他,也愛自己的愛情),無限地愛著”,他甚至說“我只怕你愛他愛得不夠”。雖然這勉強的寬容中帶有一種淡淡的絕望,但這其中絕沒有怨恨,他只是欲以沉默悄悄退出這場愛情。詩人受傷的心靈暗自療傷,他克制自己的愛,埋頭苦作。與此同時,他胸前一直珍藏著里爾克給他寫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信,可見他對里爾克的愛何等真摯親切。里爾克去世后,他又獻詩以示悼念。對這位眾人眼中的“情敵”,帕斯捷爾納克從來就只有尊重與崇拜。
茨維塔耶娃以其熱情洋溢打動了生性孤僻的里爾克,又以活潑坦蕩的魅力回應了帕斯捷爾納克謹慎、細膩的愛。她在兩個男人面前安然自若,純凈、單純、真摯的愛是她愛的瑰寶。茨維塔耶娃有著自己的愛情觀,她認為真正的愛只可能是不可企及的神圣,因此她只愛遙遠的、非實在的愛。她曾對里爾克說:“我不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將失去我”;“愛情只活在語言中。”她追求的愛是一種“無手之撫,無唇之吻”。
詩人們的愛是愛上之愛。里爾克、帕斯捷爾納克與茨維塔耶娃,用他們詩化的書信傳達了他們超塵脫俗的愛。他們的愛是真正的愛,是一種崇高的精神寄托。他們的愛情是千百年來人們夢寐以求的。他們的愛是心靈的交匯,無論多遠的距離都阻擋不了。在這場多角戀愛中,我們不可能用簡單的倫理道德來評價,那樣畢竟太膚淺。詩人們純潔的愛情如果加上了倫理道德的枷鎖,就猶如折斷天使的翅膀,再美也會讓人覺得殘忍、難受,何況那樣根本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