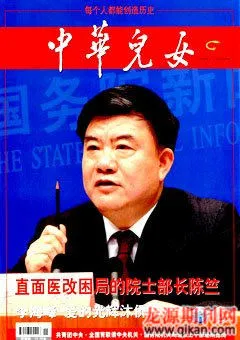我的風雨歲月
我們同遲群、謝靜宜的斗爭越來越公開化了
我們同遲群、謝靜宜的斗爭越來越公開化了。總參防化兵部政治部通知呂方正同志8月14日回部隊報到。老呂從1968年7月到1975年8月在學校工作了七年,現在要走了,學校黨組織理應對該同志作一個全面的評價和鑒定。這件事遲群并不關心,在我們多次催促下,他才召開書記會討論老呂的鑒定。鑒定稿是征求了政治部、黨委辦公室以及本人的意見后,由辦公室起草的。在書記會上,對這個稿子作了詳細認真的討論,字斟句酌作了修改,最后通過。書記會后,遲群找呂方正談了一次話,談話中,老呂對遲群的錯誤含蓄地提出了點批評意見,引起了他的不滿,于是他窺測時機圖謀報復。就在呂方正臨走前兩個小時,遲群索去鑒定書,聲稱為了“慎重”,他要再看一下。看過之后,他認為“評價太高”,背著其他書記擅自修改了書記會議集體討論通過的鑒定書。發現后,我們當然不能容忍他這種背后做手腳、違背黨的原則的行為,指出他這樣做是不對的,這才使他的圖謀未能得逞。
8月13日,柳一安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完成任務回到學校。遲群早就放出話要把柳一安趕走,現在他開始行動了。他一方面通知老柳回北京建工局等待分配工作,如果不愿回局里,在學校等待也可以。另一方面,他給安插在辦公室的親信下令,學校各種會議不準通知柳一安參加。老柳是當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工人宣傳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到學部去工作是遲群以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的身份提出,經中央有關領導部門決定從清華派出的。清華的同志都知道這個任務是臨時性的,他在學校的職務并未免除。遲群作為黨委書記個人有什么權利可以解除黨委副書記的工作職務和工人宣傳隊負責人的職務?這是明目張膽地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柳一安同志據理質問他,是何原因剝奪一個黨委副書記、工宣隊負責人的工作權利,他無言以對。我和惠憲鈞向他尖銳指出這樣對待在外辛苦工作九個月的負責干部,將會造成惡劣影響和不良的后果,請他鄭重考慮。他雖然口頭上答應研究,但一拖再拖,直到9月才召開書記會議,恢復了柳一安的工作。
自8月份以來,遲群很少同我們研究工作,連正常的書記例行辦公會也不開了。但上萬人的大學,各種問題必須及時處理,教學、科研各項工作必須有序地進行,領導機構不能正常運作,怎么行呢?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商定由我以常務副書記名義召集各部處負責人辦公會議,直接研究工作。每次這樣的會議商定的事都向他寫出書面報告,但每次他都尋找“理由”加以推翻。與此同時,他連續兩次甩開其他書記和宣傳隊負責人,私自召開宣傳隊會議,煽動攻擊校黨委其他領導人。第一次是全體宣傳隊員會議,他親自出馬講話,說:“我們要開純宣傳隊員大會,學校的人,包括劉冰在內,一個都不準參加。”“有人要同我們保持距離,我們要準備迎接一場鋪天蓋地的大字報,1acXzoSNN5dvH1qrGiYWQw==我們有辦法、有能力解決。我遲群還要做黨委書記,有人盼著我們走,辦不到。”第二次是各單位宣傳隊負責人會議,他指使他的一位親信去講話說:“現在有人反對遲群,大家知道遲群沒有錯誤,誰反對遲群就是否定教育革命,就是反對工人階級領導。”按照遲群的授意,這位親信布置到會各單位負責人把他的講話傳達到全體宣傳隊員。遲群在宣傳隊內部這些露骨的活動,表明他已經嗅到或聽到了什么,預示著他要對我們采取行動了。
已經是9月了,我們的信無論是主席或是吳德那里均無回音,怎么辦?我們不能坐等,需要走出去打聽消息。在一個星期天,我到了北京市城建委主任杜春永同志家里。這位老同志在河南我們曾一起工作過,比較熟悉,因此我向他坦率地講述了遲群、謝靜宜的情況以及我處境的困難,并打聽北京市委對清華的看法。他告訴我各方面對遲群的反映不好,問我為什么不向市委報告。當我告訴他已向吳德報告了時,他勸我耐心等待,并說:“像這樣的問題,吳德一定會管的。”又是一個星期天,紀登奎同志的女兒紀南來看我。因為我在河南省委任青委書記時,紀登奎在許昌任地委書記,我們相互來往較多,現在他女兒在清華學習,常來看我。紀南今天來,似乎有點神秘,她小聲說:“劉叔叔,我爸爸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我一面問什么事,一面把她帶到我的臥室兼辦公房間,請她坐下來,慢慢談。她說:“我星期六回家,爸爸問到了劉叔叔,并讓我告訴叔叔,遲群、謝靜宜并不代表毛主席。爸爸還問候劉叔叔好。”紀登奎的這些話表明,他這位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對于我們青年時代的友情還沒有忘記,我打心眼里感激他。紀南雖然已是大學生了,但她畢竟還是個孩子,我不便再問她什么,也不便向她談什么,只是請她轉告我對她父親的感謝和問候。登奎女兒傳遞的信息,無疑對我是重大的鼓舞和支持。我向惠、柳、呂三位同志通報了這件事,他們同我一樣受到鼓舞。我們分析,紀登奎的這些話起碼說明他對遲群、謝靜宜也是有看法的,有極大可能他已知道了我們寫給主席的信,這也從側面說明主席是會支持我們的。這是重要的信息。這就更增加了我們同遲群、謝靜宜斗爭的信心。
參加國慶招待會
9月下旬,柳一安同志得到一份9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山西昔陽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記錄稿。這個稿子不知是誰的筆記,是用復寫紙寫的。在這篇講話中小平同志說:“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也就是整頓。”我們認為這是小平同志代表毛主席、黨中央向教育戰線、科技戰線發出了整頓的號令,教育戰線有希望了,清華有希望了。要整頓,在清華首先就要整頓領導班子,解決遲群、謝靜宜的問題。我們讀到這篇講話真是高興極了。因為這是傳抄來的記錄稿,不是正式文件,也不是通過正式渠道獲得的,所以只能自己看,不能給干部傳達。但我們估計正式文件會很快下來的。現在我們要一邊等待著正式文件的到來,一邊向一些干部宣傳小平同志講話中提出的教育要整頓、科技隊伍也要整頓的任務,提醒這些同志注意形勢。馬上要到國慶節了,還沒有看到有關小平同志講話的正式文件,為了防止遲群的親信扣壓文件,我每天都直接到機要室詢問中央和市委發來的各種文件的情況。
9月27日下午,市委科教組電話通知:9月30日晚,周總理舉行國慶招待會,清華要有一位領導人參加,請學校研究確定后,28日把名單報來市委科教組。去年國慶招待會是市委科教組指名通知我去參加,今年變了辦法。辦公室把電話通知向我報告之后,我請來惠憲鈞、柳一安商量,他們二位主張我去參加。我覺得不妥,因遲群是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所以我說:“還是把遲群報上去,在這些問題上要謹慎為好。”他們二位堅持說:“遲群是政治野心家,我們已經向毛主席、黨中央及市委揭發了他的問題,不能又推舉他參加這樣重要的政治活動,他已經不能代表清華了。在原則問題上當仁不讓,這是代表廣大教職工去的,不是個人問題。”我思想上還是猶豫不決,說:“從組織原則上我們要站得住才行。”他們二位說:“站得住呀,怎么站不住呢?我們已向市委科教組匯報過這兩人的問題,科教組也沒有指定遲群去,而是指定清華去位領導人,誰去由清華決定,把你的名字報上去有什么不可以?現在就是要長我們的志氣,打一打遲群的威風!”柳一安說:“這也是斗爭嘛!”我同意了他們的意見,第二天就把我的名字報給市委了。9月30日下午6點,北京市參加國慶招待會的同志在市委會議室集合時,遲群也來了,四屆人大后的教育部已經沒有他的領導職位了,來到市委參加招待會是謝靜宜把他弄來了,這是無疑的,我作出了這樣的判斷。晚8點,人民大會堂燈火輝煌,在《東方紅》樂曲聲中,在熱烈的掌聲中,國慶招待會開始了。葉帥來了,小平同志來了,朱老總來了,陳云同志來了,李先念同志來了,徐帥、聶帥都來了,我使勁地鼓掌……怎么沒見總理呢?會來的,可能因事遲到一會兒,我在想……
剎那間掌聲停下來,小平同志走上了講臺宣布他以周恩來總理名義舉行招待會并發表講話。我驚呆了,總理不能來了,顯然是病情惡化!去年的招待會上,總理支撐著消瘦的身軀發表了長篇講話,知道他有病的同志都會清楚,他是把病痛深深地藏在自己身上,用生命在講話。今年他不能來了,真的不來了!我的思緒在延續……
是小平同志的講話聲把我從沉重的思緒中拉了出來。我向講臺望去,在明亮的燈光下,小平同志健壯的身軀、紅潤的面容比去年招待會上更健康了。從“文化大革命”以來長時間沒有聽過他的講話了,他的聲音仍然那么洪亮、剛毅有力,濃重的四川口音響徹了宴會大廳。親切的聲音仿佛把我帶回到戰爭年代聆聽我們的鄧政委戰前動員,帶回到建國以來聆聽我們的總書記作政治報告。他就是毛主席去年從江西請回來的總參謀長,第一副總理,中央副主席,替代周總理主持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的總理接班人……我的思緒立刻振奮起來。
我掃視了一下宴會桌旁的“四人幫”及遲群、謝靜宜們,看到他們得意忘形、虎視眈眈的樣子,我立刻冷靜了下來,黨內斗爭嚴酷的現實占領了我的全部思緒……時刻準備著接受最嚴峻的考驗。
決定再次上書
國慶節后,小平同志在大寨的講話文件仍未發下來,我們告遲、謝的信仍沒有回音,真急人啊!
10月5日上午,遲群突然通知開書記會,奇怪的是,不是書記會議成員的幾個遲群的親信也來參加了。來者不善,是明顯的,他們要干什么,不得而知。遲群宣布開會后,他的一個親信首先說:“應研究一下形勢。”遲群說:“就是要研究一下形勢,根據形勢研究工作。”我問:“研究什么形勢?”遲群說:“校內外形勢都可以研究。”緊接著,他那位親信用挑釁的口氣說:“我看先從學校說起。現在階級斗爭很復雜,很尖銳,黨委的領導班子就有問題,有走資派。這種人表面上裝著革命,背后在搞鬼,并且越來越不像話,大家要提高警惕。”
這位親信顯然是對著我和惠憲鈞、柳一安來的。我想既然你們開了“第一槍”,那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我說:“剛才有人說階級斗爭很尖銳,很復雜,我們領導班子里有走資派,確實如此,這是客觀存在。因此,我提醒一切革命的同志要用階級分析的觀點研究新的情況。現在我們班子里的走資派有新的特點:第一,這種走資派是‘文化大革命’中渾水摸魚爬上來的;第二,這種走資派用革命的辭藻唱高調,講大話,臺上一套,臺下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把自己偽裝起來;第三,這種走資派,用封官許愿拉拉扯扯,籠絡人心;第四,這種走資派,政治上野心勃勃,想掌握大權;第五,這種走資派,一直在搞欺騙黨的活動。這表明在新的情況下產生了具有新特點的走資派!我們必須擦亮眼睛,識破他們,揭露他們!”我這樣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地對那位親信的回敬,也是對遲群的鞭撻。他坐不住了,面紅耳赤,用苦笑來強裝鎮靜。可以看出,他沒有料到我敢于那樣直截了當地揭露他。我已下定決心,準備與遲群惡戰一場。也許是遲群未準備好的緣故,他忽然轉題了。后來1976年5月遲群在機械系的一次講話中說:“那個時候劉冰幾個人就是同我們對著干,但是雙方誰也沒有挑開,像演戲一樣。”這話說對了一半,是有多場“戲”沒有挑開,但1975年10月5日上午的這場“戲”,我們已挑開了遲群的面紗,面對面地刻畫了他的丑陋嘴臉,不是嗎!
我們發出的信沒有回音,小平同志在農業學大寨開幕式的講話正式文件還沒有發下來,遲群已公開叫陣了,該怎么辦?再寫第二封信,繼續揭發!我們經過研究作出了這個決定。這封信該怎么寫?我們商定:上封信遺漏的要詳細補上。這封信要比上一封更具體,要把遲群這兩個月來的丑惡表演,一件件一樁樁,包括時間、地點都寫上;要把謝靜宜也掛上,適度地揭發她支持遲群、包庇遲群,但仍然不要把她同遲群等同,要有區別,要使主席和中央知道謝靜宜也有問題。這封信是我起草的,10月13日第二封信完稿并復寫完畢。我們仍采取上次送信的辦法,送到鄧副主席住處,請警衛人員送交王秘書。但那位排長同志向惠憲鈞轉達王秘書的話說:“這里不收信了,信可送國務院。”老惠從城里回來說了這個情況之后,我們的心情很沉重,認為王秘書不收信,可能是頭一封信出了問題,不然為什么不收信呢?
經過反復研究分析,我們認為寫信反映問題沒有錯,小平同志看到信后一定會轉給主席,也毋庸置疑。我們原來確定的為了確保主席能看到信,經鄧副主席轉呈的途徑也是正確的,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仍然采取第一次送信的辦法不行了,只有另想辦法把信送到鄧副主席手里。經過這樣分析,我們沉重的心情緩解了。接著研究第二封信送走的具體辦法。當時老呂不在場,惠憲鈞、柳一安我們三個人冥思苦想,最后我想到了教育部副部長李琦同志。他曾經擔任過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接觸中央領導人較多。抗戰時期在太行山我們就熟悉,他為人正直,是一位可以信賴的老同志,估計他有辦法幫助我們。我的想法得到了老惠、老柳的贊成和支持。第二天,我和李琦同志通了電話,他很熱情,聽說我有事找他,立刻表示歡迎。因為那時的教育部是在原來的科教組基礎上組建的,比較復雜,其中有遲群安插的人,我到部里找他不方便。
我提出可否到他家里,他表示完全可以。于是,我們約定了時間,那是10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我來到他的家一一紅霞公寓。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似乎解放以后未見過幾次。久別重逢,回憶起以往崢嶸歲月,不免對青年時代的戰斗生活有點留戀。光陰荏苒,都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但革命的友情仍如在太行山時一樣熾熱,無話不說。我開門見山,向他介紹了遲群、謝靜宜在清華的所作所為,說明了我的來意,并告訴他這是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是8月13日寫的,已送到小平同志家里,請他老人家轉呈主席。我請求李琦同志支持我們,設法把第二封送到小平同志家里。他聽完之后,非常高興,說:“這出我預料,我沒想到清華內部幾位領導同志起來揭發遲群、謝靜宜了!”我插話說:“這叫后院起火嘛!”他笑了,我也笑了。他接著說:“這件事太好了,你們做了件好事啊!我完全支持你們。小平同志的秘書王瑞林我很熟悉,我在總理辦公室工作時他也在那里,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把你們的信交給他不就行了嘛!”我說:“上一封信,我們送到小平同志住處,是王秘書收的,不知什么原因,這次王秘書說讓把信送到國務院,他那里不收信了。”李琦同志說:“可能是送到家里不方便,我到國務院見到他時,交給他也行。你放心,信一定能送到。”我說:“那太好了,謝謝你呀!還有一件事,請你把我們揭發遲群、謝靜宜的事,向周榮鑫同志報告一下,因為他是教育部長、黨組書記,這樣的事應當向他報告,讓他知道,這樣符合組織原則。但是別的人你就別說了,請給我們保密。”他說:“這沒問題,給你們保密,并且一定向榮鑫同志報告。”告別了李琦同志,在返校的路上我對李琦同志的熱情相助感慨萬千,我又一次體會到戰友之情的可貴,體會到同志之間在最困難的時候相互幫助才是真正的戰友情。后來我得知李琦同志把我們的信交給了當時擔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同志,是他把第二封信送給小平同志的。但在那時,連向喬木同志說聲感謝的話都沒有可能。一直到粉碎“四人幫”后,喬木同志到甘肅視察工作,我才有機會向他當面表示了感謝。
從市委返回學校,我想到了萬里同志
第二封信發出兩天后,我接到北京市委杜春永同志電話,他要到學校來看我。第二天上午9點,他來到我家里,剛坐下就說:“我是有事要轉告你。”我讓他先喝點水。他說:“先說話吧!”他接過茶杯說:“昨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李先念同志和紀登奎同志召開了一個小會,聽取北京城市建設工作匯報,市里去了幾位同志,我也參加了。會議中間休息時,我和登奎同志坐在一起,他問我河南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志都有誰,我告訴了他。當我說到你的時候,他很關心,問你怎么樣。我告訴他你處境很困難,并簡要說了遲群的問題,說你給吳德寫了信。他說給吳德的信交給他了,就裝在他兜里。”
杜春永說:“我覺得登奎的意思是要我轉告你,你反映的問題他已經知道了。這說明他是支持你的,起碼他是不贊成遲群、謝靜宜的。這很重要,所以,我必須來當面給你講講,電話上不好說。”我說:“登奎的態度很明確,不知道吳德是什么態度。上封信我托肖英轉給他,并請求他接見,但他一直沒有理睬。”老杜說:“他把信交給了登奎,我想他們會交換意見的,有可能和登奎一致。不然他能把信給登奎嗎?”他接著說:“登奎是分管干部的,他知道了清華領導班子的事,我想中央會研究的,你不要太著急了,也要注意身體!”我被杜春永同志的關心所感動,我說:“老杜啊!人在困難的時候需要幫助,在困難的時候才能見真情,這個道理一點不錯,我感謝你了!”我們兩人緊緊握手,臨出門他又說:“你注意身體。”送走了杜春永,我立刻到惠憲鈞辦公室,找來了柳一安,把杜春永談的情況告訴了他兩人。他們非常高興,也認為紀登奎的舉動表明他支持我們。他們建議我再找一下其他熟悉的老同志,打聽消息,爭取支持。我表示先把第二封信送到市委后,再做其他事情。又過了兩三天,我和惠憲鈞到了市委,和送上封信的順序一樣,先向科教組肖英和軍代表口頭匯報后,把給吳德的第二封信交給了他們,請他們轉給吳德,并請求接見,我們在學校隨時等候通知。
從市委返回學校,我想到了萬里同志,他在北京市委時,常常問及和關心清華的工作,只要學校有困難,他總是設法給解決。記得1973年12月因清華教職工住房困難,我找到了他,他請來計委、建委的同志商量后,當場給清華批了10000平方米的建筑面積,還指點我拿上他的批文找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劉凱風和國家建委副主任宋養初,當天下午就辦完了一切手續。現在我又遇到了困難,需要得到他的支持和幫助。
10月中旬匆匆逝去,已到下旬了。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給萬里同志打電話。因為一般他星期天要打網球,所以我問:“明天您打網球嗎?”他說:“你干什么?有事嗎?”我說:“我好久沒見到您,很想念,想去看看您。有些事也想給您談談。”他說:“不打網球了,你明天下午3點鐘來吧,我等你。”第二天下午,萬里同志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向他詳細地講了遲群、謝靜宜的問題,以及我們兩次給毛主席寫信的情況,問他是否聽說了,知道不知道主席有什么指示。他說:“你們給主席的信,我聽說了,主席有什么指示,不知道。遲群、謝靜宜的問題我知道一點,這兩個人打著主席的旗號招搖過市,真真假假,什么主席的‘兩個兵’,我看是自封的。我對這兩個人從來都是敬而遠之。”他問:“國慶招待會,市委定的名單沒有遲群,我問過周榮鑫,教育部的名單也沒有遲群,但他卻參加了,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嗎?”我說:“我估計是謝靜宜搞的鬼。”他說:“他們是搞陰謀詭計的,你跟他們斗,你可要提高警惕,要謹慎。你要按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嚴格要求自己,不能讓他們抓住你的把柄,他們整人是要往死里整的!”我說:“萬里同志,我現在工作實在困難,每走一步,都要和他們斗。這些年來,我被整怕了,我真想調離清華,你見到紀登奎同志跟他說說,把我調出這個是非之地吧。”他說:“劉冰!你現在可不能走!你應留下跟他們斗。你一走,誰跟他們斗啊!”我說:“我走了還有別人啊!”他說:“老同志差不多都被他們打倒了。你不能走,尤其現在不能走,要從整個清華考慮。”他接著問:“何東昌的問題現在怎么樣了?”我說:“何東昌的職務什么都沒有了,一抹到底,根本不經過市委,是遲群、謝靜宜搞的。他們是不講組織原則的。”他接著又說:“你不能走。你要安心,只是工作難做就是了。這是斗爭,很復雜。你要多用腦子,遇事多想想,只要堅持‘三要三不要’,他們對你沒辦法。你給主席的信會有答復的。”隨后萬里同志又問了我一些有關教育革命的情況。6點鐘我告辭了。萬里同志的囑咐,在那些日子里一直激勵著我去斗爭!
由我來主持會議,那就要按我們的方針辦理
10月即將過去,北京的天氣已經冷了起來。學校里除了教學、科研,還要解決南方來的學生的棉衣、棉被和60萬平方米建筑物的供暖問題。教職工正在緊張忙碌的時候,遲群用北大、清華兩校的名義請來了遼寧朝陽農學院一個龐大的“代表團”,住在清華搞所謂“三校教育革命經驗交流會”。遲群從來是當甩手掌柜的,這個幾十口人“代表團”的吃、住、招待他是不管的。代表團來的第二天就要在清華召開北大、清華兩校大會,由“朝農”黨委書記向兩校作報告。
誰來主持會議,報告完了又怎么辦?我和老惠、老柳都不知道,遲群、謝靜宜不照面,這顯然有鬼。“遇事多想一想”,萬里同志的話使我多了個心眼:如果我們撒手不管,他們就會鉆空子,把會議癱瘓的責任推給我們,因此我們要作兩手準備——他來主持會議和他不來主持會議,做到有備無患。果然,第二天兩校參加會議的干部、師生早已就座,開會時間已到,遲群、謝靜宜以及他們那位北大的黨委書記都沒來。既然如此,我就來主持會議,這樣撒手不管的責任就落到了他們自己頭上。
由我來主持會議,那就要按我們的方針辦理。我宣布開會后,“朝農”的那位書記作報告,他稱清華、北大是并肩戰斗的親密戰友,呼叫著要向戰友學習,向戰友致敬。這時臺下一部分人帶頭為他鼓掌,坐在臺上的人也有為他鼓掌的,但我和老惠雙手交叉放在桌子上,老柳左手插在褲兜里,右手夾著紙煙,慢條斯理地吸著,這鮮明的對照引起了臺上遲群兩個親信的交頭接耳。報告人講完之后,又是一陣掌聲,我們仍然不鼓掌。
報告會后,“朝農”代表團要到北京郊區清華農場分校參觀。我們決定由惠憲鈞和教改組組長夏鎮英同志兩人作陪,北京大學是那位受遲群指揮的黨委書記親自出馬作陪。據惠憲鈞同志說,在農場分校,北大那位書記講話時大肆吹捧“朝農”,說學不學“朝農”經驗是態度問題、立場問題、是否堅持毛主席教育路線的問題;現在有人公然反對學“朝農”,說要結合實際,從實際出發,這是借口,實際上是堅持搞修正主義教育那一套;對這種人要保持警惕。后來老惠對我說:“這位書記顯然是對著你劉冰來的。”那位書記還對老惠說:“你是宣傳隊的負責人,你可要警惕。”惠憲鈞回敬說:“我看你才要警惕呢!不要稀里糊涂,誰是修正主義臉上沒字。”
老惠和夏鎮英從農場分校回來向我匯報時,我說:“從整頓鐵路開始,從軍隊到地方各方面工作都在整頓,而我們卻在學‘朝農’。整個教育怎么搞,小平同志在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這是毛主席、黨中央的精神。但現在看不到中央的正式文件,教育什么時候開始整頓,如何整頓,這是需要認真考慮的。”我要夏鎮英研究一下。老夏說:“最好看看文件再說。”1976年,遲群、謝靜宜在機械系的會上批判我的時候說:“劉冰他們想盡一切辦法把鄧小平的講話搞到學校來,并且急于要傳達。”一點不錯,情況屬實。我們就是以鄧小平同志講話為武器,同他們斗爭的。
被告審原告
9月間,我們發現遲群在宣傳隊的活動不正常,曾經考慮過在干部中揭開遲群的問題。但又考慮到他那樣做是錯誤的,我們不能以錯對錯,去做違背原則的事。10月5日遲群公開挑釁以后,我們在發出第二封信的同時,考慮到在斗爭的緊要關頭給少數干部就遲群問題的性質打打招呼,這不違背原則,而是捍衛黨的利益。于是我們分別找了系黨委書記以上的幾位同志,說明遲群的問題,提醒他們保持警惕。遺憾的是這件事我們做晚了。
11月3日,我和惠、柳兩同志原定下午2點半進城參觀展覽會。下午2點25分,遲群辦公室一位工作人員到我的住宅叩門,我問:“有什么事?”他說:“下午3點鐘在第二教室樓召開常委會,遲群讓我告訴你。”并說:“進城的車子,我已通知車隊不來了。”這位年輕人,平時見面總是笑瞇瞇的,此刻,他面色沉重而又有些為難,表情很不自然地站在門口。從他的神態和吞吞吐吐的話語中,我意識到有什么事要發生了。
送走了年輕人,我立即打電話給惠憲鈞,告訴他遲群辦公室來人通知3點鐘開常委會,我判斷是有關我們信的問題,請通知老柳迅速到我辦公室商量對策。我騎自行車趕到辦公室已2點40分。惠、柳二人的判斷和我一樣。我們分析,既然常委會的召開是關于我們信的事,開會不和我們商量,搞突然襲擊,證明毛主席支持遲群,而不支持我們。怎么辦?正在這時,遲群到我辦公室來了。他倒背著手,大搖大擺,喜形于色地提高嗓門說:“啊!你們都在這里。”我問:“你干什么?”他說:“3點鐘在二教樓開常委會。”我說:“你不是已派人通知我們了?如果沒有別的事,你可以走了!”他討個沒趣,溜走了。我看看手表,離開會還有10分鐘。你一言,我一語,我們三人緊張地商量著,認為我們要堅持真理,實事求是,一切按黨的原則行事。既然是關于信的問題,很可能要我們在會上宣讀,于是老惠跑步到他辦公室取來信的底稿,然后我們三人快步走向第二教室樓,進了會議室剛好3點整。
滿屋子都是人,黑壓壓一片。我們徑直地走到按慣例常委會開會時書記們的席位就座。這時我才注意到,除了常委、各系黨委書記、校級各部處負責人外,還有很多生面孔。后來發現有北大黨委的人,我這才明白了那些生面孔都是北大的人。今天的會非同一般,大概是兩校黨委聯合批斗我們,我作了這種判斷。批斗怎么辦?照常規辦!運用我多年挨斗的經驗應付就是了,我下了這樣的決心。三點一刻,吳德同志在遲群、謝靜宜的簇擁下進入會場。這位我們盼望了七十多天要求接見而不予理睬的市委第一書記、政治局委員,今天我們總算見到了。出于禮貌,我站起來同他握手,他冷冰冰地點點頭,我已伸出的手只好收回來了。看到他與遲群、謝靜宜肩挨肩、親密交談的樣子,我感到失望。
吳德從座位上站起來,清了清嗓子說:“這一個時期,清華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劉冰、惠憲鈞、柳一安三位副書記和常委呂方正四人給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寫信,告了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同志和我們的市委書記謝靜宜同志。偉大領袖毛主席對于他們的信作了批示,現在我把批示的主要精神給大家傳達一下。”然后,他對主席的指示,隱而不露,用他自己的話說了一大篇。這些話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他自己的,誰也分不清楚,但給人的印象是:劉冰等人是反對毛主席的。他提示說:“這個問題是什么性質?這個是非要弄清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進行討論,辯論認清問題的性質。”然后,他宣布:“這個會請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同志主持。”這時,遲群仰起頭,神氣十足地站起來說:“現在開會,先請劉冰他們把他們的信在這里念一念。”
我站了起來,拉過話筒,開始念信。我想這是難得的好機會,要利用這個講臺揭露、控訴遲群、謝靜宜的罪行。我放開嗓子,大聲朗讀,心想要讓到會的每一個人,要讓全清華所有的人都能聽到遲群、謝靜宜的條條罪狀。遲群事先布置的嘍羅們不斷地對我圍攻、搞得沒法念下去,我幾次提出不念了,他們才不得不暫停圍攻,讓我把信念下去。
念完了信,接著是對我們的批判,發言者不用說都是遲群、謝靜宜事先布置的。帽子、棍子一齊向我們打來。罵我們是“誣告”,是“惡人先告狀”,是“欺騙毛主席”,是“用寫信的辦法反對毛主席”,等等。我申辯說:“我們給毛主席寫信反映問題,正是對毛主席、對黨中央的忠誠。信里反映的問題都是事實。”遲群的一個親信說:“我可以證明,他們信中說的什么燒被窩、摔杯子等等都是編造的,我天天在遲群同志那里,我怎么沒見到。”這時,吳德同志火上澆油,插話說:“劉冰!你應該老老實實,把你們的活動拿到桌面上,不要在桌子底下活動。”
也許吳德同志有什么難處,但這種時候,說出這樣違背事實的話,迫使我不得不說:“我們沒有搞桌子底下活動,我們完全是按照組織原則辦的,給市委科教組匯報過,給吳德同志報告過。”吳德說:“你沒有給我報告,你那是信。”我說:“信也算數吧!我們還兩次請求你接見,要向你匯報,這是在桌子底下活動嗎?”他啞口無言了。頓時,吳德同志的形象,在我心中倒塌了。
(未完待續)
文字編輯:孫